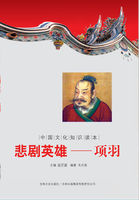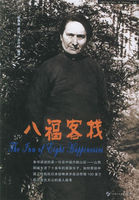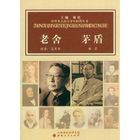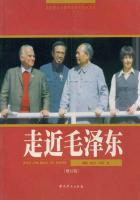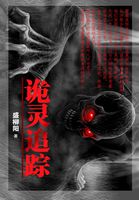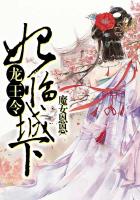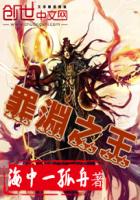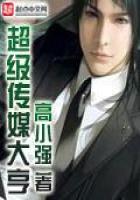博闻强记的天才
关于吴兴华,我父亲其实从未向我提起过。2005年年底,我收到友人冯睎乾的电邮,他说我父亲是吴兴华的至交,问我家中是否藏有吴兴华的遗稿,这时我才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之后我便留意有关吴兴华的一切。到了2007年,李安的电影《色,戒》上映,我当时正整理张爱玲的信件,竟意外发现了六十二封吴兴华写给我父亲的信。
吴兴华自小便非常聪明,因成绩出众而连续跳级,十六岁即考入燕京大学,同年在《新诗》上发表《森林的沉默》,一鸣惊人。我父亲在《林以亮诗话》中常常引用他的新诗。夏志清在《追念钱锺书先生》一文中曾引述我父亲的信:“陈寅恪、钱锺书、吴兴华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后逝世,从此后继无人,钱、吴二人如在美国,成就岂可限量?”后来读到王世襄也这样评论:“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
吴兴华生于1921年,浙江杭州人,比我父亲小两岁。他父亲是医生,家中兄弟姊妹共有九人。他在北京崇德中学读书时,认识了同校的孙道临,孙道临后来也成为了我父亲的好友。
我父亲跟吴兴华大概在1939年认识,当时吴兴华在燕京大学西语系念书,我父亲则从上海回到燕大就读。由于志趣相投,他们很快便成为好友,父亲也认识了吴的室友孙道临。吴兴华在家中排行老三,故朋友也昵称他为“吴三”。在燕大读书时,他和我父亲合编《燕京文学》,翻译、发表了大量英国浪漫主义诗歌。1940至1941年,他们又向上海的《西洋文学》供稿,吴兴华更相当前卫地介绍并节译了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这部奇书的中译本到2012年才问世)。吴兴华因此认识了当时的杂志主编张芝联。我父亲和张芝联早在1935年已相识,当时他们是燕大同窗,后来又一起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一起借读武汉大学和上海光华大学。之后我父亲独自回到北平,张则留在光华读至毕业。多年后,张芝联成为了法国史专家,也倡导了中国的人权研究。
到了1941年秋,张芝联回到燕大研究院攻读历史。他、吴兴华和我父亲在东门外赵家胡同合租了一所四合院,我父亲和吴兴华住西厢房,张芝联和妻子郭蕊则住北厢房,彼此切磋学问。但这种快活日子仅维持了三个月,然后便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改写了这几个人的命运。
他们读书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父亲曾自叹跟吴兴华切磋学问,像虬髯客遇上李世民,怎样追也望尘莫及。几年后吴兴华给我父亲写信说,当时大家嗜诗如命,一起“玩命念英国文学恨不得要赛过英国人”。到80年代,我父亲写信给张芝联、郭蕊回忆往事,大谈吴兴华的才学和性情,信里内容很多都被张、郭采用到纪念吴兴华的文章内,已收录到2005年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从父亲的这些信中,我发现吴兴华在大学时已很神。
我父亲认为即使没测过吴兴华的IQ,也可肯定他是天才。先说外语能力,他不但精通英语,且法、德、意等欧洲语言皆一学就会,成绩全班第一,听说读写都没有问题。后来还能阅读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他外语学得快,除了有照相机般的记性外,也跟耳朵灵敏有关。一次,有位美国教授在黑板上抄了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一看便立即指出某行的“ed”应是“d”,因为“ed”有轻音,那行就写成十一个音,多了一音,一查果然,可见他对诗歌节奏是多么敏感。据我父亲回忆,吴兴华还有一心三用的能力:他往往一边打桥牌,一边看书,同时和其他人谈笑风生,而每一件事都能做得非常流畅,令旁人啧啧称奇。他看书也是一目十行。有次他到学校图书馆,规则是每人限借三本,他却一口气借了十本,当然不批准,于是他就坐在那里东翻西弄,过不了三个小时,便把十本书的重点都记在脑中,然后把书归还,施施然出去打桥牌了。
当然,最传奇的还是他的记忆力。他房间里常放着几本旧诗选集,如《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故意引人打赌,如果随手翻出一首诗,你念出一句而他不能把诗题、作者和上下句说出来的,他便输两毛钱,否则对方便要用两毛钱买花生请他吃。他从未输过,后来大家知道,都不敢再赌了。一次,有位叫汪玉岑的诗人嘲笑吴兴华只懂埋首故纸堆中,吴之后便对我父亲说:“如果Hello,Mr Wang能举出一位名诗人、一首名诗而我未曾看过的,我可以从此不谈诗。”那“Hello,Mr Wang”就是我父亲和吴兴华戏称汪玉岑的外号。这令我想起钱锺书和我父亲也经常在私下里以诨号称人,例如卞之琳便呼为“鱼目诗人”,叶维廉是“花岂洁”等。1944年,吴兴华写信跟我父亲说,不论是英、法、德、意哪一种语言,只要是好诗,别人一提起,他便能立即说出它形式上的细节、内容的好坏,否则他便回家再念十年书。
关于吴兴华的博闻强记,例子当然数不胜数,我不妨再举一事。在燕大西语系读书时,包贵思教授(Grace Boynton)开现代诗课,用叶芝(W.B.Yeats)编的《牛津现代英诗选》为课本。大考时选出十节诗,要学生猜出作者并陈述理由,可这十节诗并没有在课本内。吴兴华不但能猜出作者,还能说出诗名和上下文,因为他全都看过,且过目不忘。他有一篇学期论文,题目是《评论现代诗选各选本之得失》,为了写得滴水不漏,他遍读了清华、北京国立图书馆和我父亲所藏的各种选本,然后在论文中逐一论列,内容竟超过包贵思所知。照这类轶事来看,我父亲认为他是另一个钱锺书,的确不是没有理由的。
当吴兴华遇上钱锺书
钱锺书和吴兴华二人有没有交往呢?1942年,我父亲在上海认识了钱锺书,钱比他大九岁。那时吴兴华在北平沦陷区,经常跟我父亲通信。在1942年4月8日的一封信上,吴兴华第一次提及钱锺书,他只写了一句:“钱锺书现在干吗?”我没有父亲回复他的那封信,但可猜到他一定是去信时提及钱锺书,所以吴才有此一问。我想,吴兴华跟钱锺书最早的交往,应该也是我父亲做中介的。到了1943年10月22日,吴兴华在信中这样写:“前几天我又翻了一遍钱锺书先生的杂感集,里面哪管多细小的题目都是援引浩博,论断警辟,使我不胜钦佩。可惜我此时局促在北方,不能踵门求教,请你若见到他时,代我转致倾慕之意。近来我总没心念英文,也找不到一个有点脑筋的谈谈英美文学,此地大部分号称主修英文的人,等毕业了,关于整个世界文学的知识,还赶不上我们大一的时代。”
单看这一小段文字,已可见吴兴华的傲气,对自己的学识十分自负,同时也看到中年钱锺书在那个文化小圈子中的地位。最耐人寻味的是信中提到“杂感集”,钱锺书根本没有一本书叫“杂感集”,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猜那就是《谈艺录》的初稿。《谈艺录》在1942年写就,其后不断修订,直到1948年才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钱锺书在序后附识:“书既脱稿,偶供友好借观。”可知吴兴华在1943年看的“杂感集”,大概就是流传于朋友间的《谈艺录》手稿了,而“杂感集”也许就是《谈艺录》最初期的书题。由此已可看到,吴兴华这叠书信实在很有文学史价值,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出版吧。
1985年,孙道临来香港,我父亲跟他聊起吴兴华,说吴曾和钱先生对谈古诗源流,博学如钱先生亦不禁叹服。几年前,吴兴华的妻子谢蔚英接受访问时说:“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出版,兴华提了一些意见,都被钱先生接受。”
钱锺书是否真的接受年青小辈的批评呢?友人冯睎乾给我看过一本他多年前买来的盗版《谈艺录》,由香港鸿光书店印行,是上海40年代旧版的影印本。友人发现这旧版中,钱锺书的序后多了一条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附记,只有两行,第一句是:“此书刊行,向君觉明、吴君兴华皆直谅多闻,为订勘舛讹数处。”该是40年代末第二次印刷时加上去的。但我翻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种《谈艺录》新版,整则附记都消失了,很奇怪。我怀疑到了80年代,连钱锺书自己也没有这版本,所以后来的修订版都漏了这则附记。
钱锺书、吴兴华真正见面相交,可能始于1952年。当时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钱锺书主持英译汉的翻译组,吴兴华、张芝联也参与了口译和审稿工作。钱锺书很爱才,我父亲说他和吴兴华对谈古诗源流,大概就是这时。他们的关系应该很好,因为据谢蔚英回忆,吴兴华在1966年去世,她与钱锺书、杨绛夫妇为邻,杨绛多次问她生活有否困难,还设法帮她。当时她的大女儿吴同十多岁,没有工作,杨绛便借口要找人抄《堂吉诃德》译稿,让吴同帮着抄,每次也付给数倍的稿酬。翻译家李文俊曾说过一件轶事:在干校时,一个年轻人向钱锺书请教一个英语问题,钱先生看了一下,便说:“这种问题还来问我,你去问谢蔚英就行了。”李文俊又说:“谢蔚英在文学所图书室管理外文书刊,钱锺书乘借还书常去她那里闲聊打趣,博美人一粲。这也算是苦中作乐了。”为什么李文俊说她是美人呢?吴兴华在1951年写信给我父亲时曾提及当时还是他女朋友的谢蔚英,说她是“燕京校花”。
关于钱锺书、吴兴华的文学因缘,大概还有一件事可以讲讲。那是1985年,吴兴华已去世了近二十年。当时我父亲写信给钱锺书说:“亡友吴兴华在华北沦陷时自修旧诗,昔年曾抄录其戏作旧诗四首,根本未经人指点,亦从未向人提过,今录上以博一粲。”其一是这样的:
哀乐相寻剧可怜,故都乔木又风烟。
铜仙去国三千岁,锦瑟留人五十弦。
北里笙歌犹昨日,西台披发忆当年。
蓬莱弱水今清浅,输与麻姑一怆然。
我查过吴兴华的信,这四首诗是1947年写的,从来没有发表,除此之外,也没有再见过他写的旧诗了。看过他旧诗的人应该绝少,除了父亲,就只有张芝联、郭蕊等几位好友,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人,就是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兼电子计算器专家吴允曾。他们在40年代中期相识,吴允曾也精通德文,曾写德语情诗,也许正是这样,两人便非常投契。吴允曾记性极强,他很喜欢吴兴华那些格律精严的旧诗,往往一看便能背诵。
钱锺书对吴诗又有何评价呢?他在给我父亲的回信中说:“与兄交近四十年,不知兄作旧诗如此工妙,自愧有眼无珠,不识才人多能,亦克善藏若虚,真人不露相,故使弟不盲于心而盲于目耳。今日作旧诗者,亦有美才,而多不在行,往往‘吃力’,‘举止生涩’;余君英时、周君策纵之作,非无佳句,每苦无举重若轻,‘面不红,气不喘’之写意自在。尊作对仗声律无不圆妥,而蕴藉风流,与古为新,盖作手而兼行家矣。欣喜赞叹,望多为之。”原来钱锺书误把诗作当成是我父亲的,评价虽然不错,但是否只是客套话则很难说了。我不懂旧诗,也无从判断。
谈文论艺
1941年吴兴华毕业,留在燕大任教,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校方还打算保送他出国留学,但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封锁燕大,他只好转行当翻译谋生。
在1985年写给张芝联、郭蕊的信中,我父亲谈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愿景。那时他和吴兴华在燕大当助教,一心要在学界发展:“学校方面内定在我教书两年之后,送我去Berkeley(伯克利)深造,谢迪克的理想是西语系应有以中国教师的核心,将来以Lucy赵(赵萝蕤)、我、兴华三人为成员。如果没有珍珠港事变,说不定我仍然会走上这条路。如果从硕士读起,三四年下来,英文至少可以弄通。无奈日本人一偷袭美国,兴华同我二人的命运就此重写。”
1941年12月7日后,燕大被日军占领,师生解散,大家便各奔前程。我父亲留在上海,吴兴华则与众多兄弟姊妹挤在会馆的小屋里,终日读书作诗,生活非常艰苦。
沦陷期间,吴兴华的两个妹妹先后病逝,对他打击甚大,同时因为生活清苦,营养不良,结果患上了肺结核,之后再也出国无望。那时为了生计,他曾经和德国神父合编德华字典,又为中德学会编译了中德对照的《黎尔克诗选》(黎尔克,今译里尔克)。1947年,吴兴华把这部诗选寄给我父亲,附信说:“我自己只有这册,希望你别丢了。”但不知道多少年后,这书给人借去,竟真的遗失了。父亲想从别处弄一个影印本来,闻说哈佛有一册,便设法去借,但对方回复因为纸张脆薄,无法影印,结果也没有办法借到。据我所知,吴兴华有二十七首里尔克译诗已收入臧棣编的《里尔克诗选》(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可惜2005年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却漏收了。
北平沦陷,工作不稳,反而令吴兴华更迷上读书写诗,而他跟我父亲的通信也是这时期最频繁的。现在我家里有他六十二封信,三封是英文,其余的是中文,中文用白话。所有信都用墨水笔写,他曾说没有墨水笔便一切写作翻译皆无法进行。通信自1940年开始,直到1952年,即他十九至三十一岁的时期,多数由北京寄往上海,1949年后我们南下,信便寄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