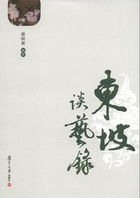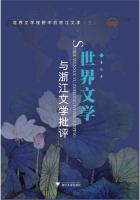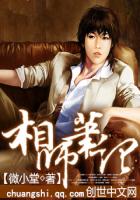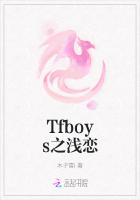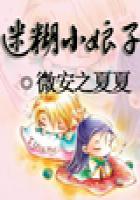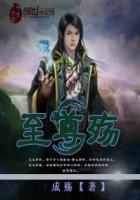采访:《南方周末》记者张英杜越
时间:2009年10月23日
吴伟是国务院新闻办三局副局长,“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面向全球出版商,吴伟组织“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出版人3 3对话会,还邀请了奈斯比特和夫人发布他们的新作《中国大趋势》。
书展开幕前,有120家德国出版社宣布将出版新的中文翻译图书,其中包括40部文学作品和20部作品集。
从2004年开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启动。2009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出台。在赴法兰克福书展前夕,《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吴伟。
中国报纸没有一家真正国际化的
南方周末:国新办做“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
吴伟:中国图书为什么要走出去?现在中国的产品制造,已经誉满全世界。外国人从中国的产品开始认识中国,但是我们的文化传播没有跟上。结果就导致中国越发展,它觉得你越威胁它。所以西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崩溃论”、“威胁论”、“责任论”、“机遇论”,这里边比例大和声音高的是“威胁论”。
因为国际经济危机,西方的发展模式受到质疑和挑战,于是国际目光聚焦在中国,“中国模式”被热议,出了若干本比较有名的著作,其中有一本叫做《当中国统治世界》。它引用了高盛的有关数据:到202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2050年就是美国的两倍。过去两百年里,都是西方统治世界,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等一切都是西方定标准,全世界都要按照它的标准来作衡量下判断。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西方人就不得不在中国人参与制定的标准下生活,就不得不学习中国的文化。他们为这种情景担忧,也很恐惧。
我们的对外传播没有把我们的核心理念传播出去。就像你的一个邻居,他原本默默无闻,什么也没有,你就忽视他。突然有一天,他站了起来,长大了,你又不了解他,就心怀恐惧。我和奈斯比特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他说国际攻击我们有三个F,就是恐惧、嫉妒和不理解,经常这样心情复杂地攻击你。因为他们对我们完全不了解,我们虽然一直在做工作,但没有取得根本的改变。因此,加强对外传播工作,非常有必要。“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是其中的一个举措。
南方周末:在对外宣传推广中,和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相比,图书的份额占多大?
吴伟:图书在文化产品的产销额上,算是大户。我们通常称自己是出版大国,但却不是出版强国。比如,我国去年出版图书品种突破了25万种,但单本的销售量能卖一万册就算销售不错。13亿人的大国,分母那么大,单品种销售那么少,更不要说图书往国外传播了。
想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我们作过调研,有三个路径:电影、报纸、图书。中国电影的发展我们有目共睹,是不是真正能传递我们的价值观,我不好评论;中国报纸没有一家真正国际化、市场化的,在国外我们没有竞争力。去年奥运会和奥运会之前的两年,我们在国外一些大报做了一点国家形象广告,价格非常贵,好几百万花出去了,到底有多大作用,我们无从评估。
第三就是图书。三个路径比较,图书应该是性价比最好的。只有书才能表达人的深刻思想,那种有系统的思想,有理论架构的思想。如果我们把一本书放在图书馆,它面对的就不是单一的读者受众,是一个你想多少就是多少的受众群。
南方周末:我看到数据说,2004年的时候,中国图书的进口和出口是逆差,到了2006年的时候,就变成了顺差,为什么有这样的巨变?
吴伟:图书的实物出口逆差指的是贸易额,贸易量应该没有逆差,因为中国的书便宜。通常所说的逆差指的是版权贸易,1999年是15:1,那么到2007年就是四点几比一,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纵向地看,我们还是有很大进步的。你说的顺差是2006年北京国际书展和法兰克福两个书展得来的,不是整体情况。光这两个书展实现顺差也是二十年来的首次,说实话,政府的推动还是很大的,希望能够有点成绩。所以,很多出版商把平时做了的也拿到书展上签约,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不会说,不说,说得不好
南方周末:在目前的图书出口中,贴钱补助性的输出和商业性的输出,各占怎样的比例?
吴伟:过去来申请资助的,100本我们同意70本,现在大致有50本,甚至40本,反正比例越来越小。申请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批准的越来越少。
我们更加希望有这四个方面的书,即国情类的、文学类的、文化类的、科学类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大文化。我们把今年这个“文化著作翻译工程”叫做“推广计划”的加强版,也有人叫升级版,反正是支持的力度更大了吧。我们更加注重翻译系列出版物。因为是想通过量来达到质的飞跃,因为一本书的力量和三十本书的力量是不同的。另外,我们的“翻译出版工程”,除了翻译费用,还可以申请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
南方周末:用于此类项目的经费有多少,够用吗?
吴伟:和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相比较,我们的钱花得真不多。电影报纸都是大头,图书是性价比最高的。基本上每年是1000万,今年加上翻译出版工程能达到3000万。
我们还有一个“推广计划”的子项目:“中国之窗”。“中国之窗”就是给国外的100家知名图书馆赠书。具体操作是我们给书目,图书馆选好了之后,我们赠。凡是在图书馆设专架专室陈列这些赠书的,我们还会多赠。
南方周末:中国的出版社在国外发展业绩怎么样?
吴伟: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几家出版社在国外设了出版机构,直接走出去。我们的外国专家顾问,还有当地的华人华侨,都给他们提了很多意见、建议,所以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出了不少东西,什么中国画册、西藏的画册,而且不赔钱了。再比如像人民卫生出版社,先在美国成立出版公司,接着就收购了加拿大戴克出版公司的医学部分,然后又去美国收购小出版社,这样等于有了一个本土化的出版平台,这样的本土化可能是我们图书出版“走出去”的必由之路。
就像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的原老总赵斌说的,出书和卖书就像厨房和餐厅,厨房离餐厅老远老远的,弄出的菜都凉了,或者那菜根本就不符合人家那口味。如果餐厅跟厨房离得近,你就可以随时改良。因为有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传播方式的问题,所以我们新闻办特别希望找一些有世界影响的人来写中国,从而解决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的问题。
南方周末:比如库恩写《江泽民传》、奈斯比特写《中国大趋势》那样?
吴伟:我们希望这样的书会慢慢越来越多。希望找到那些有影响的学者、作家,我们并不强加给你什么观念,而是请你来中国走走看看,你希望得到哪些帮助,你希望得到哪些资料,或者说你希望采访谁、见见谁,深入了解情况,我们都可以帮助安排。你给他提供一点儿方便条件,他做起工作来就会更快一点儿、方便一点儿。我们没有说你必须写说明,必须怎么写,没有这样的要求。
奈斯比特写《中国大趋势》还真不是一时性起,更没有走马观花,他关注中国几十年,来了一百多次。最近这三年,他为了写这本书,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研究院,他是严肃认真的。《中国大趋势》明年可能有很多国家的出版机构会购买版权,用不同的语言出版,哪个中国学者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比如,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里面提到3T:天安门、台湾、西藏。台湾他去过多次,北京他都来过一百多次了,唯独没去过西藏,他希望去。希望去我们就安排,你想看什么就看吧,结果他看完了回来说,这是他生平最伟大的一次旅行。他觉得他眼睛看见的,不是西方媒体里描述的那个样子。
任何事情都有多面性,不只是两面。所以,对外宣传中国,对外介绍中国,我们老说人家不理解我们,对我们有偏见。当然有他们的问题,没来过中国,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有冷战思维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有问题,一个是我们没有说,也没有做,有些事可能我们觉得这有什么呢,不用说,恰恰那就是他们关心的事情。有的时候是我们说了,没说好,说的不是他想要听的。
南方周末:奈斯比特印象中的西藏是什么样的?“伟大的旅行”指的是什么?
吴伟:奈斯比特这次到西藏,除了自己到社区基层采访外,也与很多地方官员会见,几次座谈会上,很多官员都在那儿讲结论,什么多少年我们翻天覆地,我们现在生活好,我们宗教信仰自由,然后就一堆GDP。奈斯比特和妻子就有点着急,我也有点着急。我跟这些官员说,他们都是天天看《中国日报》的人,你不用给他讲这些,他都能看得见,都能查得着,要讲一点故事,或者回答他们的问题。
于是奈斯比特就问,去年“3·14”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那么多人攻击中国?去年“3·14”是从哲蚌寺开始的,刚好一位活佛就是哲蚌寺的,于是他就讲,这么多年因为党的宗教政策好,宗教热不断升温,信教的人就越来越多。拉萨是高僧大德聚集的地方,生活条件也好,吃穿用度都不用花钱,之外每年还有两三万元的收入,外地的人愿意到拉萨来学经。他在寺院学习三四年,学完了之后他就不要走,就想入寺,那么多人想入寺,寺院就承受不了啊,寺院就考试择优录用,一些考试没通过的人,就开始闹事。去年“3·14”,凡是正式注册的喇嘛,凡是有正当工作的工人、农民,没有上街的。上街的全都是那些闲散人员,农民不好好种地,喇嘛不好好念经,都是这样的人。
奈斯比特听懂了,他说,达赖喇嘛说过去他在的时候西藏是天堂,现在是地狱,有这样的地狱吗?奈斯比特说,为什么达赖的威信在西方这么高,西方人都说他好?为什么班禅没有人说他好?因为达赖老在西方说,西方人老能看见他,他看上去慈眉善目的,懂得西方人的说话方式,真的是很会说。我们不会说,甚至是不说,说得不好,所以,这样的状况必须要改变。
这次到西藏以后,我就更加觉得,西藏的故事很多,没有讲好。我们过去出的书,数字多,故事少。假倒不假,但它是结论式的。外国人说话肯定不这么说,一定是先讲一个故事,然后让你自己得出结论。所以,咱们的这种叙述方式,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
推广中国的价值观极其困难
南方周末:我们的图书对外推广怎么走?是我们提供无偿的版权还是给出版补助?
吴伟:在2004年之前,我们作过若干尝试。比如,我们跟外国出版商承诺,你们看好了哪本书,我们负责给你买版权,或者我们买了版权之后送给你,都不成功。他们觉得你们买了版权,你们不是要强加于我吗?你们送我们版权算怎么回事啊,他觉得你有强行推广的意思。
后来到了2004年的“中法文化年”,法国图书沙龙咱们是主宾国,新闻办原来的老部长和作协老书记向我们建议,资助国外出版社,让他们翻译咱们的书。开始我们提供了一个三百本的书目,他们选了其中几十本,有些是书目上的,有些不是书目上的,我们后来一并资助了七十种,真的是大获成功。当时,希拉克到了中国展台,原来预计在那儿待七分钟,结果在那儿看了四十几分钟。不光是总统喜欢,老百姓也喜欢,四五天的时间,三分之一的书就卖完了。2005年,我再去法国的时候,书全卖完了。我们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我们给国外出版商一点翻译费,钱不多,但效果很好。南方周末:目前我国图书引进和输出是什么比例?
吴伟:纵向看,有进步;横向看,比例还是失衡,每年引进一万本左右,才输出两千多本。
现在很多世界上畅销的好书,中国基本上都能同步出版。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美国出了22本书,我们不仅全都引进了,自己又编写了二十多本。我去书店一看,满书架子都是“奥巴马”,中国人实在是太热情了,别的国家不会有我们这样的热情。中国的出版人要好好想一想这个事,反思一下这个现象。
南方周末:现在国内一些出版社也开始直接出英文版了,还干脆在国外设立分支出版机构。
吴伟:是的,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想说说中国出版社直接出版英文版的好处,对版权贸易有很大推动。比如,我推荐了两套书给剑桥大学出版社,一套是《中华文明史》,一套是大众化的中国文化丛书。因为他们以前出过《剑桥中国史》、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他们的CEO潘仕勋也很愿意出版中国图书。潘仕勋把两套书都带回剑桥,回去不久告诉我,中国文化丛书的三十本书通过了他们学术委员会的审查。这和我的预想完全相反,我以为他们会看中《中华文明史》的。
后来反复和他沟通,才知道原因。中国文化丛书是已制成的英文版,虽然我们的英文离他们还有点距离,但它图文并茂,又是说中国文化的事,学术委员会的任何一个人拿起这本书都能看懂。《中华文明史》四卷本,有200多万字,鸿篇巨制,而且全是中文,潘仕勋拿回去先要请汉学家看,拿出意见,再请学术委员会讨论,过程比较复杂。
汉学家看过之后,认为一、三、四卷都还不错,第二卷讲到了马克思主义史观,他们西方人好像不能接受。但我坚持,什么都好商量,唯有这马克思主义史观是不能改的。我们谈了很多次,最后达成一致,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同时,也介绍一些其他的史观,这样符合平衡的原则。我和作者袁行霈教授商量,他也觉得能接受。负责这个项目的剑桥大学的博士也特别兴奋,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南方周末:推广中国价值观的书是不是很困难?
吴伟:刚才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马克思主义史观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坚持,应该是我们的价值观,但是国外不能接受你只说这一个史观。这还是与我们非常友好的出版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
我们出版的小说,这几年比前些年数量要多,但效果都不是太好。比如说《狼图腾》,在中国这么畅销,英国企鹅的老板亲自拍板决定高价买的版权,十万美元预付款,这是中国第一本卖出这么高价的图书,结果虽然比其他中国图书卖得好,但比起在中国的畅销,距离大了点。原因就是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
像哈珀·科林斯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五年出版50本书,结果才出了两三本小说,卖得不好,他就不愿再继续出版。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传播中国文化的义务。他也许看着你的面子给你出几本,长此以往就不行。所以,中国小说到底怎么样能够传播,这是一个问题。
比如陕西作协开会,希望我去讲讲,如何让“陕军”走向国际。陕西的文学创作还是很厉害的,我跟国外的出版社谈,他们也愿意出版。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的作品,却没有人翻译,贾平凹作品里有很多陕西方言,我们说普通话的人都不大懂,外国人就更加不懂了。再比如阎连科的《受活》,2004年版权就卖出去了,到现在也没有翻译出来。为什么啊,人家不会翻,不懂你的方言。
现在,《于丹〈论语〉心得》也是卖了很高价格的版权,但是我也很难预测市场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难题,我们输出版权,不光是语言的对接,还有文化背景的对接,这就是我们的困难。
南方周末:电影是靠历史打国际市场,图书里的历史小说有国际市场吗?
吴伟:卖得不好。你坐在家里面想外国,你就想不明白,你认为应该是怎么怎么,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像《明朝那些事儿》,如果外国出版商愿意出,我们也愿意,但这不是我们一相情愿的事。
2000年我们新闻办在美国搞活动:“中华文化美国行”。记者随机在街边调查,问美国人对中国什么东西了解,对中国什么东西印象深,结果是一熊猫、二长城、三春卷。长城、熊猫吧,这毕竟是中国独有的东西,春卷是怎么回事啊,不就是街头小摊的食物嘛。这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些东西。
南方周末:在跟西方出版人的接触中,他们想买的书和我们想卖的书,这中间的差异大吗?
吴伟:差异应该说是在逐渐缩小。最开始他们的目光聚焦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上,包括那些古典的小说,因为出版那些图书没风险,不用费劲。
现在外国人很关心你的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关心的是威胁到它了,怎么遏制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他们和原来的中国差不多,你经过了这么三十年能发展成这样,他就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发展的。去年我去越南,越南人就对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有兴趣,希望能从里面学到点什么。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书太少,写得好的更加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