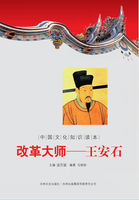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星期六的下午,在关望家里的纸牌游戏,正在如期进行。
玩牌的有四个人,依次是:老胡,李科,于在江,郑文,还有一个旁观者,应该是旁听者————那自然是盲人关望。
于在江今天的手气不错,他跟李科一伙,两人把另外一伙赢得没了脾气。他们玩的是抓百分,这种玩法不仅要求你会用脑子,还需要牌好,加上对家配合得好才行。让李科欣慰的是,那个平时总是玩不好的于在江今天比他还神勇,几乎成了牌桌上的无敌致尊。
大约在下午两点半左右,吴是非来了。吴是非神情沮伤,脸色青黄,右额头还肿着一块大包,宛如一只霜打的茄子。几个牌友一见到他这副模样,就止不住乐起来。你咋的了?让人煮了?老胡用刚刚从电视上学到的广告词来讽刺他。
吴是非不想让人知道他被女患者家属收拾的事,胡乱应付着:这两天走背字,我那二徒弟把人嘴给扎歪了,人家告到消费者协会去了。你说他妈的消费者协会管得着么?他一支牙花子:非要让我跟他打官司去,要不就赔他们一万元钱,我还怕他们?哼。说着就进屋里,跟关望闲聊去了。
几分钟后,李科进来跟吴是非打了个招呼,说有点事,让他去玩几圈,吴是非也就回到厅里。
吴是非并不想跟于在江一伙,李科空出来的位置却正在于在江对面,他就跟郑文换了个位置。几把下来,于在江的手气让几个人惊羡不已,因为是玩钱的,老胡和吴是非一下子就输了一百多。再看于在江前面,连零带整总也有三四百了。等李科回来时,吴是非和老胡已经写起欠条来了。一旁的关望劝大家和气为重,还是换种别的惩罚形式吧,别玩钱的急了眼大家闹得不愉快。老胡当即表示赞同,郑文和于在江也就顺口答应了。于在江去了趟厕所,回来后位置又被闲在一边的李科占了。
时间大约是下午四点,于在江又回到牌桌上,这次他与吴是非坐对家。于在江跟吴是非开始把另外一伙杀得大败,后来于在江又犯了老毛病,不是出错牌,就是露了底,再不就是光顾自己走脱,不管吴是非,结果玩到一局出郭,他们整整被老胡和郑文赢了一千分。
你们想怎么办吧?老胡不依不饶地说。于在江犹犹豫豫地说:算钱吧,是非,你说呢?
算钱算钱,那什么老于,你先借我二百。吴是非刚要从于在江那里拿钱,一把被郑文挡住。钱给不给另说,你们得受罚。
怎么个罚法?于在江似乎对处罚更关心。怎么处罚吗?很简单,老于你到地下室去一趟,这有钥匙,你到地下室里把他们放在小屋中的管钳子拿上来。老胡有些洋洋自得。你不是怕黑嘛?就这么着。
那吴是非呢?你们也不能光对我这样呀,这太不公平了。于在江表现出极大的愤怒。
那也好办,现在还能看到人呢。郑文朝窗外望了一眼,然后拍了拍吴是非的手背。你这就到天台上去站一会,就十分钟吧,不能耍赖哟。老胡替吴是非打圆场:你能行不?别没上去呢腿就先哆嗦了,你不是有恐高症么。
吴是非脸有点红,他朝老胡,于在江和郑文各瞅了一眼,那三个人都用鼓励的目光回敬他。吴是非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不就站楼上十分钟么,你们说站哪?
站哪呢?老胡想了想,前几个月咱们上去抓那个小偷,不是看到楼那边有个缺口么,有能耐你就站那去。他又对于在江说:你行吗?地下室里可挺长时间没灯了,借你个电筒吧,别把你吓着。
于在江又用征求的目光瞅了瞅吴是非,老胡和郑文,他们也正用鼓励的眼光回敬他。只要吴是非敢上楼去,我就敢去地下室。于在江轻声说。站在一边的李科早就不耐烦了,他拉拢关望也跟着起哄:有什么不敢的,你们就是胆小,锻炼几回就没事了,怕啥呀,这就是个心病。
于是几个人从关望家里出来,于在江拿起老胡的手电筒,坐进了下行的电梯。他的任务很容易检验,一见到管钳子就算胜利。至于吴是非嘛,郑文老胡和李科都想亲自见证一下,于是四个人都上了天台。
果不其然,吴是非刚一上去腿就软了,他脸色煞白,浑身颤抖,一个劲地告饶。几个人都想看看他的丑态,所以一会言语讥讽,一会讪笑连连。他们更是拿于在江做比较:你还不如那个胆小的老于呢,再往前走,站到楼边上去。对,只管往前走,别朝两边看。往前走,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走吧,去吧。他们鼓励着吴是非,还不断地指挥他怎么怎么做。在众人的高呼低喊中,吴是非终于站到了那个缺口的边上,他想把手按住旁边那个水泥石灰台,这样既可以防止脚下发软动作扭曲,也可以让抖动劳累得双腿稍微休息一下。他做到了,一种凌空欲飞的感觉让他轻飘飘的,他不想往下看,可往下看的想法一刻不离地勾引着他。其实他的眼睛始终在眯缝着,生怕什么小虫子飞进眼窝似的,现在他大睁双眼,觉得世界一下子变得奇大无比,一种荡胸生层云的爽快迅速占据了那颗久已郁闷的心。什么离婚的困惑呀,什么诊所里的繁杂琐事呀,什么乱七八遭污秽不堪的滥女人呀,什么神医秘方专治男子性病的神药呀,在那一瞬间都统统不去想了,那感觉真的很奇怪,是一种尽乎彻悟的解脱和超越。
吴是非的脚向前挪动了一小步,也就几寸远吧,他觉得他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本能地看了一眼,在鞋尖上有一个锃亮的东西,是一枚图钉。那是什么呢?他想,那是一枚极普通的常用的图钉,它怎么会在那里?他又想。那会是谁的呢?谁把它放在这么高的地方?他刚一这么想时,腿就不太好使了,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把那鞋上的图钉用力一甩,一个亮点就飞了出去。他又往前迈了一小步,他觉得他必需这么做。
半小时后,从地下室里哆哆嗦嗦爬上来的于在江感觉到有什么不对,有许多人正从楼上下来,还叽叽呱呱地议论着。他扯住一个人问:怎么了?
那人告诉他:有个人跳楼自杀了。就在楼后头,好象是从楼顶上跳下来的。
那人不再理会他,而是匆匆忙忙地跑去看热闹了。他呆在原地愣了一会,然后默不作声地反问自己:就这么完了?他把手里举着的管钳子用力挥了挥,又在心里骂了一句:可不完了吗?这个早就该死的王八蛋。于希,爸爸给你报仇了!他用力挤了挤自己的眼睛,很疼,但是没有一滴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