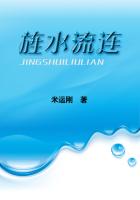阿吉打电话来,阿吉是旧时的一个同学。他说他找到了阿文的手机号,匆匆来告诉我。
“那么,你和阿文联系了吗?”
“没有。我一知道就来告诉你。”
“是吗?你也不试试,能打通吗?”
“能打通吧,号儿是从阿文的哥哥那儿找来的。”“好的,我会找时间和阿文联系的。”
“嗯”
放下电话,虽然有一阵的恍惚,但还是意识到该去做晚饭了。晚上是准备烙饼的。
烙饼的时候,还是想着阿文。
那时,我们年少,好像一群春天里的土拨鼠兴奋地谈论着夏天的原野一样,我们热切地盼望着未来,就好像未来的五光十色已经绘在了我们的身上。
尽管那时我们都在学着齐秦的声调唱那首《外面的世界》,尽管在那歌声中,我们不仅听到了精彩,也听到了无奈。但是我们依旧盼望着。
高中的生活是单调的,单调依然美丽。
清晨走进教室,是单调地朗读,但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喜欢朗读了。当然,阿文比我读得好。
课间有广播体操,我总是很认真地完成每一个动作,就好像现在花钱去健身。同样,阿文还是比我做得好。
中午我们会夹在嘈杂的学生群里,大声喊着说再见。
最美好的时间在下午,因为下午我们会有很多的自修,而且还有一个课外活动——这个课外活动时间一直被我们的班主任保留到了高中毕业。我和阿文会绕着操场跑步,边跑边聊,边聊边笑。
偶尔,我们还会在一个有着阳光的下午,偷偷地跑到学校背后的小山上去,躺在农人弃在田地里的麦草上,看草、看树、看浮云,谈着各自的理想。
是的,那时我们是有理想的。
阿文的理想最美,是要做播音员的,还要写文章,写属于自己的文章。
比起阿文来,我显得很笨拙,除了喜欢物理实验室以外,我只知道考学是我仅有的出路。
就在那些个美丽得似乎可以抓得住的日子中,我们的友谊慢慢地生长,一转眼就亭亭玉立了。
高考终于来了,是的,是终于来了,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恐惧。我们相约去看考场,去熟悉那被誉为是我们的战场的考场。一路上我们还是说着笑着,而且约定着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友谊决不会因为高中的结束而结束。
这是我们的约定,是我们年轻时候的约定,是见证了青春年华的约定。
高考,一座独木桥,我们很幸运地挤了过去,只是,理科考生的我们,一个去了英语系,一个去了历史系。
人学以后的深秋,阿文给我寄来了信,英语的,我开始逐字逐句地翻译,很吃力,因为那时我正在啃《古文观止》。
我们的信就在英语和古文之间行走了三年多的时间。其间,会在一个很热或者很冷的时候,中断,添加一些欢声笑语。
就在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可以进入一个自主的、自立的、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突然地就断了联系。
断了联系,就好像当年约定友谊时一样,自然极了,没有一丁点的别扭。之后,谁也没有再找过谁。也正是这一点,让那些旧时的同学很不解。
其实,到现在我自己也不能解释什么,也许真的就是一种冥冥中的直觉呢。
不知道,阿文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解释。
后来的所有关于阿文的消息都是从别人那里知道的。
听说,阿文去了深圳,那时的深圳,是刚刚起步的特区。
听说,阿文辞去了工作,开了公司,那时的公司是刚刚兴起的产业。
听说,阿文结婚了,夫妻双双去了新加坡,因为那里有产业。
听说,阿文离婚了,回来了,自己带着孩子,孩子长得很像阿文。
现在又听说,阿文开了两家洗浴中心,做得很大,很漂亮。
都是听说,我已经厌倦了,但是我又不能让自己放过每一次听说的机会。
不知道岁月在我身上涂上痕迹的同时,是不是也会让阿文改变?不知道时间让我后悔了当年联络中断的同时,是不是也让阿文有了些遗憾?
不知道家庭生活让我学会了居家打理的同时,是不是也让阿文适应了家的琐碎与零乱。
不知道。
但是有一样我是知道的,阿文不会恪饼。她说过,想吃珞饼的时候会想起我。
真希望现在阿文可以想起我。
锅里的饼该翻个儿了。
2004年3月。一线黄土山,驮着多半个太阳,橘红色的,映红了天边的云,山也更加黄了。小河泛起阵阵金色的涟漪,树梢晃着。夕阳落着,只剩下了小半个身子,仍在探寻着这条小街,一条铺着小石子路面的小街。这是记忆中的一道风景,很美,好像阿文一样。
小涵姑娘
凑巧得很,最近总是有小涵的消息。
离开原来的单位,也就离开了一些人,一些很投缘的、称得上是朋友的人,还有一些不很熟知的、只有点头之交的人。小涵和我只有着点头之交。
小涵毕业分到单位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孩子,碍着年龄和经历,我们只是客气地打招呼,客气地来往。
最近的关于小涵的消息不是很好,说是小涵结婚了,但又生病了,怎么会这样呢?
说实话,小涵给我的印象还是蛮深的。刚来的时候,小涵胖胖的,丑丑的,是啊,一个刚毕业的女孩子,被人这样形容是很遗憾的,小涵也实在是显得有些孤单。
我和小涵共事的时间不长,很快我离开了那里,而小涵还留在那里,一直到现在。
小涵的恋爱过程也不很如意,这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打击,谈了一段时间而且感觉还不错的男友到单位接她,见到小涵和其他的俊男靓女走在一起时,就和她散了。为此,小涵伤心了很长时间。
小涵知道自己的容貌,但是长期以来的学校生活并没有让小涵为此伤神,然而此时,我想小涵是彻底地伤心了,不然她不会疯狂地减肥。
小涵减肥是在我离开那里以后的事情,听说,是到了几乎不吃任何主食的地步。减肥是很见成效的,瘦了以后的小涵我没有见过,也只是听说,似乎好看了一些。
后来的事情不很清楚了,反正是结婚了,在去年的冬天。
可是,结婚不久的小涵就住进了医院了,进进出出,反反复复。
在断断续续的关于小涵的消息中知道,她的病是因为减肥弄的。
听说最近她又病了,我想也许我该去看看小涵的,带一束健康饱满的马蹄莲。
2003年夏天。
阳光中的逝去
窗外艳阳一片,天空中连一片云彩都没有。空气被太阳烤得炙热,无论盛开的鲜花,还是灰调的楼房,一切都在这空气中静置着,没了生的讯息。
十年前的初秋,那时,我第一次,是的,是第一次接触到死亡。她,我的同学的同学,一个善良的女孩。记得她到我们宿舍来玩,我还为她吹过头发,她的头发软软的,有些黄。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们宿舍的女孩都是那么喜欢她。她是师范学校的,然而就是在那年的教师节的早上,她被从那深深的美丽的南湖的水中托了出来……在那天晚上,我们宿舍的女孩都为她,那个只走过了二十春秋的她写下了深深浅浅的文字。那晚,我看着天上的星星,数呀数呀,奶奶说每个人都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如果谁死了,那么天上就会有一颗星星落下来。可是,我终于也没有数清有多少颗星星,也没有看见有星星落下来。
那晚,我哭了。
年轻的岁月很容易带走以往的忧伤。然而……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我的外公去世了。外公是一个农民,一个吃苦耐劳的农民,他不仅养大了六个孩子,还为六个孩子的孩子来去奔波。我出生以后,妈妈没有奶水,饥饿的我在死亡的边缘啼哭。外公为了有钱给我买吃食,他挑着自己做的豆腐翻山越岭,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儿,有时一天要走上百里路。豆腐换成了钱,钱又换成了奶粉,奶粉喂活了我……与其说是奶粉喂活了我,不如说是外公的汗水喂活了我。
外公去世的消息妈妈一直没有告诉我,也许妈妈是怕我一人在外,伤心了没有人安慰吧。其实,当我知道了以后,我感觉到的是―种恐慌,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我害怕,自此以后,我的那些至亲至爱的人会一个一个地离我而去。很久以后,跟妈妈谈起这件事,妈妈很伤感,但她却说我是杞人忧天。我知道那是妈妈用她的方式安慰我。
我结婚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带着我的孩子,去看望我的爷爷奶奶,屋里屋外的人都说可真是好啊,四世同堂。人们赞美着,我们幸福着。
爷爷、奶奶在几年以后相继去世了。再回到老屋时,我注视着二老的遗像,呼吸着尘土的气息,品尝着泪水的滋味。我搜寻屋里的每一个角落,想找回童年的影子,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童年已经跑得无影无踪,所能浮在眼前的只有黄土坡上我的恸哭,红色的棺木在黄色的土地上显得那么的不真实,满堂的儿孙离得咫尺之遥,可是谁也无力牵住他们离去的脚步。那时,我昏倒了,同来的人手忙脚乱地摇着我叫着我。事后,有人说按迷信讲,那是爷爷、奶奶舍不得我。真的,我宁愿相信那是真的。
今天,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楼下正摆着长长的一排花圈,那些花圈在强烈的太阳光底下,显得也是那么不真实,那么刺眼。去世的人我不认识,听说是个女的,是个三十岁的女人,她的孩子五岁了,在老家。“孩子很可爱”,见过的人都那样说;“孩子真可怜”,今天的人都这样说。院子里安安静静,没有哭声,不像其他的丧事。听说她的妈妈得了癌症,她的婆婆有严重的心脏病,这事没有告诉双方家里,所有来的人都是同事和朋友,可以看得出,他们把泪流在了心里。真不敢想那失去了女儿和儿媳的两位老人知道后是怎样的难过。没有听说她丈夫的情景,我想那是人们不忍心谈论那个男人的悲伤吧,那会是怎样的心痛,我不愿也不敢想。听说那张遗像中的她笑得很美……
1999年初夏。
我是怕死的。
——我这样说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说,
那是因为我还年轻,有太多的东西割舍不掉。
我说,如果我死了,我希望有朋友可以常常想起我,念叨我。
——我这样说时,有朋友说我口无速拉,钆讲诂。
我们的传统中,对于死,是忌讳的,
于是,我们把思念都埋在了心底,生根也好,繁衍也好,但最终是不能让它发芽,这真的是很不忍的事情啊。
因为思念
那一晚我睡着了,睡得很沉。
我看见奶奶走了进来,奶奶来告诉我说她要一把伞,可我分明看见她手里拿着一把伞。
那是老历的十月初一,奶奶是来看我的。
自从奶奶去世以后,我很少梦见她,有时候,在临睡前,我会仔细地想上一会儿,希望我能看见奶奶,可是,每次我都会失望。而那个晚上我看见了奶奶。
自小和奶奶在一起,我身上有许多痕迹是奶奶留给我的。可我又真的不知道那是些什么,反正别人都这么说。
听说奶奶吃过很多苦,很能干,可是,我记得奶奶总是有些臃散,她告诉过我她是大家里出来的。奶奶对我很好,可是现在我也几乎想不起来那些个好是什么了。不知道,会不会在有一天,我会把奶奶忘了。
记得奶奶以前是抽烟的,一种叫黄金叶的烟,烟总是在手上,好像从不离开,但是,后来奶奶把它戒了,因为奶奶得了哮喘病。每到冬天的时候,奶奶就会用大量的时间躺在床上,然后告诉我怎么踩到一个発子上去抱下来那个装着饼干的罐子。我还一直记得那个罐子,是个瓷的,有花,奶奶去世以后,我没有能找到它,要不,我会抱走的。奶奶在冬天很少管我,总是希望我爸能早点儿来把我接走,总是说到了冬天我就不听话,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之类的话。于是我喜欢夏天,夏天的时候,奶奶可以给我做好吃的炸酱面,尽管,我也会偶尔想起那个装着饼干的罐子。
奶奶戒了烟,后来又用一种针灸的方法在夏天的时候治哮喘病,身体慢慢地好了起来,甚至,在冬天还能坚持她的那一套甩臂健身法。只是,那时候,我巳经不在她身边了,我上中学了,回到了我的父母那里,奶奶也开始带她身边的另一个孩子姑姑的女儿了。于是我不再是她的唯一,她还有了另一个,现在,这个小表妹也上了大学,偶尔会在星期天来我这里,我很高兴她来,并和我说说我的奶奶,她的姥姥,我的祖母,她的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