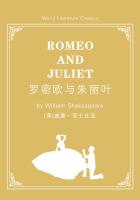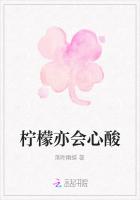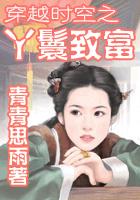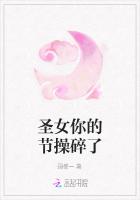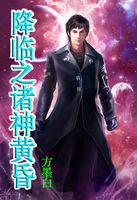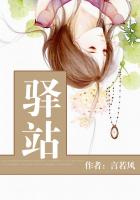上学的时候,能够得到老师的认可,多半归功于我记笔记的功夫。十多年前的大学里,教材是匮乏的,大多数的课程老师用的都是讲稿,课堂上学生们的一项主要的任务就是完成笔记,而我的笔记一向被认为是很好的。
可是,面对先生,我知道了自己的肤浅。
也许是厌烦了笔记本的呆板吧,我的笔记用的是散张的白纸,一页一页的,摞在一起包在更大的一张挂历纸中,自以为很自由洒脱。
课程结束的时候,先生要检查我们的笔记,这已经是例行公事了。我把积攒的厚厚一沓儿白纸交了上去,等待着也许这位先生会表扬我呢。
应该是一周以后的事情了,笔记被一个同学从先生家里带了回来。我的呢?那个用大大的挂历纸包着的笔记不见了,一个新的面孔呈现在我的面前。白纸做的封面,白纸做的封底,黑色的上了胶的鞋带儿装订在左侧,还有先生的字——古代印度文化史笔记,就连我的名字也被先生写在了封面的下角。
有些迟疑,不,是有些忐忑,很小心地翻开我的笔记,几乎每一页上都有红色的字迹,要么填上我漏掉的字,要么改正我写错的宇,甚至是我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
那一瞬间对我的触动深深地印在我思想的深处,融汇成了一种感动,而且随着生命历程的延续,这感动不断地变得凝重,渐渐成为一种态度,一种生活的态度。
2003年春末。
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使用“先生”一词,记忆中“先生”和“老师”的称呼是有不同的。没有浮华躁动和做作,有一种固守、坚持、沉浸、春风拂面的感觉,这种状态真好!
风的作业
离开教室的时候,风的心里充满了愉悦。
老师要求大家去做一个参与式观察的作业,观察在晚上七点半至十点半的时间段里光顾酒吧的人,其身份情况,伙伴情况,消费情况。
虽然只是个作业,但这为风去酒吧提供了一个再正确不过的理由。
风其实很喜欢酒吧的那种气氛,柔柔的灯光,淡淡的花香,轻轻的音乐,静静的呢喃,一切都是那么完美,还有传统的红酒,或者哪怕是一杯果汁,风是不喜欢那些怪怪的叫不出名字的鸡尾酒的。甚至,风还幻想可以燃一支烟,带人些缥渺的感觉。
但是风的先生是不喜欢酒吧的,这一点在风的面前,风的先生表现得很坚决,不像平时事事对风迁就。也正是这样,风的两次酒吧之行,都是在百般纠缠之后由先生陪同的,尽管灯光柔柔,花香淡淡,音乐轻轻,呢喃静静,但是,风总觉得在先生焦急的目光下,那红酒的味道不很诱人。
而今天,今天的作业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老师说了,这次作业要单独完成,为的是避免观察者之间的相互干扰。多好!风有了单独去酒吧的理由,就算是带着任务,而且被作业严格限定了时间,但是,毕竟这是一件倾心已久的事情呀。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日子了。
风的手机响了。听完电话,风的笑容更加灿烂了——风的先生告诉风今晚有业务,要很晚回家。风决定了,就在今晚吧。
时间这个时候走的是有些慢了,风想。一切都准备妥当以后,风到了“昨日重现”的门外,这里是风心仪已久的地方,咖啡色的门窗,套着纯白色的框,就和风心中勾画的昨日小屋一模一样,还有线条简单的窗棂、低垂的窗幔,都是风喜欢的风格。
七点半,风准时地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但是有良好视线的座位,把身体陷进软软的沙发,风轻轻吁了一口气,一杯红酒在手,荡漾开来,悠然自得。
风开始做作业了。
右边较远的地方,藤椅围着的桌旁坐着四个人,两男两女,年纪三十岁上下,统一的西服套装,两位女士也不例外。他们谈话的声音听不到,偶尔会有一两声笑传来,四个人轮流接听着一部手机。风想看来他们是老朋友了,而且还有着共同的朋友,大概是同学吧。他们的桌上是红酒。
还是右边远一些的地方,沙发里有三位男士,三位男士的穿着很休闲,桌上摆的是扎啤,刚才风已经问过了扎啤的价格,知道今晚这三位男士的消费不会低了。
左边是临窗的,只有一桌坐了两个人。他们,有二十岁了吧,或者还不到,女孩抱了一杯果汁,男孩呢,背对着风,风没能看清楚。女孩总是说着说着就低下头,玩弄那只装果汁的杯子,很羞涩的样子。风认定他们是两个正要涉足爱河的少男少女,有一些青涩,也有一些向往。
风的座位对角一端有五个,不,是六个人的一桌,他们的声音最大,在打牌,风不喜欢他们,也就不愿一再看他们了,幸好他们离风还算远。
天越来越黑了,酒吧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风每隔十分钟一次的实地笔记也密密麻麻地记了不少。一边记着,风一边在想着什么:原来来酒吧的人不少呢!都市的气息是不是这夜晚酒吧的气息呢?怎么没看见只身来酒吧的人呢?看来先生说的还是对的,哪能像我现在这样只身坐在酒吧里呢?
想着想着,风有些坐不住了,尽管是坐在一个幽暗的角落,但风现在觉得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看着她,似乎她成了所有人的观察对象。
离开的念头越来越强烈,风叫了买单。
服务生笑容可掏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风的单。
风的眼睛一亮,不是看服务生,也不是看单,风看见了跟在服务生后面进来的新客人。
风又叫了一杯果汁。风想留下来,但是不想失态。
新来的客人一男一女两位,坐在了仅剩的一处别无选择的空桌旁。风细心地观察着,那位女士的笑容浅浅的,像是浮在脸上,在柔柔的灯光下,若隐若现。借着桌前的一株棕榈树,风知道自己的观察可以是肆无忌惮的。
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只见那位女士很优雅地低头、抬头、笑和皱眉,不时地用手指拢过眼前的发。
风就这么远远地看着、看着。
女士侧身翻包,男士也开始翻包。一闪,打火机亮了,男士熟练地为女士点燃了手中的烟。透过刚才打火机的亮光,风看见了美丽女士的手指亦是芊芊的美丽,连着玫红色的指甲。
风的手很漂亮,认识风的人都这样说,还说风的手是很有福气的那一种。风的指甲是修长的,但是从不涂指甲油,因为先生说涂了不好看。
风也会抽烟的,可这只有风自己知道,在绝对的一个人的时候,风会自己点燃一支烟,看袅袅的烟飞升,看落落的灰飘散。风的先生没有抽烟、喝酒的嗜好,这一直让风感到欣慰,毕竟烟、酒伤身的。
风的思绪一下子跑得很远,眼前的一切似乎也就成了空白。风抱着那只装果汁的杯子,忽然想起了那一对儿少男少女,目光寻去,那里已经换了客人。一阵沮丧袭来,这作业做的,连观察对象走了都不知道。
风看看表,这是风第几次看表了?终于是十点半了,作业时间到了,可以准时离开了。可是风知道这个时候是走不了的,因为风的目光一直就没有离开过那对男女,也不可能离开;因为风的腿有些酥软,尽管第二杯风叫的是果汁;还有,风的泪未干。
在风的观察笔记中,有这样一些文字:
实地笔记——男一女,三十多岁,衣着考究,笑容浮动,开启一瓶红酒。
个人笔记——先生今早出门的时候穿的是这身衣服吗?
方法笔记——角落,静观,有泪。
2003年夏,因为写作要求,费了些心思。
风的电话号码
晚上的时候,风才醒过来,风是真的醉了。
上午,从很远的地方来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也疏于联系,突然的造访让风多多少少有些吃惊。
来的朋友名字叫书,但是和风在一起的时候却是一个从不愿读书的人,尽管当年读书就是他们那帮子人的天职。
书仍然像当年一样随意,随意地喝着风为他沏的茶,随意地与风聊着现在的工作、生活和过去的时光点点。
风很好奇,询问书是怎样找到她的,对这个问题书也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是啊,怎么找到你的,连我自己也纳闷儿呢,你十年前的电话居然没有变!”
可不是嘛,风的电话自开通以后就没有变过,十年了,尽管家搬了一次又一次,尽管手机接二连三地换,但是这一部固定电话真的是没有变过。
书还在感叹着:“要找你太容易了!”
“嗯。”风也这样想。
就像喝茶一样随意地,书提到了另一个名字。另一个名字在风的心里咯噔一下,停住了——林——这是十几年以后第一次听到吧。
书喋喋地说着关于林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有十几年前分配时的机遇,也有今天一帆风顺的仕途。
风静静地听着,偶尔起身为书续上茶水,并报以认同的微笑。
“还记得那个没回家的假期吗?”书像是在问风,又像是自己问自己,因为在那个时候,每个假期,风都是规矩地往返于大半个中国之间。
书谈得很尽兴,“那个假期,我和林都没有回家,那小子动不动就闹失踪,我问他是不是处女朋友了,他还竟然敢说没有!”
“他不是毕业以后才找的女朋友吗?”
“哪呀,毕业以后才找,他能有那么好的运气?只不过那个时候,无论是他,还是他找的那一家儿,都不希望公开罢了。”
一片落叶从窗口飘了进来,风的窗前有一株丁香,总是在五月绽放清香,而在这个秋季里挥洒别情。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那个电话保持了十年吗?”风像是在问书,又像是自己问自己,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想着等待书的回答。
风想起在临别的时候,林的话一现在也不可以吗?为什么要一直拒绝我?
为什么要拒绝林呢?也许从来就没有为什么,就好像风这么久地留着那个电话号码一样,从来就没有为什么。
随后的午宴上,风喝了酒,喝了许多酒,酒后的风也只是去睡了,睡到晚上才醒过来。
2003年9月。
小颜的婚亊
小颜和小良是我的学生,他们明天要结婚了。
他们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和我们家来往很多,渐渐地也就成了我们家里的常客,也就成了我们家先生和孩子的朋友。
小颜长得很清秀,有着南方人的俏丽,而且很能干,正所谓是心灵手巧,但说着一口不很标准的普通话,这一直是我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我曾信誓旦旦地许诺,要教会小颜说普通话,但是我的力量实在是抵不过她生长生活了十多年的那片土地。并且,从她身上我总结出了南方人说普通话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不会儿化音,只要一碰上儿化音,她的舌头就不再灵巧了。
小颜很会做饭,而且是喜欢做饭的那一种,住单身的时候,就置办了一整套厨房用具,开始了津津有味的厨房生涯。这和我很不一样,我喜欢的事情,往往都是不现实的,比如说流浪。这不仅让我有时候很羡慕她可以静下心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态度,我是应该实际一些的。
小良在学校的时候,属于那种女孩子很喜欢的男生,不仅长得很帅,而且很会讨女孩子欢喜。但是对于小颜,他很是全心全意,小颜也正是因为小良的爱情才留在这座城市的。
十一前,两个人来看我,告诉了我们他们的婚期,并且说结婚的时候,想让小颜从我们家里嫁出去,也就是说要把我这里当做娘家。说这话时,显然他们有些紧张,大概是怕这要求不合适吧,但是我却是很高兴的,很高兴他们能这样看待我们的关系,尤其是小颜,我很愿意她可以把我这里当做是娘家。
小颜是湖南人。
她真的是因为爱情才留在这座城市的。
我收拾着家里的角角落落,孩子的零零碎碎,想要在明天的时候,让小颜感觉到这是一个整齐温馨的家。把那一盆晷花从阳台上搬到了屋里,细细地擦拭着每一片绿叶,希望这深秋的绿能够给房间里更多一些生机。
明天,小颜就要走上人生的另一段旅途了,小良,也不再是她的男朋友了,应该叫做丈夫了。丈夫,这个词有着多深的意义,担负着多重的责任啊!
以前,总觉得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跟随生活进人婚姻以后,我才慢慢地体会出了更多的东西。婚姻,简单地来讲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又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是两个家庭的事情,或许可能是两个民族的事情,甚至可以是两个国家的事情。这让我又想起了文成远嫁的故事。
我把核桃、红枣、苹果、花生装在盘子里,仔细地检查着小颜明天要带的东西,小心地把大红的喜字儿贴在花瓶和镜子上,自己心里也充满了这些吉祥物品带来的幸福的感觉。
一边做着这些事情,一边和先生回忆着当年我们的婚礼。
希望明天艳阳高照。
2003年10月,那个秋好美。
花花
花花属狗,而且生月小,所以从小一起玩儿大的朋友都叫她“狗尾巴花”。习惯了,倒也觉得顺耳。
今年过年,花花依然很安静,安静得像老祖母膝盖上的那只猫,那只猫也很老了,老祖母说它老得像七十岁的自己。
最早,在花花刚离开家的时候,每到过年,花花都盼望着回家,尽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是,回家在花花心中还有着另一层用意,她可以把爸爸栽的满院子的米兰捎一株回来,让自己的单身宿舍香气宜人。
可是到了后来,花花开始害怕在过年的时候回家了,因为自己的婚事成了家里过年时的全部话题,尤其是在小两岁的弟弟结婚以后,花花开始找借口避开在过年的时候回家,可是,没有一次可以成功,不仅因为家中的盼望,而且,还因为花花也在念着那些米兰。
自从三十岁的生日过了以后,为花花张罗介绍男朋友的人渐渐地少了,稍稍熟悉一些的人会皱着眉头,但是让人感觉是很温馨的抱怨一一花花呀,你到底在挑什么呀?
是啊,花花想挑什么呢?如果说,二十岁的花花在学校可以算得上是校花的话,那么,三十以后的花花可就没有了年少的资本。
面对别人的探寻,花花只是一笑,一笑足以。也只有花花自己知道自己这是病了,这病就从那米兰的花香中飘出来,虽然清淡,却久久不散。
青春短暂吗?其实真的不短,这不,花花的回忆一下子就回到了二十年前,二十年,真的不短。
那时正在读中学的花花是出名的好学生,也许所有的好学生的标准花花都占全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花花知道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是不允许的,那就是她在和石头来往。
大家都叫他石头,石头,是在学校的要求下,让家长领回去的,因为打架的时候石头打破了另一个学生的头,那个学生的爸爸是市教育局的一个什么头头脑脑。
那是高一。
在街上溜达了一年多,石头参了军。
集训之后,石头被分到了特务连。为了这个“特务连”,花花没少笑出声来。
再后来,要打仗了,是真的打仗,不是演习,去老山,老山一一在那个时候,不是地名,是个概念。
石头跑回来一次,对花花说,等我打仗回来,就去考军校。
什么时候回来?
米兰花开的时候。
米兰花开了,开过了千朵万朵,开过了春夏秋冬,开过了微笑与烦恼,开过了花花的大学四年,开过了湿的枕边、红的眼角,开过了花花从江南到北疆的每寸旅途。
在米兰的芬芳中,花花记住了一个词:英雄。
——等我打仗回来,就去考军校。
——什么时候回来?
——米兰花开的时候。
也许这可以算是一个约定,也许,这什么都不算,是不算数的,可是它成了花花心中不解的情结,它让花花漫步安静的青春,却不忍离去。
盼望着,花花可以走出米兰花开的时候。
2004年2月,春节之后,寂静中。
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