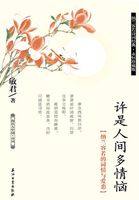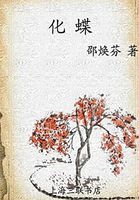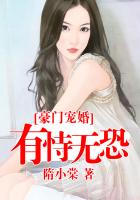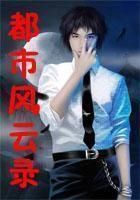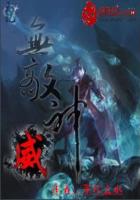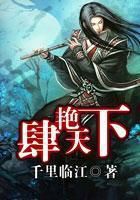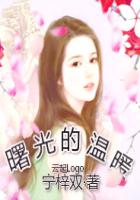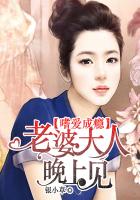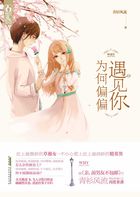正午,云雾散尽,四周重峦叠嶂。从山巅向南俯瞰,洮河犹如一条绿色的飘带,弯弯曲曲,伸向远方,两岸郁郁葱葱,给苍茫的西北髙原注人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再回头向北看,远处的山野清晰可见,可近处的兰州城却被灰蒙蒙的烟雾笼罩着,什么也看不清,那穿城而过的黄河和两岸的城市新貌,都隐藏在烟雾之中。这一清一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虽值夏天,可八楞山却凉爽宜人。满山遍野的青草给八愣山披上了鲜艳的衣衫,山坡上的羊群如朵朵白云,在山花烂漫的草地上飘动,山脚到山腰的层层梯田,把沟壑纵横的黄土髙坡,装饰得整齐、自然、美观,那块块长满五谷的梯田,记载着八榜山历史的变迁,也记载着生活在这大山里的人们的勤劳、朴实。在楞山观云雀的精彩表演,特别有趣。蓝天下,离地面数百米上下的空间内,无数的云雀扇动着翅膀在高空飞行。起初,只见许多云雀悬在空中不动,忽然有一只云雀叫了起来,顷刻间一呼百应。清脆悦耳的鸟语像在开讨论会,也好像为我们这几个闯进它们生活的领地而焦虑不安,商议着如何对策。空中的云雀突然停止了喧哗,有几只云雀从空中垂直掉落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滚了几个跟头后一动不动。当时,我以为这下子至少也被摔昏了,便跑过去捉它,可想不到距它只有两三步时,它便敏捷地飞走了,几个回合下来,把我累得喘不过气来,却一无所获。
在八愣山,只要有自然村的地方,就有山泉。下午2时许,我们下山到一个名叫马家的小山村,住着30来户人家。村子周围和山沟里生长着很多树木,多为杨树、柳树、榆树、杏树和苹果树等。离村子下方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山泉,泉水清澈见底,一串串珍珠般的水泡从水底冒出水面,在阳光下闪烁着银色的涟漪。我用山泉水洗了一把脸,顿时,一身的疲劳一扫而光。我喝了几口山泉水,只觉得比城市里卖的矿泉水和纯净水的口感还要好,一股清凉直达心田。突然间我明白了,我喝的就是名副其实的没有污染的天然矿泉水。在这山泉旁,我感受到了山村的宁静、和谐和自然生活环境的美。
有许多五彩缤纷的蝴蝶在一泓清澈的水面上,环绕着山泉翻翩起舞,美丽异常。当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山泉时,一些蝴蝶追过来,围着我们上下翻飞,左右盘旋,好像在欢送我们。
关山绿韵
关山林场位于金城以南15公里处,西与永靖县相接。它的面积虽然不大,但名气却不小,这缘于山上有一座金花娘娘的大殿和一棵神奇的松树。
盛夏的一天,我应朋友之邀,又去了一趟关山林场。一走进林区,绿意便层层叠叠地绵延开来,似绿色的波涛在眼前起伏变幻,顿感山里山外断然有别。山里的空气新鲜爽洁,带着松针和树木的清新,一阵阵地沁人心脾,做上几次深呼吸,仿佛即刻洗去了身居闹市肺部沉积的尘土。在林间弯弯曲曲的小道上,洇着如细雨轻拂的湿润,沿路而上,曲径通幽,山花烂漫,鸟儿争鸣,景色迷人。愈往山的顶部走,愈觉得清凉之气通透全身。这里有泥土的芳香,有自然的空调,而这一切都是满山绿树碧草的功劳。
我的母校南堡中学,离关山林场只有5里路。在我就读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学生食堂做饭的燃料,全靠林场的干柴。所以,每学期学校都要组织全校师生去林场捡干柴禾。林场管理很严格,凡进人林区,都要有林证记得有一次,我利用一位堂哥在林场工作的关系,办妥了手续,有老师带队拾柴。我们在返校的路上,受到了护林员的严格检查。他发现有位同学的柴捆中有一根没有完全枯死的小树干时,说是学校违反了封山育林的规定,硬是不放我们走,那位同学和带队的老师怎么向他解释都不行,越解释,他批评得越厉害。无奈老师只好写了一封《检讨书》:“我们对学生教育不够,在林区捡柴时,拔了一棵半死了的树,今后决不重犯……”于是,护林员才放行了我们。
已经爬上山腰公路的朋友的一声高喊,把我从36年前的岁月中叫醒。我抬头仰望,已经到了松树岘。这里有传说中的仙姑金花娘娘在岩石上插下的烧火棍长成的一棵活松树,就挺立在光秃秃的岩石上。树的四周护着铁栏杆,紧贴山岩的树根似盘龙,或扎入石缝,或伸向6米以外的土壤中。树的下面是一条1958年大跃进时修的公路,由于当年炸石筑路,严重地破坏了山岩的整体性和树的根系,松树就慢慢地枯黄了。但使人欣慰的是,后经关山林场科技人员和当地老百姓的抢救及精心管护,原本就神奇的松树,奇迹般地吐出了嫩芽新枝,这也使这棵奇树更神了,引来了更多的香客和游人。发黑的树干的下半部分,像火烧过似的,树干上皱褶重重,刻满了岁月的沧桑。仰观树冠,只见松枝青青,向天空伸展着生命的渴望,那形,那态,如同黄山的迎客松。
相传,金花娘娘生于明朝成化四年农历四月八日,于明朝弘治六年农历七月七日在叭咪山坐化。祖籍为兰州榆中金崖镇人,寄居现兰州城关区井儿街,父辈为当时的绅士富户。金花为独生女,从小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金花伶俐好强,聪慧勤奋,虽为富家闺秀,但饭菜家事样样得心应手,且能识文绘画,缝衣制绣,深得左邻右舍、亲房和亲戚及好友的赞誉。当金花长到16岁的时候,父母将她许配了人,金花得知后闷闷不乐,不吃不喝,继而成疾。后经一道姑的点治,病是好多了,但金花却变成了另一种性格的姑娘,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没有了往日的勤奋好学,只是早起早睡,只去厨房烧火做饭,成天少言寡语。一天,婆家托媒人来商谈过门之事,金花从心里是特别的不愿意。就在那天晚上做饭时,金花趁家人不注意,顺手拿上烧剰的一根烧火棍和刺绣丝线,从家里出走。过了许久,不见金花端饭上来,父母家人就到处寻找,但不见金花,却发现一条红丝线挂落在厨房里,红丝线沿着屋院从门庭里出去,人们沿着红丝线寻找,红丝线到卧桥就断了。后来得知金花只身出走家门后,一直向西走,当走到崔家崖时,黄河滔滔,伸手不见五指。突然西南方向出现一道白光,于是金花向发出白光的方向走去。不知走了多少路,不知摔了多少跤,又累又渴又冷的金花昏倒了。当金花醒过来时,雨停了,太阳出来了,朝霞万朵,金光闪闪。金花环顾四周,才意到自己是靠在路旁的大石头边睡着了。金花看了看远处的村舍,宁神静气,坚定了信心,继续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行走。又走了一天,到天黑的时候,金花走不动了,便坐在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休息。正在这时,找她的人们追赶了上来,并要她回去成亲。金花对寻找她的人们说:我金花已成仙,不回去做凡人的事了,你们回去吧。来人不相信,就说:金花,如果你能把这根火棍插进石头里,让它活了,我们就相信你真的已成仙,我们就马上回去,你就留在这里。金花照着来人们的要求做了,不大一会儿,烧焦的火棍果然长出了新芽,活了。追寻金花的人们见此情此景,就立即回到城里,向金花的父母叙说了在找到金花后所发生的一切。后来,金花在叭咪山坐化,当地的百姓为了怀念金花,分别在叭咪山和松树岘修建了金花庙。金花庙建成后,广大民众求医问病,络绎不绝,每逢天旱无雨时,便去祈求降雨,有时还从湖滩到叭咪山求雨,人们用柳条编成凉帽,戴在头上,并赤着脚,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敲着锣,口里不断地喊着:“金花娘娘,大雨三场,小雨四场,粮食上场,丰收在望。”在我小的时候,还看到了这种场景。松树岘的金花庙,在“文革”时期被毁,现在的金花庙是近年来由民间捐款重新修建起来的。
在奇松神树的林区,经林场工人几十年的辛勤努力,栽满了松柏,长得苍翠,在山风的劲吻下,松涛阵阵。此情此景,使我想起了陆游的《松下纵笔》“陶公妙诀吾能会,但听松风自得仙”。
向北远望,金城兰州笼罩在烟雾之中。在干旱少雨的大西北,绿到这种程度,须经过多长时间的积蓄和酝酿,须经过多少次的百折不挠,这需要几代人的艰辛耕耘和多么坚韧的生命意志,才能一寸寸,一年年向着髙远的蓝天,不息地生长。
当我沉醉在关山的绿韵时,不由得对林场的护林员们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是绿色的真正播种者和守护神。
故乡的野菜
人过天命,喜欢怀旧。这种心情,使我常常追忆自己生活中的往事。
我的故乡在金城南面的大山里,祖祖辈辈是种庄稼的农民。托共产党的福,我才有机会走出了大山,在城里成家立业,享受着改革开放后带来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过去农民作为猪词料的或只能在灾荒之年拿来充饥的野菜,现在却登上了大雅之堂,居然成了筵席上的美味佳肴。每当我在应酬中品尝那些我十分熟悉的野菜时,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便会使我勾起童年与野菜的故事。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整个国家还没有从治理战争的创伤中缓过劲来,经济还不发达,尤其是在农村,生产力还很落后,再加上当时的浮夸风,使得农民的负担超过了实际所承受的能力。农民们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即使丰收年,在缴过公粮和爱国粮、卖过余粮和留够次年的种子后,留足农民口粮的政策就大大地打了折扣,一到春天,不少农户就陆续缺粮,青黄不接。也就在这个时节野菜帮助憨厚朴实的庄稼人度过了那缺粮少菜的日子。
初春的山野,凉风习习。然而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各种野菜,被春风唤醒,纷纷从地下冒出了嫩绿的新芽,夹杂在杂草中竞相生长。每天放学后,我就和村上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山野挖野菜。起初,由于我还不完全认识哪些是野菜,哪些是杂草,哪些是毒草,有时就把一些好看的宽叶植物,误当作野菜挖了回来。可我的慈母一点儿都没有责怪我的意思,相反她却一个劲儿地夸奖我做得不错,挖来的野菜数量多,还像老师一样,说明我挖回来的那些不能食用的植物分别叫什么名字。后来在一个星期天,母亲特意把我带到野外,一同挖野菜。现在想起来,母亲真是用心良苦,可谓是植物课的现场教学。在母亲的耐心指教下,我逐渐认识和熟悉了故乡的蒲公英等野菜,同时,我也逐浙认识和熟悉了铁棒槌等致人毙命的毒草。
故乡的野菜种类繁多,品种不少。最常见的有苦苣菜、苦根菜、蒲公英、马英子、猪耳朵、雀儿菜、茴条、野韭菜、野小葱、鲜麻、地娄子、地达、蕨菜、蘑菇和头发菜等。每当我挖回野菜被母亲做成美味端上桌时,我总是欣喜万分。苦苣菜、苦苦菜和蒲公英是最普通的野菜,也是山野和田地里长得最多的,缺粮的日子里基本上全靠这几种野菜度过。用这些野菜制作的紫水菜,清热解毒,很有特色看起来绿绿的,吃起来酸酸的,而且口感不错。用浆水菜做的装水面,还是陇上的一种有名的小吃。在我的老家,谁家的浆水做得好,谁家的小媳妇在村子里就很有面子。在麦收的前一些日子里,几乎要断粮那就只有不断加大野菜的食用分量。我记得那时家家户户都在做菜团子好的菜团子里放的是面粉,差的菜团子里放的是麦麸子。吃过菜团子后,肚子不饥心里饥,可顶不了多久就觉得胃里在咕咕叫了心里总盼望着早点放学,赶紧回家去吃饭。野韭菜和野小葱是味道最尖的野菜常常用来做包子吃,味道好极了吃过后数日不忘。用这两种野菜腌的咸菜,很有下饭和调味的作用,为咸菜里的精品。地达和头发菜均属菌类野菜,前者量多名贱后者稀少珍贵,多用来包包子吃珍贵得大都舍不得吃积攒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就拿到城里换回些钱以补贴生活或给娃娃们交学费。
蕨菜和蘑菇都是季节性很强的野菜,这两种野菜的共同特点是生长速度快,味道鲜美,但可供采摘的时间较短,蕨菜在春天采摘,蘑菇则在秋天采摘。在采摘蕨菜的时节,只要一到星期天,我就和小伙伴们相约,到八里以外的关山林区去采摘,晚上回来,各个人的背篼里都装满了鲜嫩的联菜。采摘蘑菇,出了村子一上山就有,但最要紧的一条是,要十分细心地辨别清楚所采摘的蘑菇是不是食用菇,千万不能把有毒的蘑菇采摘回来食用。否则,吃了后人会中毒,甚至死亡。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一年里,连野菜都吃不上了,那时我也吃过榆钱、榆树皮、还吃过用荞麦杆为原料制作的“代食品”。那一年,父亲患上了浮肿病。尽管如此,父亲仍然承担起了作为一家之长的责任。在我家的后山上,有一种薤切草,结的籽有点像髙粱。父亲采集回来后让母亲做,因过去没有人吃过它,父亲对全家人说:“这薤切你们先不能吃,我老了,又有病,不中用了,死了就死了,等我吃了没事了,你们再吃。”父亲是拿自己的生命在为我们做试验。父亲的话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刻骨铭心。这就是世上最伟大的父爱。
我的母亲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居家过日子的人,好强能干且人缘好。在那个年代里,真是太难为母亲了,但她老人家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始终是以乐观的精神面对艰辛的生活和困难。每年春夏,母亲就开始把采集的野菜晒成野菜干储存起来,准备在冬季里调剂着吃,以便多省下点粮食,保证在来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能够有粮吃。那时候,在我的心目中觉得母亲就是靠山,只要母亲在家,就不怕没有饭吃。在缺粮的日子里,母亲真不愧为是位“巧妇能做无米之炊”的当家人,她老人家用野菜做出的饭菜,各有风味。
就这样,野菜伴随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代。
故乡的路
有人说过,世上原本没有路,人走得多了,这才有了路。
出门就得走路,路是生活的希望,因路是连接外界的桥梁。出门在外的人,不论离家多么遥远,离家多么久长,也不论官职大小,生活贫富,可眷恋故乡的情感时刻在心窝里,游子们都在盼望着再一次踏上故乡的路。
我的家,在金城以南的大山里,十九岁那年,我就离家了,走出了那片土地,到世界屋脊的西藏服兵役,正式闯荡天下了。曰月如梭,时光飞逝,离家在外三十六年如梦一场,如今的我已成了老汉。然而三十六年来,故乡的爹妈、老屋、土炕、树林、清泉,还有那故乡的路,却像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着我。
故乡的路是沉甸甸的一部书、一段历史。在这一部书里,记载着这山里人的辛酸和欢欣,有说不完的传说;在这一段历史里,记载着那片山地的昨天和今天,有说不完的故事。
山里人就靠祖辈们一年年,一代代用脚踩出来的山涧小路,牵上骡马或毛驴,驮上生活的希望,出山,进山,艰辛劳作,创造未来的幸福。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山里人终以肩上的背篼,额上的汗水,脚下的布鞋和他们沉重的喘息声,把出山的小道拓宽为迈向小康生活的金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