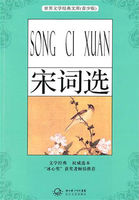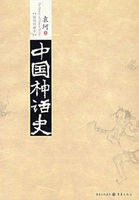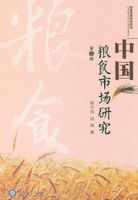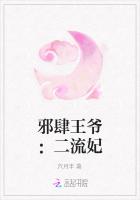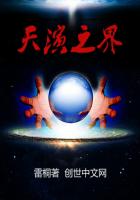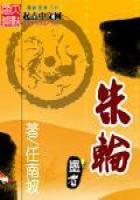我小的时候,故乡的路是些不起眼的土路,弯弯曲曲,髙高低低,伸向远方。在我上小学和初中的岁月里,几乎天天走在故乡的路上。那时候,我始终遵循父亲他老人家的教诲,一门心思地刻苦读书.立志长大了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光宗耀祖,报效祖国。为此,我踏着故乡的路求学,年年月月风雨无阻。我没有辜负家父的期望,终于有了那么一天,在全村父老乡亲们的欢送下,我披红戴花,骑上村上最好的马,恋恋不舍地离别了父母,离开了家走出了大山。
我记得第一次回家,那还是1971年的事了,当我办好手续领到探家的《军人通行证》后,兴奋得几夜难以人眠。我从边陲哨卡乘汽车经拉萨到西宁,再转火车到兰州然后步行五十多里的路程回到了家那时故乡的路依然如故。过了两年,我同妻子一起,费了一天的工夫,翻山越岭步行着回到了家,那时故乡的路已有了变化,原先的小路变成了架子车能走的路。
上世纪80年代初,故乡的路又起了变化。一条年轻的备战路通到了离我家5里地外的邻村,进村的路也修成了农机路,那一次回家,我们一家3口人是坐着城里外甥的拖拉机回到家的,这比起走路回家便当多了。80年代末,我从部队转业到刘家峡的一个企业里工作。从此,离家近了,回老家的机会和次数也就相对的多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故乡的路早已变成了简易公路,曲曲弯弯,平平整整,四通八达。村子里有经济头脑的人家,前些年就买回了拖拉机或三马子农用车接送村子里的人出山,进山。从而,彻底解除了山里人外出全靠步行的疾苦。
今年国庆节放长假,我和老伴及我儿他们小两口一行4人,又一次踏上了故乡的路回到了家。这次回家,我们一家人坐小车从刘家峡出发,经即将竣工的刘兰二级公路、7201号备战路和故乡的简易么、路,仅用了1小时30分钟就到了家门口。这又比以前坐拖拉机或三马子回家便当多了既快又省时。
我踏上故乡的路走进老屋,就会回忆起许许多多的往事,我离开故乡的路,返回单位,便会常常思念故乡的路。路的这头,是我供职的地方是我的新家路的那头,是养育我的地方,是我的老家。
清醇竹林
竹子,修长而挺拔,清癯而高洁。我喜爱竹子,见竹必驻足,必仰幕,转而就是悠悠退想,轻轻喟叹。
在我老家的园子里,生长着一丛翠竹,一米来髙。小时候听母亲讲,那竹是父亲栽下的,父亲爱竹。父亲在那丛竹子旁曾经多次对我说:“做人要像竹子那样,髙风亮节。要活到老,不拿别人的一根草。”父亲以竹教我怎样做人的话语,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受益匪浅。
遥想1968年,我参军到西藏后,就一直遵循他老人家的教诲,努力实践着。1978年初春,我被选调到成都陆军学校工作,当我看到四川盆地到处生长着茂密的竹子时,兴奋极了。学校位于川西盆地的边缘,有山有水,老百姓的房子周围没有院墙,多为翠竹围屋。学员在野外演练战术课目,大多在莽莽苍苍的竹海里进行,竹林所散发出来的清醇气味让人陶醉。这里的山,这里的竹,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山是竹之榻,竹是山之发,相互依假,融为一体。为赏竹,我专程去了成都的望江楼公园,在这个以竹为特色的公园里,栽种了各种竹子。有高大挺立的毛竹,有高不盈尺的菲白竹、有竹节呈龟背状的龟背竹、有节间大如佛肚的佛肚竹、有斑斑黑点的斑竹、有绿底黄纹的花毛竹、有叶大如帛的箬竹、有叶细如柳的大明竹、有英俊挺拔的楠竹……徜徉于竹林间,如入幽静脱俗之境,竹的气息又一次令我有种说不出的快意。
竹虽无梅花之俏丽,也无青松之雄奇,但竹有竹的品格,竹有竹的气度。它坦然、正直、潇洒、坚实、清雅、古朴,尤其可贵的是,无论经历多少恶风苦雨,竹子总是不卑不亢,它始终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枝横云梦,叶拍青天,此为竹的精神。故苏东坡居士不得不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还有人说,竹的瑟瑟之声与读书的朗朗之声,最为合拍,也最为和谐。难怪蜀中的最高学府四川大学就与望江楼公园仅一墙之隔。
1987年,我转业回到了故乡,自然也就少有机会看到碧绿的竹林,但是,竹林始终为我所眷恋。这些年来,我到南方出差或旅游,都要抽时间到竹林去,寻觅那飘逸的,灵动的,静谧的诱人气息。去年国庆节放长假,我同夫人一起登上了黄山,下山途中,在云谷寺,我又一次看到了竹林。那天正好下雨,秋风萧萧,细雨绵绵,云雾缭绕,平添了几分浪漫的诗情画意。此情此景,定格在我给老伴摄下的胶片上。
游览竹海,观赏林子,套用一句时髦的用语叫做:吸氧、换气、洗肺。诚然,此中可以涤荡污浊,冲洗尘埃。不过,更玄妙的是自然清新,能够净化灵魂。在尘世间越来越迷乱的各种诱惑前,浮生反省,竹有节,人有格,有的能做,有的却是万万不能做的。虽然,高风亮节圣贤事,但是,守住节操,凡人也要努力去做。
原栽2002年8月17日《甘肃电力报》
往事抒怀
我在神奇的青藏高原整整度过了十个春秋,在那里所经历的一段往事,使我终生难忘。
那是在25年前隆冬的一天,我们侦察组在尼木县境内完成任务后,按照指挥部所规定的路线,相互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行进着。中午时分,在翻越一个海拔5347米的山口,还剩100多米时,我突然感到头痛、耳鸣、恶心、四肢麻木,两只脚怎么也抬不动。我意识到这是因严重缺氧而引起的高山病的征兆。这时,同行的战友刚刚翻过山口。
到山口没有路,是一段流沙陡坡,表层的沙子被山风吹得不停地向下滚动。我使尽浑身的力气站起来行走,可没走两步就跌倒了,这样反复了好几回都没成功,此刻我心里十分清楚,在这里多停留一分钟,死神就向自己更逼近一步。于是我在心里不断鼓励自己,爬也要爬过山去。生存的欲望促使我艰难地用上身托着两条腿匍匐向山口爬去。10米,20米30米,50米……我爬过的地方留下一道槽,可不一会儿就被流沙填平了。这短短的50米,我用生命和信念整整爬了半个多小时。
眼看就要到山口了可信念并不等于体力,随着高山反应的加重,我没力气向上爬了。我抬头仰望,天髙云淡,雄鹰飞翔,远方的雪山在斜阳的照射下,晶莹绮丽,巍峨挺拔。世界是这样的美好,但眼前这50多米的沙坡,却挡住了人生之路。我心神有些恍惚心里也有点绝望。我紧闭双眼,心里想再也见不到故乡的亲人和军营的首长及战友们了。我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拔出心爱的54式手枪,朝天上打了6枪,渴望已翻过山的战友们能听到我发出的信号。枪声过后风仍然刮着沙仍然滚动着,雄鹰仍然飞翔着,雪山仍然屹立着,渐渐地我的眼前模糊了,脑海中空白一片。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隐约听到有人呼喊我,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一座帐蓬里,两位参谋守护在我身旁,还有一位老阿妈在轻轻地搓着我的脚。地上,一堆牛粪火燃得正旺,一把铁壶直冒热气。帐蓬顶上的吊吊灰被热气冲得忽闪忽闪的。他们见我醒来,都髙兴得流下了泪。原来,两位参谋翻过山口后,下山到一个能避风的地方等我,结果等了一段时间,还不见我赶上来,便从原道返回迎我,快到山口时,听到了几声枪响,就迅速赶了过来,见我已昏迷,就轮换背着我走了十多里地,来到了藏族老阿妈达瓦卓玛的帐篷里。
老阿妈自称60岁了,可看上去比她说的年龄要大得多,她热情地端来了羊肉干、酥油茶和糌粑并一个劲儿地劝我们多吃点,我一边用手揉拌糌把吃,一边喝热乎乎的酥油茶。不一会儿,从心里热到了周身,2小时后我的髙山反应就减轻了许多。平日里,我总觉得酥油味很臭,糌粑难咽,牧民很脏可那天,我感到酥油茶是那样的香甜可口,糌粑是那样地顺口好吃,牛羊肉是那样的别有风味,老阿妈如同自己的妈妈一样是那样地朴实、亲切、慈祥。
当我重新踏上归途时才看清,这里是一个向阳的山坡牧场,牛羊成群,帐篷就扎在山坡根,不远处有一条结了冰的小溪。
太阳落山了,夜色渐渐吞没了山野沟谷,白天的一切都远离而去了,但山坡根的那座帐篷、老阿妈的笑容和战友救护我的深情厚谊,使我永记心间。
香甜的酥油茶
金秋十月,我在金城兰州参加学习。一日,巧遇藏族老战友,他邀我到他在兰州办事处的家里去做客。热情的女主人一见是我,打过招呼后,便转身进了厨房,不大一会儿工夫,就端来了热气腾腾、散发着诱人的香甜的酥油茶。顿时,我在西藏工作时与酥油茶的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一下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32年前,我参军到西藏雪域高原。走在拉萨的大街上,就能闻到刺鼻的酥油味,进了拉萨的百货商店,戴上口罩还觉得闷得慌。到了部队驻地后,为了使新战士尽快适应西藏的生活环境和战备需要,连队安排每星期吃3顿藏饭,即吃糌粑和喝酥油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