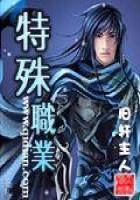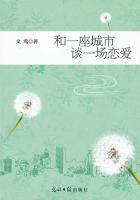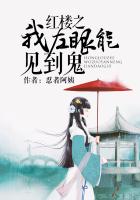在公社化的年代,队里出钱请来石匠,为山泉打了两个蓄水的大石槽,并在山泉的四周铺上了石板,从而,改变了山泉的土面貌。后来,随着刘家峡水电站的建成发电,我的故乡也受益,拉上了电,照上了电灯。上世纪70年代初,由政府投资,队上出劳力,在山泉旁和村中心各修了一个蓄水池和泵房,并安装了水泵、电动机和上水管道等配套设施,使山村祖祖辈辈用牲口驮水吃的地方改成了挑水吃,还用山泉水浇上了果园和菜地,极大地方便了乡亲们的生活。到了农村包产到户以后,集体财产大多被分到户了,而抽水上山系统虽然仍为集体所有,但由于缺乏维护资金和管理,设备坏的坏了,丢的丢了,就连那些埋在地下的钢管道,也被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偷偷地挖去卖了。没办法,村上的人们又开始了用牲口耿水吃的日子。好在今年春节,我给我的两位嫂嫂祝61岁寿辰时,听村上的人们说,大伙又在张罗着如何恢复抽水上山系统的事情,听后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听我三哥讲,有一年夏天,下了一场特大暴雨,山洪卷着泥石流淹没了山泉,这可急坏了村上的大人们。雨后天晴,全村的人都去了山泉的地方,挖开泥土搬走乱石,整整用了两天的时间修整山泉,当全部清除掉压在泉眼上面的泥石后,山泉依然如故地从地下涌了出来,一串串珍珠般的水泡从水底冒出水面。我也曾听父辈们讲过,村上的这口山泉,就是在历史上最干旱的年间,山上的草都干枯了,可山泉从来没有干涸过。
故乡的山泉,它默默无私日夜不停地流淌着千万年的积蓄,以甘甜的乳汁养活了一方人。我爱故乡的山泉,因为它从故乡的八愣山流出,具有八楞山的宽厚;它先流入洮河,具有洮河的气势;它后汇人黄河,具有黄河的喧腾;它最终奔向大海,具有大海的激情。它虽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溪,可在我的心里,它是一条永远奔腾不息的激流。
我愿故乡的山泉,永远流淌,永不干涸。
远去的蝈蝈声
夏收季节,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故乡的变化之大,让我都有些陌生的感觉。过去的山间小道,变成了宽敞的公路;山坡陡地,变成了狭长的梯田;矮小土屋,变成了高大的瓦房;昏暗油灯,变成了明亮的电灯……这些巨变,使我兴奋陶醉。然而,在回到故乡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听到一声小时候每年在麦收时节能听到的那满山遍野的蝈蝈声。
我的故乡在金城以南八愣山的马家,村名是因为全村的住户都姓马而得名。在我童年时,村上只有十来户人家,耕耘着大山的土地,守着一眼清泉,过着清静安宁的农家日子。故乡虽在干旱少雨的大西北,可村子的周围都是人工树林,喜鹊的窝,就搭建在高高的白杨树上,这林子面积不算大,可这儿却是鸟儿们的天堂。沟沟壑壑的植被也不错,长满了狗刺、毛儿刺和茂盛的蒿子等杂草,还有一些看上去已有几十年没种过庄稼的荒地,荆棘丛生,连人都难以进去。这些地方,都是狐狸、野兔、松鼠等小动物和呱啦鸡及昆虫的世外桃源。而在众多的昆虫中,爱叫唤的蝈蝈最受山里的娃娃们的喜爱,这也就自然成了他们的宠物。
蝈蝈体长4公分左右,有六条腿,大肚皮,脖子上长一垫肩,背部是一双透明的短而硬的翅膀,头上的一对相当于体长的又细又灵活的触角,上下左右飘动自如,美极了。而最美的是它背上的双翅相互摩擦所发出的吱吱响声,节奏清晰,明快动听,而且能连续不断叫上个把小时。每年的收麦时节,也是蝈蝈成熟的时节。当太阳的光辉照亮大地的时候,山野里的雄蝈蝈就纷纷攀到草的上端和各种刺的尖尖上,背向太阳,便开始欢叫起来,阳光越烈,它叫得越来劲。要是仔细欣赏,好似在演奏乐器,韵味十足。其形式,既有独奏,又有合奏;其声韵,既有粗旷高昂,又有细小低沉;其节奏,既有快的,也有慢的。到了这种境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的阵阵蝈蝈声,仿佛在与我的心灵对话,同时,也使山野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活力。
蝈蝈那样髙叫,是炫耀自己?是歌唱太平?还是寻求配偶?到现在我也不得而知。但它那悦耳的声音却惹人喜爱,于是山里的娃娃们享受了城里的孩子们难以实践的捉蝈蝈、养蝈蝈,欣赏蝈蝈的乐趣。如今回想起来,那场景,那情趣,那快乐,使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一到星期天,我和村上的小伙伴们,用麦杆编制好小笼子,就到山坡草地去捉蝈蜗,捉蝈蝈需要有技巧和耐心,要慢慢地接近目标,再根据声源判断蝈蝈的具体位置,一旦看清目标,捉的时候要迅速,但不能伤了蝈蝈。养好蝈蝈需要有爱心,要付出真爱,精心喂养,才能养出好蝈蝈。而欣赏蝈蝈是个非常快乐的过程,我们按约定的时间,带上自己喂养的蝈蜗,进行比赛,看谁的蝈蝈长得精神,先叫,不怕人,连续叫得时间长,声音清脆好听。要是谁的蝈蝈参加比赛,没得上好名次,那次曰非要再去野外寻找捉来上等的蝈蝈不可。有时我也单独欣赏蝈蝈的叫声,也十分高兴。即使是在上学读书时,要是变天刮大风下雨,对自己养的蝈蝈也常常是牵肠挂肚,怕风吹着了,怕雨淋着了。记得有一次刮大风,蝈鲴笼子被吹到地上,让大公鸡把蝈蝈吃了个精光,这使我伤心了好几天。后来还气不过,
我便把大公鸡背上的毛拔了个精光。山里的孩子们玩蝈蝈,虽然比不过旧社会城市里的达官贵人玩得那样奢侈,但毕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精神上的满足。
听我三哥讲,在大跃进年代,村上的大树被砍光了,就连两人合抱不住的老榆树,也被砍了当燃料炼了钢铁。后来随着村上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燃料的不足,开垦了荒地,先割完了沟里的一人多高的刺条,后连根也挖出当柴烧了,加上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所以在故乡已有十几年没有听到蝈蝈的叫声了。我不敢相信三哥讲的是事实,抱着希望,于此日独自一人,踏遍了我在儿时捉蝈蝈的地方,眼前的现实证实了三哥的话,令人失望。我面对凄凉的山野,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我的心中却万分怀恋那悠远的蝈蝈声。
父爱无边
我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但种一手好庄稼,而且拉二胡、弹三弦、打锣鼓、吹唢呐和笛子,在家乡是很有名气的。在收成好的年头,要是闹社火唱大戏,十里八乡的都来争着请父亲,都以能请到他坐在戏台上伴奏为荣。在我小的时候,每有这样的机会,父亲总是把我带上,让我感受民间文化生活的熏陶。
八岁那年,父亲摸着我的头对我说:“到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有出息。”我理解父亲的话,在一年级就当上了三好学生,父亲一高兴,就给我买了支三元六角钱的黑杆杆金笔。这对一个家庭十分困难的学生来说,是一件奢侈品。当然,我也深知父亲对我的希望。到三年级时,恰遇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村里的大部分学生都相继停学,到生产队挣工分去了。有一天晚上,有一个来我家串门的人,在闲聊的时候,劝我的父亲说:让娃娃们读书不如让娃娃们挣工分,抓现的,到了年底分钱分粮食,让娃娃们上学是白花钱。我听后急了,哭着向父亲说:“我不去挣工分,我要念书。”父亲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安慰我说:“不要哭了,只要你爱学,家里再困难,也要供你念书。”父亲的话,更使我止不住流下了来人劝说我父亲让我停学的伤心泪,同时我也从父亲那双粗糙的大手中,深深地感受到了父爱的无边。
我家离学校有五里的山路。一日,我在放学回家的胳上,被暴雨淋病了,发了三天的高烧。于是父亲就在我上学的路上,靠山坡挖了两个避雨的窑洞。我读五年级时,也是家里最困难的时期,每天的主食没有面粉,都是土豆煮苦苣菜。每顿吃饭时,母亲都要把不多的土豆块分到每个人的碗里,而每次吃饭时,父亲也总要把自己碗里的土豆搛上两块放进我的碗里。因长时间营养不良,父亲在那一年得了浮肿病,这对我家来说是雪上加霜。好在母亲是个要强的人,支撑起了经济十分拮据的家。那年秋天,新学年开学,家里却拿不出一元五角钱的学费。到了报名的最后一天早晨,我违心地对身有重病的父亲说:“爹,书我不念了,我去参加队里的劳动,给家里挣工分,等家里有钱了,把你的病治好了,我再去念书。”可我一万个没想到,在重病中的父亲,已为我借好了所需的学费钱,并慈祥地对我说:“你尽说傻话,念书要紧。”我含泪接住父亲给的钱,便一口气跑到学校报上了名。后来,父亲的病经过治疗,也渐渐好了,我也没辜负父亲的希望,以学区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
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后,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应征人伍到了西藏边疆服役。临行前,父亲一再叮嘱我:“到部队上要听领导的话不要怕吃苦。”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父亲在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天天念叨着我,可他怕影响我的工作,再三吩咐家人不要将他的病情告诉我。在父亲病重时,我没见上一面,成了我终身的憾事。
我的父亲享年八十岁,离开了我们兄弟姐妹。父亲的吹拉弹唱的绝活我一样也没学会,可父亲的高尚的品格使我懂得了如何去做人,如何去做事。父亲的慈爱更使我终身难忘,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与共和国同龄
1949年春天,随着解放祖国的隆隆炮声,我出生在大西北一个小小的山村里。从我记事起,父亲总是对来人介绍我是解放那年生的,后来懂事了,才知我与共和国同龄。
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以她江河的乳汁,大地的血肉,孕育着我生命的幼苗;用文明的长流,智慧的泓泉,滋润着我心灵的嫩芽。山村小学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高髙地挂在我心中,在那简陋的教室里,我聆听老师的教诲,天真朦胧地勾画着我童年的梦,长大后要做一名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把母亲的万里边疆巡守,或者做一名教师,用永恒的爱,把祖国的花朵精心浇灌,或者……
在祖国母亲的温暖怀抱中,我如愿以偿,1968年应征入伍,到了西藏边防部队,为祖国站岗放哨。虽然雪域高原的自然环境条件十分恶劣,但有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我心里踏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没有悲观失望,依然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和希望。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我一个农村娃,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入了党,提了干,立了功,上了学。1987年,我脱下穿了二十年的军装,转业到甘肃省电力工业局水工维护检修公司工作,后来又走上党委书记的工作岗位,并获甘肃省省直机关优秀党员的称号。回顾自己成长的过程,深深感到,自己的幸福,快乐、成功与失败,都与伟大祖国的贫困与富饶、困惑与振奋、阴影与光明、落后与崛起、创痛与希望,休戚相关。没有祖国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就没有自己的健康成长与幸福生活。
斗转星移,我同共和国一起迎来了50岁的生日。在这50年里,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从屈辱中觉醒,而且从苦难中站起。卫星上天,“两弹”成功爆炸,改革开放富民强国,一国两制使香港胜利回归,澳门即将回归,台湾问题也必将得到妥善解决,祖国的统一大业一定能够实现。
我是祖国母亲的热血男儿,在有生之年,要时刻把祖国装在心里,把我生命的全部献给伟大的中国。
原栽1999年7月貌的建设
回家的感觉真好
虽然,我早已成家立业,儿子也已长大参加工作,小家温馨,幸福美满。但由于对故土的眷念,我时常想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家,因为故乡的家赋予了我生命的全部。
14岁那年,我考上初中住校读书。初次离家,心里急得难熬,天天盼星期六的到来,只要星期六下午一放学,15里的山路我仅用一小时就跑回了家。那晚母亲做的饭,准是我最爱吃的。夜里,我偎在母亲的身边,一一回答她的问长问短。母亲没有进过学校门,不识一个字,可她对我所讲的学校里的每一件事都很感兴趣,并不时地指点我如何去处人处事。次日,我背上母亲烙的馍,按时返校,坐在煤油灯下上晚自习。
没想到在我19岁上出了个远门,参军进了西藏边疆部队。在那特殊的年代和那特殊的地域,半年都收不到一封家信,那想家的心情常常使我茶饭不香,睡不安忱,思念母亲,渴望回家。当兵四年后,被批准头一次探亲,我手捧《军人通行证》,激动得一夜没合眼。我乘飞机、坐火车、搭汽车,急匆匆往家赶,一到村头,我一眼就看见了母亲在大门口。后来听三哥讲,读自家里收到我要探亲的电报后,母亲就天天坐在大门前的大石头上,等我回来,不等到太阳落山,她老人家是不肯进屋的。我远远地大声呼叫妈妈,妈妈高兴地迎我走来。见到几年不见的母亲,才感到回到家的感觉实在是真好。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真正理解了母亲牵挂儿在外的忧郁心境。于是,我越想回家。每次回家,母亲一定在大门口等我们一家三口人。母亲只要见到她的孙子回来了,就特别高兴,给她的孙子尽讲一些我儿时的顽皮和所干的一些“坏”事,并数落我永远长不大。有一次,母亲呼唤着我的乳名悄悄地问我:“你在部队上管多少人?干多大的事儿·”我回答母亲说:“妈,我管的人不多,干的是七品芝麻官差不多的事儿。”母亲听了后点了点头,笑了。我从母亲的笑容里,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平凡母亲的满足。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母亲笑口常开,不要为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而担忧。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在获得成功时,想回家与母亲共享胜利的喜悦;每当我在遇到挫折时,想回家让母亲的爱,愈合我那被创伤的心灵。
我想回家,因为家里有母亲,有我童年的梦,有我生命中永恒的根。
原栽1989年6月10日《西北电业职工》
夏登八楞山
八楞山,位于兰州以南30公里,是七里河区与临洮县和永靖县的交界处。海拔2851米。为了看日出,我们在黎明前就沿崎岖的山路登上山巅。5时10分,东方发白,随后一轮红曰燃烧着从山背巵冉冉升起,顿时天空流霞飞彩,大地群山生辉。我曾登上泰山、黄山看过日出,而在八楞山观日出,同样可以观赏到初升太阳的洁净、美丽、壮观和神奇。
在八愣山看云雾奇景,也算得上一绝。因前几天下了一场透雨,云雾缠满了洮河川谷,淹没了村庄、树木和田地。太阳升起不久,云雾就开始翻腾起伏,迅速沿着沟谷,直向山顶扑来。此时此刻,我只觉如踏万顷波涛。在朝阳的辉映下,云雾变幻,构成了一幅气象万千的奇妙画卷。面对这样的云雾奇观,谁能不赞叹天公造物的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