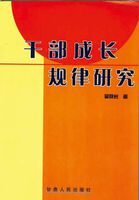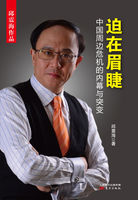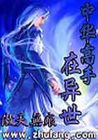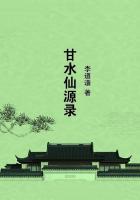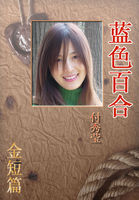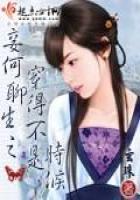“剑桥学派”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至今算不上显学,但研究者对它都已不再陌生,这首先应拜赐于斯金纳的若干种著作在近年来被译成中文,其中尤其不能不提的,便是1979年出版、近由译林出版社重新推出中译本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该书自面世以来,便成为这个学派最重要的基础读物之一。
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说法,斯金纳这本书研究的是“早期现代”。近年来随着思想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回到“早期现代”重新检讨当今社会诸般现象的源流已然蔚成风气,因很多过往的历史事件,其意义是到了20世纪才逐次展开,人们由此提供的新线索,在重新审视和思考历史时就会对前人的视角有所不满。在政治思想史的领域,这种努力的结果便是“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界线与关系,要么变得更加模糊,要么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也使过去的很多成见为之而发生动摇,当初被人们否定或忽略的思想,或因社会巨变而一度被淡忘的人物,随着历史场景更充分的铺展,会重新彰显其价值,一些曾几何时轰轰烈烈的“新事物”,反而变得不再那么新鲜。
在这种风气之下,斯金纳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把现代的起点推前到12世纪的南欧,也就不必奇怪了。此一时间观念的变化,其实早已出现在伯尔曼等法学史家的研究之中。斯金纳在这本书里并不想引导读者去了解各种“成熟的”理论,而是要讲述这些理论早期的话语背景与观念的来龙去脉。这也正是剑桥学派的优势所在,即所谓的“语境主义”。斯金纳在《观念史研究的意义和认识》一文中,将这一点说得很明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应看重偶然性而非必然性,揭示观念在特定时代的具体面貌,而非它在后世的效果;每一部经典文献的价值在于它自身的特性,而不是它在理论体系中的共性。在这种研究取向之下,斯金纳的著述特点一向在于发掘政治生活场景中的各种思想的具体表述或“修辞”,而不是哪个大思想家的学说或“思想体系”。所以,回答所谓“哲学的永恒问题”不但无益,而且是“完全没有指望的事情”,因为“任何陈述都必定是在特定场合、从解决特定问题发出,必定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意图,因而有特定的情境,超出这个情境去认识就只能是幼稚的”。这样的言论,埋首于历史文本的思想史学家最易于说出,但把文本整理为条理分明的叙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涉及的时间范围是12世纪到16世纪,全书并未严格按时间顺序布局,而是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作为上下两卷的标题,把这两场充满内在紧张的思想文化运动作为理解推动近代政治思想演变的力量的主轴。相应地,从书中的各章节中,我们也几乎看不到以哪个思想家作为标题,而几乎完全是以某些观念作为核心,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气氛的描述。当然,读者仍可能看到彼得拉克、但丁、马基雅维里、路德、加尔文和博丹等这些显赫的大人物,但还有更多的篇幅是留给了佛罗伦萨早期的人文学者萨卢塔蒂、布鲁尼、布拉乔利尼,以及后来的苏亚德斯、比代、维多利亚、德索托、热尔松等这些不太为后人所知的思想家。在这种叙述模式中,众多出现在特定时代背景中的思想素材相互交错,构成了一个斑斓的织体。这使读者难以祈盼思想体系的明晰性,只能从原始文本的分析中透视思想演变的细节。这大概也是它不像一般宣示和讲述理论教义的著作那样易于得到普及的原因。研究思想史的人大概也都能体认,这种讲述理论的方式最不易讨好读者,但也最吃功力。
对于“现代政治世界”肇始于何时这个问题,斯金纳选取“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作为标准,应是一个方便而安全的选择。他以12世纪“自由理想”在意大利商业化城邦如佛罗伦萨、米兰和帕多瓦等地的出现作为起点,分析那里的人文主义者如何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的斗争中,重新回头去挖掘古典城邦的共和理论和公民意识。但是这里的“自由”一词的所指,并非那种后来得到大力强调的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更多地是指一种个人在城邦的公共生活中所要承担的责任,或者从国际公法意义上说,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城市所享有的独立和自治。从这个角度看,它与现代的自由观仍有很大距离,然而它却孕育出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雏形。
就像任何重大思想运动的初期一样,这些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努力由于缺少成功的政治经验带来的方向感,因此并不易取得成功。他们有关公民素质和自由的论述过于世俗化、过于超前了(或者有人更乐意说,过于古老了)。由彼得拉克最先树立的这种共和主义自由理想,虽然一时蔚然成风,但它并没有在意大利结出政治上的硕果。而只能成为“残存的共和价值”。马基雅维里充满信心要去战胜的“命运”,最终是以圭恰迪尼对这项事业的彻底绝望而收场的。他们在文艺复兴的世俗化大潮中构想的那种现代国家观,必须重新返回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唾弃的教会传统之中,通过教会会议至上主义的立宪思想、罗马法框架内对君权与人民的关系的梳理,以及伊拉斯谟等“北方人文主义者”对美德和教养概念的再加工,才能最后完成于博丹的现代专制主义。另一方面,清教徒将共和主义思想与基督教的团契精神重新整合在一起,才使其在北欧地区重新焕发生机。同样,像人民主权论、契约论或“自然状态”学说,这些后来成为现代政治理论基石的东西,虽然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未能成为主流话语,但它们同样是萌发于教会内部的思想家,例如16世纪的托马斯主义者已经对它们做过相当细致的论证。正是这些观念的涓涓细流,后来逐渐汇集成思想的巨浪,对现代政治世界的塑造发挥了巨大作用。
大体上说,斯金纳这种本书最可贵的价值,是它为现代人耳熟能详的诸多理论提供了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宽广的视野。我们或许不必过于认真地看待剑桥学派所标榜的语境主义和客观精神,从以上这些概念在斯金纳书中的运用来看,他也不可能跳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魔咒。历史不仅是经验和思想创造的积累,而且是对意义的重新发现的积累与叠加,这就是我们今天不可能再像前人那样续写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还原思想史的真相,总是要带着今人给我们制造的有色眼镜,这并非思想史的不幸,而是它的魅力所在。
(原载于《读书》,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