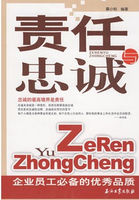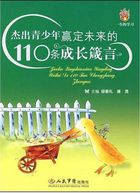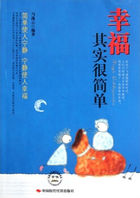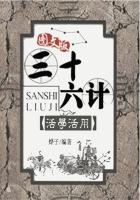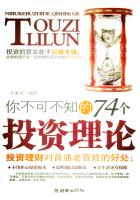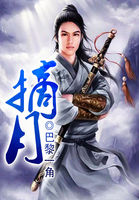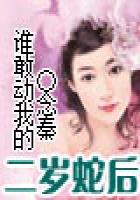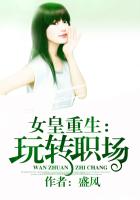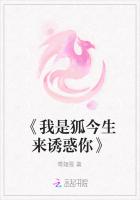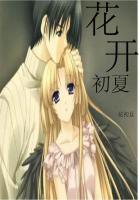三十六、水平高超
工作方式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是完成任务、实现目标的手段。毛泽东曾经用过河与桥或船的关系对比作了深刻而通俗的说明。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有桥或没有船都是不能过的。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尽管有正确的方向,良好的动机,如果方式不当,就会影响办事的效率和效果,完不成任务,甚至南辕北国计民生,背离初衷。周恩来极为讲究方式方法,做什么事情总要反覆琢磨,选择运用最精当妥贴的方式方法实现目标。
一九七二年一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白宫发言人齐格勒等一行,为尼克松访华来到北京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周恩来指示他的助理熊向晖约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此事。会上,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表示了断然否定的态度,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并说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同志都明白,于所说的"首长"就是指江青一伙。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气愤地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经由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他明确反对那种表面上似乎很革命的极端作法。
当时中国还没有通讯卫星及有关技术,须向美国租用卫星,转播技术方面也得请美方协助,问题是采用什么方法进行。当时提出了三种方式,一是美方齐格勒提出的:租用卫星很贵,尼克松访华八天,八天的租金可能要一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方承担。二是熊向晖提出的:他认为修建地面站的费用,若由美方承担,这有损中国尊严。他向齐格勒表示,费用由中国支付,只要求美国的技术协助;至于租用卫星问题,他考虑的是既然美国政府已经作了准备,就何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卫星呢?周恩来听了熊向晖的汇报后,认定齐格勒的办法,有损中国的尊严和主权。熊考虑的方式虽有道理,但美国卫星若不由中国租用,而是由美方在中国使用,为美国服务,岂不同样损害中国的主权?周恩来批评熊向晖说:"让你商谈租用通讯卫星,你一听百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他提出了第三种方式:一是向美国租用一颗通讯卫星,二是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国收取费用;三是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齐格勒听了中国方面提出来的这一合情合理的方安,立即表示接受。至于租用费和使用费他认为是互相关联的。他说,他想这两项费用将画个等号。
上述三种方式,都是用美国卫星、美国技术,在中国修建地面站,为尼克森访华服务,而实质上不用中国出钱,但却有了不同的性质和效果。按照齐格勒和熊向晖的方式,程度不同地都损害了中国的尊严和主权。而按周恩来的办法,中国实际上仍不用拿出分文,却维护了我国的尊严和主权。周恩来考虑问题的周密细致,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的精当妥贴,给美方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齐格勒一再表示:"我很佩服你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
与方式相联系的是形式问题,形式必须和内容一致,否则,无法正确表达内容。刊登新闻报导版面的选择,属于形式,它必须和稿件内容的特点及重要程度相一致,才能收到良好的新闻效果。周恩来对这类形式问题,从不马虎对待,总是要求有关负责人,精心地选择采用最恰当的形式表达内容。
一九六二年,中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蒋介石集团以为有机可乘,叫采反攻大陆,调兵遣将,有蠢蠢欲动之势。当时认为蒋介石如果没有美国当局的同意和支持,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为了摸清美国的态度,周恩来指示参加中美会谈的我方代表王炳南,约见美方代表,对美国提出严重警告。
四天后,美国总统甘乃迪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反对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重申美国军事力量在台湾海峡地区的目的是所谓"防御性的"。他在答记者问时又进一步说出了台湾曾经作过的保证,即:一九五四年美蒋条约签订时,双方交换过信件,国民党当局在信件中保证未经美国同意,不对大陆采取行动。他明确表示:"我认为那封信仍然有效。"很明显,甘乃迪的声明和谈话是对中国政府的警告做出的正式反应,断然否定了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问题。美国当局的态度清楚了。
对于这样一条重要新闻,《人民日报》如何刊出,应放在那一版,什么位置?报社负责人和编辑部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放在国际新闻版显著地位;二是放在第一版显著地位一;三是放在第一版不显著地位。他们倾向于第二个方案,但拿不定主意,于是向周恩来请示。
建国初期,《人民日报》负责人遇有重大疑难问题,总要请示周恩来。白天无论如何是挤不出他的时间,只好安排在晚上。所以周总理几乎成了他们的"夜间总编"。周恩来听了《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的汇报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样一个和中国直接有关的重大事件,放在国际新闻版显然不妥,但也不必放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因为甘乃迪的态度显然很重要,但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像这类很重要而不宜过分突出的新闻如何安排,他根据过去刊登这类新闻的经验,提出以放在第一版右下角为宜。大家都十分佩服周恩来精心刻意的处理和安排。把这类新闻放在第一版不显著位置,既未贬低,也未拨高,做到了形式与内容一致,天衣无缝,恰到好处。
三十七、情意深长
1958年7月的一天,江苏省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受县委委托,准备"走个后门",上京见周总理,要点钢材发展地方工业。没想到总理接见他时,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但在分手时,总理又说:"我和你的事还没有完、改日再谈。"王汝祥听后,心里忐忑不安,两天来心上总像压了块石头。"改日再谈",这一定是总理批评他不远千里来开后门吧。第三天,他忧心忡忡地穿过如茵的草坪,总理已在办公室大厅外等候了。
"吃好了吗?"总理老远打着招呼,拉着王汝祥在客厅藤椅上坐下。王汝祥局促不安地搓着手低着头,不敢正视总理的目光。想起那天来见总理时,自己没有将来意和盘托出,而是转弯抹角地以汇报家乡情况为由暗示故乡的困难,而总理却一语道破:"你是来找我这老乡起后门吧?"王汝祥的脸上又觉火辣辣的。不知这次等待他的是什么?想到此,王汝祥更心神不宁地抹了把额上的汗水。
总理早已体察到老王的心境,他带着歉意地说:"老王,这次你来,我招待不周,仅让你吃个便饭,你一定要嘀咕我这老乡小气了。"
"不,不,总理,那天我吃得很好。"
总理摇了摇头:"你们在下面招待客人可能比它丰盛,我这总理不自由啊!国务院有待客标准,我不能例外。"
王汝祥听罢,心中别有一番滋味,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总理谈到对自己旧居的处理时说,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特殊,该怎样处理就怎么处理。当听王汝祥讲到近年出现的耸人听闻的咄咄怪事,大搞生产"捷报"的谎报,把粮食亩产以5000斤逐渐增加时,总理面色严峻,感情激动地说:"干劲要鼓,但要实事求是。"接着又谈到当时执行政策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改造"。目前,改造讲得多,团结讲得少,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推心置腹地同我们交谈……"
谈着谈着,总理象要摆脱和暂时忘却那些纷繁的政务似的把话题一转,微笑着说:"老王,老乡之间可不兴贿赂"。
"贿赂?!"王汝祥心中吃惊不小,想起这次进京,带一盒家乡土产茶馓子。旅途上,自己冒着炎日,汗流浃背地拎着这盒茶馓,唯恐受压。到京后,便托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转交给总理。想象着总理大口地吃着故乡的茶馓子,会连连赞不绝口的。可总理讲是"贿赂",王汝祥低头嗫嚅地说:"这是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请总理尝尝。"
"尝尝?整整一大铁盒子哩!不准请客送礼,国务院有规定。"
"这……"王汝祥语塞了。看到这情景,总理抬手摸了摸鬓角,哈哈大笑:"看,都把我当成黑脸包公了!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位从家乡来找我的父母官,好吧,我也只好破例地来个执法犯法了。"
总理十分感慨地说:"离开家乡太久了,连你这父母官都不理解我了!"说罢,又轻声地问道:"文渠没有堵塞吧?"
"没有。"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们怕出事,把小船都锁起来,我们就悄悄地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着大锣,满街满巷吆呼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地从文渠划到河下去,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的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了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少不了要挨惩罚!可婶娘半句也没责怪,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涮涮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谈到童年,总理娓娓叙来,神情关注。他仿佛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孩子提时代,变得年轻多了。王汝祥见总理对故乡如此情深,便说:"总理,您老离开家乡这么多年,现在家乡变化不小,您老该回去看看。"
总理微微点头,仰躺着藤椅上,微启双目,充满感情地说:"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1946年,有一回,我在南京梅园新村,梦见自己在文渠划船,醒来后便想,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一定要回去看看。可这些年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有时候工作忙,遇到棘手的事情、难遣的烦恼,紧张得饭都成不上吃,觉不能睡,真想立即回去约几位童年时的朋友,爬爬鼓楼,放放风筝……"总理说着,说着,双眸湿润了,完全沉浸在缠绵的思乡深情之中。
王汝祥不忍打断总理的回忆,他深情地打量总理。王汝祥忽然发现,总理两鬓斑斑,瘦削的面孔铁青,一刹那间显得那么疲倦和憔悴。想起曾听总理的婶娘讲过,总理少年时"乌眉大眼,天堂饱满,身体很结实",王汝实心头一震酸楚,极恳切地相劝道:"总理,工作再忙,您老也要注意休息啊!"
总理微笑着未加置否,沉默了一会,说:"老王,你是父母官,我的心里话对你不隐瞒。我讲个事你听听,你裁判裁判。有这么一个摆渡的,他在湍急的激流中,把船划到了中心,这时,他感到很疲劳,而对岸又是旅客们很向往的地方,你说,这个摆渡的该怎么办?"
王汝祥听了这话,胸口顿时象一股强烈的漩流在激荡:自己是个打游击的出身,年轻时是抱着找出路的思想参加革命的。解放后,自己这"老革命"有时还怀有一种功臣的荣誉感;而总理自幼投入革命,戎马多年,出生入死,到现在还感到渡船才走了一半,还要为他毕生追求的事业鞠躬尽瘁!相比之下,这差距……王汝祥倏地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双眼酸涩,忍不住住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的泪花,望着总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打破沉默,总理递过一封信,信封上写道:"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同志收",总理说:"扯到现在,没入正题,你从老远来,我不能让你空手而归。我这淮安人也得尽点淮安人的责任。这封信你交江苏省委,你们的困难尽量请他们帮助解决。"
王汝祥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对开"后门",吃"小灶",王汝祥深感给总理带的麻烦,想不到,总理并未过多责怪,还牢牢记在心里。怪不得总理对自己说:"我和你的事还没有完。"王汝祥接过信,高兴地连看都没看,就小心翼翼地把这封沉甸甸地信札放进口袋。总理的乡情,比金子还贵重。这时候,王汝祥只恨自己的工作没做好,没能尽快改变淮安的落后面貌,还要让总理操心。
总理看看王汝祥装好信札,又用商量的口吻说:"老王,我有个不成熟的看法,上次,你说你们打算把全县的旱田全部改为水田,我看这不一定妥当,要照顾群众的习惯和情绪,旱作物也有高产的。"总理的话更引起王汝祥的一阵内疚和不安。
转眼3个小时过去了,王汝祥起身向总理告辞,缓缓走出客厅,又回头望着总理,许久舍不得离开,总理站在台阶前,也沉默地凝视前方,好象在深情地看着家乡那汩汩流淌的文渠,又象在牵拉着家乡那飘在白云间的风筝。王汝祥百感交集,再次请总理有机会能回去看看。总理没有忘记家乡人民的请求。1960年,总理从上海开完会,准备回故乡一行。正好毛主席来电要他赶回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原订回乡的计划未能实现。他在飞机经过淮安上空时,紧贴机窗,目不转睛,眷恋地俯瞰故乡的土地。他多想实实在在地捧一把故乡的泥土,喝一口故乡的水,偿还多年的夙愿啊!机组的同志没惊动他,让飞机减速低旋,转了好几个圈了。总理察觉后说:"毛主席在北京等我们哩,全速前进吧。"
总理始终没有回到故乡,但他的骨灰不是已经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了吗!他的浓烈的乡情,已经融会在故乡人民的心田里。
周总理的"小老乡"
——总理与"海政"演员杨桂林
一连数日,每当门外邮递员的车铃一响,杨桂林总是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出去,询问有没有寄给她的照片。是什么照片让她这样惦念,急切想得到呢?这不是从一次演出说起。
1959年的一天,绿萨掩映的钓鱼台礼堂里,正在进行着精彩的表演,周总理和许多中央首长都来观看演出。台上,一位扮作"红领巾"的部队小演员,以她那娴熟的动作,洒脱自如的演技,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周总理悄声问身边的同志"她是谁?"
"她就是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杨小亭的二女,"海政"文工团演员杨桂林。"
周总理欣喜地点点头。"噢,这孩子长这么高了!"
演出结束后,总理来到演员中间,他一眼便认出了演伞技术的小演员杨桂林,亲热地握着她的手,鼓励她:"小老乡,你演得不错!"
桂林愣住了:"怎么,总理也是天津人?"
"哈哈哈!"总理爽朗地笑了,"我嘛 ,就算个半吊子天津人吧!"
桂林恍然大悟。天津——桂林的故乡,正是周总理早年投身的革命的地方。那时,总理和邓颖超等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领导过风起去涌的学生运动。难怪总理对天津一往情深,风趣地自称是"半吊子天津人",而称自己是"小老乡"呢。
周总理拉着"小老乡"的手坐在一张沙发上,关切地询问她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小老乡"无拘无束地和总理拉着家常。总理还勉励桂林姐弟几人,要象他们的父亲那样,做一个既有精湛技艺,又有高尚艺德的杂技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