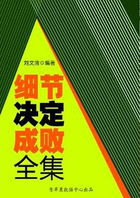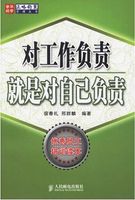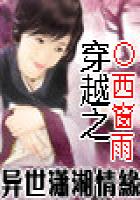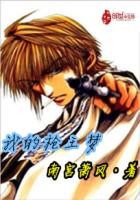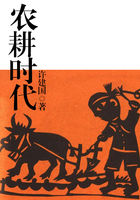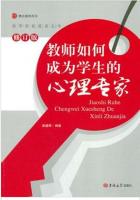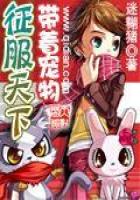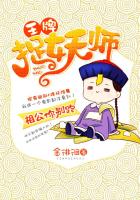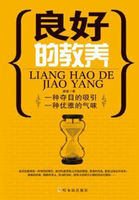对于当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周恩来更是严于律已。1954年9月16日,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一届人大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稿第二、第三部分,本约好今(十七日)早送你。第二部分还有些材料可以取用。第三部分……可用的材料甚少,也不好删改,……我很不安。原想由我先将各方面初稿汇集改好后再送你修改,不料拖了两周,竟不能终篇,而且延误了时间,给你造成极大困难,这是我的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严格说,也是思想上的错误。"这封信表现了周恩来同志严于律已的精神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周恩来进行自我批评是主动的、自觉的。有些事,并不是他的直接责任,但只要是国务院,党中央决定的,他都主动承担责任。
1953年,我国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职工群众劳动热情高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生产发展很快。全国工业生产率有相当大的提高,但几年来职工工资增长却比较缓慢,部分职工工资有所下降,没能照顾好人民的生活;1956年3月4日,周恩来在国务院部委召开的21个专业会议,31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一开始就说:"我今天是来负荆请罪的。"他接着说:"生产发展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职工工资没有相应的增加,甚至下降了,作为总理我是有责任的。"到会的同志无不对周恩来这种对人民极端负责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深深感动。
1959年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一天,周恩来去北京饭店参加小组讨论会。当他坐的汽车快要开到饭店门口时,饭店的一位工作人员,怕前面那辆车接住,就让前面那辆车继续往前开,先给周恩来的车让路。
看到这情景,周恩来立即走下车来,对那位同志说:"你为什么让人家的车开到前面去?快把人家请回来。人家是代表,我也是代表啊!"说着,周恩来站到饭店门口,等那位代表下了车,主动迎上去同他握手,道歉说:"对不起,请原谅!"并坚持让那位代表先进了饭店大门。
还有一次,周恩来应邀出席一个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乘坐的是一辆普通轿车。到了使馆门前,调度车辆的交通民警没有认出来,把他的车子调到离使馆大门较远的地方停下,当周恩来从汽车里走下来时,那个民警愣住了,深感自己失职,又立即指挥另一辆车躲开,让周恩来乘坐的那辆车开到使馆门前。这时,周恩来笑着对民警说:"这很不好嘛!车子停在这里,我走几步有什么关系?这样可以把使馆面前的地方腾出来,让别的汽车停放嘛!"
周恩来这种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的做法,使这位民警深受感动。望着周恩来高大的身影,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正是因为周恩来发自内心地把自己看成普通人中间的一员,善于尊重群众,平等待人,因而也常常得到加倍的回报,受到对方由衷的敬重。
此外,做好批评的善后工作还要总结教训,加以补救或改正。
对此,原总理办公室秘书,副主任李琦曾到过几起这类事情,并且映象颇深,几十年后,他回忆起来,仍象是在眼前。下面就是李琦回忆的两件受总理批评及善后的事。
1950年初他从地方上调到周总理身边工作,刚到不久,有一天半夜值班,总理交给他一份有关外交方面的声明,要求第二天见报。他照例封好,交给收发室就睡觉去了。没想到第二天报纸上没有刊登,总理自然生气,要他立即查明原因,并嘱咐他要每个环节都查清楚。经调查,原来是由于天气寒冷,汽车在政务院机关旧式库房里很久没有发动起来,等将声明送到新华社时已经晚了,错过了发稿的时间。总理想到他刚来,并没有过多地责备,而是告诉他:要采取措施,保证不再出现这类事。同时建立了一套必要的制度,如文件发出后,要逐件检查送达时间,特别是对于即将发出的重要稿件要及时预告对方等等。后来,这些已成为秘书们习以为常的工作程序了。在这件事以后,秘书们仍难免发生差错,总理除了对负责人员进行批评外,往往是严肃地要求找出原因,想出改进办法,建立制度。尤其是在涉外领域出了差错以后,总理总是要求做到消除差错所造成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有时,总理甚至自己出面去补救,力求消除这种影响。这种事例就不只一件了。错了,怎么办?不是单纯批评,而是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原因,加以改进。
大约是1952年,江西的邵式平来北京开会,打电话说想要见总理。当时是李琦接的电话,因为看到总理特别忙,就没有立刻报告。等到向总理报告时,总理说:"好哇,你跟他联系一下,约个时间。"他赶紧同邵式平联系,一打电话,才知人已经走了,回江西去了。李琦立刻向总理承认错误,说看您太忙,不忍心打扰您。总理听后十分严肃地说:"你太祖心!我再忙,你也应该告诉我嘛!能否见他可以由我决定嘛。"后来他才知道,总理对地方同志来北京要求见他的,一般都要想法接见,以便听听他们的意见。李琦认识到错误后,立刻写了检讨。总理批评说:"你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有问题,看不清问题的实质。只是看我忙,就不分事情的轻重缓急。"当时,他以为作了检讨,只要吸取教训,这件事大概就算过去了。没想到总理严肃地指示他说:把你的检讨改成电报,文字简洁些。以你的名义发给邵式平同志,道歉!这一下,他才知道总理是真生气了。他当然照办。同时也明白只有这样处理,才能说明造成这次失误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过错。而他起初只想着向总理有个交待就行了,却没有想到如何及时去消除因为他的错误而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教训。
周恩来认为,领导者和群众相处时,要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对群众中那些正确的建设性意见,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采纳;对于不可取的意见,也不能简单生硬地加以否定,而应肯定其合理成分,同时详细说明自己的见解。在交谈中,尤其不能打断群众的讲话,要让人把话说完。那种当面肯定,工作中否定的做法,往往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领导者应该懂得:"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对于群众敢于提出的不同意见,更应当特别珍视,慎重考虑。一旦发现比自己原来的主张更正确、更合理,就要勇于否定自己,而采纳群众的意见,决不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
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写道:"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式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周恩来实际上道出了他身居高位,领导群众但又和群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奥秘。
半个世纪以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居于高层领导职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担任总理达27年之久。但是,周恩来从不给人以居高临下之感,无论是他的部下,还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战士、教师、演员、职员、服务员、炊事员、理发员,他都平等对待,倾听他们的呼声,重视他们的看法。周恩来从不发号施令,从不强加于人,从不以命令的口吻讲话,即使发布命令或作出指示也丝毫没有两样。
周恩来遇事十分善于同群众商量,博采众长,倾听不同的意见。他说:"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他还说:"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
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确定之后,争分夺秒的施工立即开始了。当时建筑界有一位老教授,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提出种种责难。大家认为既然已开始挖槽施工,对这些非议可不理睬。不料周恩来听到反映后,很快请大家再次开会发表意见。会上,周恩来把那位教授请到自己身边,鼓励他畅所欲言。那位教授对周恩来平易近人的作风有所了解,便毫无顾忌地讲个不停。说各种建筑形式中最差的是"西而古",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就是"西而古",把大家一个多月的设计成果包括周恩来无数的心血抹煞殆尽。在场的同志都觉得太刺耳了。但周恩来却谈笑风生,十分耐心地请他把话说完,才和颜悦色地问道:"先生说的"西而古"表现在哪些地方?"那位教授毫不客气地指出:门前大理石柱的柱头、柱基和柱身"西而古"。周恩来听了爽然一笑,转向施工的负责同志说:"既然先生对门柱有意见,请你们尽快做出模型,再请大家来讨论。"会后,周恩来还亲切地留下大家进餐。10∶1的柱模型制好后,周恩来特地把那位教授请到现场,和工人及设计人员一起,最后审定柱头的式样。
坚持真理、修理错误,这是每一个领导者所认同并愿意为之而努力的。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领导和群众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争执不下,而双方又都有道理,说不清谁对谁错。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就要允许对方争论,允许对方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以权压人,以势压人,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1961年,新侨会议期间,周恩来去探望生病的黄宗英,赵丹也在场,赵丹便和周恩来谈起会上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时有责任中意见,有人认为电影好,有人认为小说好,争论相当激烈。周恩来说:"小说我没看过,谁有这本书借我看看。"赵丹说:"我有这本书,但不能给您看,因为上面写了许多批语。"周恩来说:"我正要看你批了些什么。"两天后,周恩来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了这篇小说,并同电影作了比较,认为电影改编得比小说好。赵丹则坚持认为小说好。7月1日,周恩来到香山和参加故事片创作会议的代表共同欢度党的诞辰。赵丹仍一门心思地盯着周恩来议论《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的问题。赵丹对周恩来说:"总理,我对你作的报告有不同的意见,你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是电影好,我看还是小说好!"周恩来说:"电影的时代感较强,场景的选择更广阔……"赵丹却说:"那只不过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最后,赵丹还是坚持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周恩来听后,偏过头微笑着看着赵丹高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保留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周恩来就是这样,从不因为自己是总理就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赵丹感慨地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
周恩来不以领导自居,他的部属和人民却把他看作最令人尊敬的好领导;他从不发号施令,他的意见总是以商量的口吻说出来,人们却总是自觉地、雷厉风行地去执行他的指示。相反的情况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见到:有的领导高高在上,处处摆着一副领导的架子,动辄以势压人,生怕人家不把他当作领导,结果偏偏相反,人家从内心里鄙视他,并不把他看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者;他们喜好"一言堂",喜好命令式的指示,生怕人家不照办,结果每每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或者拖着不办,或者阳奉阴违。
领导与被领导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事实上至少存在两种关系:由组织结构所规定的一方服从另一方的强制性关系,这种强制性关系通过权力体现着;由个人品格、形象所决定的非强制性关系,这种关系则通过非权力影响力体现着。在每一种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场合,权力和非权力影响力都同时存在着。组织所赋予的权力使领导者必须在行动上服从领导者;而领导者的个人品格、形象,他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包括友爱、信任在内的个人关系,则决定或影响这种服从的行为是自觉自愿的还是不情愿的、勉强的甚至反感的。权力和非权力影响力不仅同时存在,缺一不可,而且相互补充,相互作用。非权力影响力使权力带来的服从成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从而极大地加强了权力;而适当地运用权力,又能有效地强化领导者的个人影响力。事实上,被领导者从来都没有也不会把领导者与自己等同看待。正因为如此,领导者放下架子,平等待人,总能收到他竟想不到的增强影响力的效果。而影响力的增加,反过来又成倍地强化其权力。"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这正是周恩来作为一个高层领导者能深得群众信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奥妙。
周恩来逝世时所穿的灰色制服上有一枚纪念章。这枚纪念章上有毛泽东的形象,铭刻着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为人民服务"。周恩来非常喜爱这枚寓意深刻、构图美观的纪念章。从纪念章问世起,不论春夏还是秋冬,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周恩来都佩带着它,直到逝世。这枚纪念章,中国人民十分熟悉,许多外国朋友也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毕生实践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教导,也经常用"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他的保健护士郑淑云曾绘声绘色地回忆道:
"人们都知道,总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苦撑危局给累死的。但一般的人很少知道在"文革"前总理就通宵达旦地工作,自我到西花厅就没见他定时休息过。"
"记得在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总理一连工作了二十二个小时没休息了,还在一边工作一边等华沙会谈的电报。这天夜里大姐给我们值班的打了几次铃,听着铃声我们就过去问大姐有什么事。后半夜铃往往就是叫我们提醒总理早点休息或活动一下。这天是我和冯佛成值班。遇到这种时候都是男同志进去。那天冯佛成进去一催,总理把眼镜一摘说:"我休息你替我办哪?"冯佛成没办法,往里送杯茶,递块毛巾,就退了出来。这样只好我出马了。我有另一招儿,人们都知道总理对人是非常客气的,所以我催他,他不理我,我就站着不动,我想总理总不能老看我站在那儿吧?过一会总理一看:"啊,还没走?"我就说:"你还没有活动呢!你不睡,可总得站起来活动一下。""啊,好,好。"说着就从办公桌旁站起来。我清楚地看到总理的手直发抖。那时总理年岁不大,也没什么病,就是拿笔批阅文件,坐的时间太长了累的。真让人看了不忍,他站起来围着办公桌走了一遭,喝了口水,又坐在桌前了。其实也就是应付一下,不然我不走啊!那边邓大姐正在等消息,我就过去告诉一声,总理已经活动了,休息了。至于活动多长时间,是否真休息?也就免说了,否则邓大姐不放心也就无法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