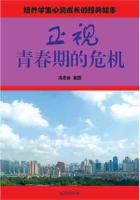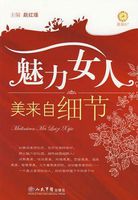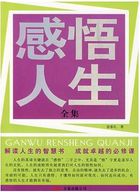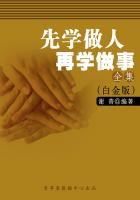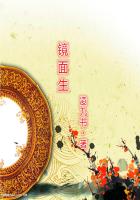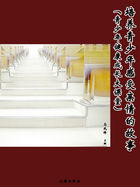"另一次是核对粮食定量的时候,那天总理已连续工作了十七个小时,虽然已经进了卧室,但没有要休息的意思。大家心里都很着急,催几次不行。我进去给总理送药时看见他半躺半坐地靠在枕头上,戴着他那副老花眼镜,正聚精会神地计算什么,身边到处是纸,加加减减的公式和密密麻麻的表格。我本想等一等再说,可想起了大姐的话。大姐说过:有些事别人能做的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于是忍不住脱口说道:"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听了我的话,总理看了我一眼,当时他没说什么,还是在算。我知道,这时候肯定是药也不会吃的。我就往那儿一站,等着吧!就这么过了半天,总理把笔放下,眼镜也摘下来了,他轻轻揉着疲劳的眼睛,面容很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怎么能这样看呢?这可不是个小事,是个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声音不高,因为隔壁邓大姐正在睡觉,但责怪的口气是很显然的。我懂得,那含义就是:"我要说,你真不懂事!"但没有说出来。"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不算怎么知道。"我就看了看,才知道算的是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粮食定量,其中还包括半劳力。那时正是全国遭受自然灾害,苏联又背信弃义停止援助的困难时期,总理是为着怎样带领全国人民度过难关而苦思焦虑的。那时,总理跟全国人民一样过苦日子,瘦得眼窝都陷进去了,还这么操心。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站在那儿无话可说了。总理端起杯了喝了口茶,接着说:"这是关系全国人民的事情,可不是像你讲的单纯技术性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么,所以都应该为人民着想。这个道理你懂,就能够理解我的工作了。我跟你不多说了。"他把我递上的药吃掉了,就又开始工作。总理的话不多,但今后我就把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是不是为人民着想联系起来。"
"还有一次,我去给总理做保健治疗,总理好像正在刮胡子。总理问:"你们青年团是怎样学习雷锋的?"我那时是团的干部,就把我们团组织的计划、设想和活动安排向总理汇报了。总理一边刮着一边听着,然后说:"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到不怕苦不怕累,但要持之以恒可不容易。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他停一会儿,又接下去说:"你们年轻人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也同样要向雷锋学习。"我心想:你还用向雷锋学习么?你不知道要超过雷锋多少了!我想着就脱口说了出来:你还怎么向雷锋学习,现在忙的连睡觉的时间快给挤没了。他放下刮胡刀擦了脸回过身来说:"你坐下,你坐下听我给你讲。你这种说法怎么去做青年团的工作。你这是停止的论点。毛泽东代表中央发出这个号召,不光是对青年人讲的,而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讲的。既然是这样,我怎么就不应学习雷锋呢?向雷锋学习,就是要为人民而加倍地工作,这就是我的理解。尤其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开始不久,虽然有毛主席的领导,但还要靠我们全体人民增砖添瓦。你们年轻人要加倍工作,我们走过来的人也要加倍工作,社会主义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主席给徐老的信你看过没有?""读过。""你把它找出来再读读。向雷锋学习,没有哪些人该学,哪些人不该学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你们年轻人更要多学习、多锻炼、多实践。"我听了总理的话很感动,觉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入死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立下了那么多的功劳,还这么谦虚,这么严格要求自己,我作为年轻的团干部的确应该向老一辈学习,接好革命的班,才能不虚度年华,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
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他的一生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的一生。郑淑云回忆的几个片断,就是他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缩影。
二十五、跟周恩来学处理亲友关系
处理与亲友的关系是为人处世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在处理与亲友的关系时做到了既有情有义但又不损害党性原则,把这两个对立的方面统一了起来,使其高超的驾驭矛盾的艺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周恩来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在于他真诚地关心亲友,对他而言,虽然党性原则神圣不可侵犯,但他可以在不违背党性原则的情况下,竭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亲友。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由衷地赞叹,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在他身上都体现了出来。
周恩来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对他们的至孝亲情却感人肺腑。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为人忠厚善良,不善应酬,一生没有稳定的职业,四处谋生,颠沛流离,生活极不稳定。周恩来因从事革命工作,到处奔波,因而父子俩总是时聚时分,聚少离多。但父子的感情却是十分真切和浓厚的。周劭纲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相信大儿子恩来的选择是正确的,对儿子从事的革命事业从内心来说是支持的。周恩来投身革命,他从不阻拦,但他确实一直为儿子提心吊胆,牵肠挂肚。为此,他关心时事,经常看报,了解共产党的活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他曾两次到上海,帮儿子做通讯联络工作,尽自己的力量为儿子作掩护。
周恩来是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一向很孝敬。1918年夏,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利用暑假回国探望在北京的父亲,并向父亲讲述了自己留学期间的故事。临别时,周恩来依依惜别地写下了这样两句诗:"昨日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1938年,在武汉工作期间,周恩来的工作相对安定下来,他便给正在天津的父亲写信,让他到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周恩来与父亲团聚后,由于工作忙,仍没有多少时间来陪伴父亲。在周劭纲随部队辗转到重庆后,周恩来知道父亲寂寞,曾经对临时在红岩养病的工作人员张颖说:"小张啊,我工作忙,你有空帮我多陪陪老爷子。"周恩来平时在重庆城里曾家岩工作,周末的晚上,回到红岩村过党日。当他经过父亲周劭纲住的院子时,从不忘记去看望一下老人,并告诉他:"我休息了,你有空过我这儿来玩。"然而周恩来何尝真的休息,往往是周劭纲第二天早上去看儿子时,儿子又熬了一个通宵,方才睡下不久。
对老人的身体,周恩来总是记挂在心。周劭纲老人有一个小嗜好:爱喝酒。为此周恩来没少劝过父亲,担心他血压高,喝多了会摔倒,毕竟平时没有人陪他;又担心他喝多了出门走岔了路,下山会被国民党特务抓走。而如果有人打算用公款给老人买一点酒,更要受到周恩来严厉的制止。周劭纲老人觉得儿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让他喝酒这一点他不能接受。
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因小肠疝气发作,住院手术治疗。他虽然整天卧床,行动不便,伤痛难忍,但心里却一直挂念着父亲。他还清楚地记得旧历五月二十八日(即公历7月11日)是生父的68岁寿诞日。他为自己这次不能亲自为老人家操办和主持生日庆典感到内疚和不安。7月6日,他致信邓颖超,托付她来操办。但究竟是于当日办还是等他出院后补办,他请妻子同老人家商量,并希望她尊重老人家的意愿。其实,7月5日周恩来的父亲就身染疟疾病倒了。起初,邓颖超怕他着急回来,影响治疗,一直瞒着他。直到7月9日,老人病情不见好转,邓颖超才写信告诉他。周恩来得知父亲病情后,两夜未睡好,心神不宁。10日,他致信邓颖超说:"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好养病。我在这里默祷他的康宁。"并嘱邓颖超:"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李海文主编:《周恩来家世》,第187页,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2月版。字字句句渗透着对父亲的深切了解和关心。短短数语,周恩来对生父的一片赤子之心,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了。然而,在周恩来给邓颖超写这封信的当天,周劭纲老人就去世了。对老人的去世,大家都十分悲痛,同时又担心如果现在周恩来知道了父亲病故的消息,精神受刺激,对养病不利。于是,董必武与邓颖超、吴克坚、童小鹏等商议后决定,暂时不告诉周恩来,待他出院后再报告。但是,细心的周恩来很快就从邓颖超一连几日不来看他和童小鹏等人的不自然表现中察觉出来,他连连追问,使童小鹏不敢再隐瞒,只好照实说了。周恩来一听他父亲已去世三日,立即惊得脸色苍白,加之他手术后身体虚弱,站不住立即蹲到地上,悲痛欲绝,恸哭不已。回到办事处后,他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他又向邓颖超大发雷霆:"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责问得邓颖超直掉眼泪。当晚,周恩来为父亲守灵至拂晓,虔诚之心,感人肺腑。
17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立即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37页。电报既表达了战友之情,也表达了对周老先生的敬重。
周恩来生前对自己的亲属极少谈到自己的父亲,但每次谈到父亲时总是饱含深情。1964年8月,他对亲属说过一句:"我对父亲是同情的"。1974年春夏之交,周恩来即将住院之前,他的侄子周秉钧从广州出差来北京,去西花厅看望他时,他竟主动地对侄子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对你爷爷是同情的。他人很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李海文主编:《周恩来家世》,第189页。话虽然不多,却情真意切,寓意深长,耐人寻味。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工作人员在为他整理衣物时,发现在他的衬衣口里,有一个很旧的小皮夹子。夹子里夹着一张周劭纲老人的照片。照片大约3寸左右,由于年代久远,颜色已经变黄,但却保存很好,没有一点折损。在照片的背后有周恩来亲笔写的四个字:"爹爹遗像"。从这张保存完好无损,并且一直作为贴身之物的旧照片,不难看出周恩来对父亲的深厚感情。
对自己的三位母亲,周恩来更是充满浓浓的亲情和深切的思念。留日时期的周恩来,在1918年1月2日,曾将深切悼念嗣母陈氏去世10周年的经过写进自己的日记:"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了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不知道还想着有我这个儿子没有。"《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08页。此后,在日记中他还多次写到母亲。他虽身在日本,心中始终挂念着家乡的父亲。每逢新年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他都思亲心切,无限愁怅。时常"想亡母,不能成眠"。他对母亲的生日和忌日,记得都非常清楚。可见母亲在他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1920年,周恩来因领导学生运动在天津被捕,被关在检查厅。他在狱中曾写了《念娘文》,回忆生母万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深情地对新闻记者说:"35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李海文主编:《周恩来家世》,第204页,第205页,第196页,第196页。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对美国记者李勃曼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时说:"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按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七词唱。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又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1950年,周恩来在怀仁堂动员中直干部过好土地改革关的报告会上含着泪深情地说:"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三百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1964年8月,周恩来在与亲属谈话时又说:"封建家庭一无是处,只有母亲养育我,还是有感情的。"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周恩来仍能讲这样的话,足见他的勇气和对母亲的爱。
周恩来还有一位乳母蒋江氏,是位勤劳、朴素的劳动妇女,和周家相处很好。陈三姑去世后,周恩来回到淮安,周家已无钱开工资,蒋江氏仍时常到周家来帮忙。周恩来到南开读书时,蒋江氏拿了"印子钱"(当时淮安一带的高利息借贷)到天津看望周恩来。周恩来请她住在四伯父周贻赓家。回淮安时,周恩来又请四伯父给她买了船票,并送了一只搪瓷缸和一条毛巾。建国后,周恩来还曾向淮安县委负责同志打听过蒋江氏及其后代的情况,表现了她对乳母的深切怀念。
周恩来与妻子的关系更是世人楷模。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这支女学生讲演队是天津爱国斗争中十分活跃、影响突出的一支宣传队伍。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报纸在周恩来主持下,立场鲜明,抨击时弊,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阴谋,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在京、津、保等地声誉鹊起,日销最多时达二万余份,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随着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马骏、谌志笃、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20名男女青年,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由周恩来执笔的《〈觉悟〉宣言》,举起了"革心"(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和"革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两面旗帜,表达了中国先进青年在十月革命启发下,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体现了"五四"时期革命青年。努力向"觉悟"道上走"的进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