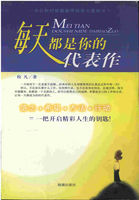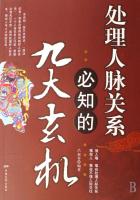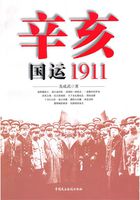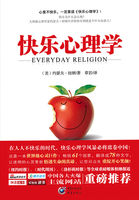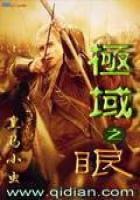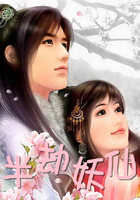更有甚者,是那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利用党内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鼓吹"毛主席是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字字句句都是真理,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这实际上是使毛泽东与人隔绝,架空毛泽东,借毛泽东之名以售其奸。结果使国家、民族的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
周恩来历来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认为崇拜只能滋生庸俗的人际关系。
早在二十年代初,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就提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领袖,不能像教徒对神父、牧师那样,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而应该一方面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面时时监督其行动。周恩来尊重、接受自己的领袖,并坚决拥护、执行领袖的正确意见和主张,但反对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认为个人崇拜只会给上级帮倒忙,使上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从而损害上级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前夕,针对已经出现的神化领袖的苗头,周恩来及时指出,不能"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领袖也是人,"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他还指出,领袖在党内也要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即使有不同意见,"组织上还是要服从。"
在五十年代后期,周恩来对党内开始盛行的个人崇拜现象十分忧虑。1959年,周恩来主持召开全体会议,由冶金、煤炭、机械、交通、商业等部门的同志谈情况,说问题。散会后,周恩来又把计委和经委的同志留下来开了个小会,就在这个小会上,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话:"主度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假思考,以为件件都是主度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开会。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
对于林彪提出的"顶峰论"、"最高指示"这一类言词,周恩来也是听不顺,看不惯的。为此,他多次同毛泽东开诚布公地谈过,也和林彪交换过意见,认为这些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当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迷惑群众,大搞形式主义,制造过多的毛泽东的像章,发行过多的毛泽东著作时,周恩来不客气地批评:"城里有些人有上百个像章,有很多毛主席著作,还不是浪费吗?""现在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铝材用得很多,物资部一发就是5000吨,现在收回没有?应由物资部下命令收回。"他还指示"今年计划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可以考虑少出一些,节省一些原料转产别的东西,如节约纸张和能节约一些碱搞肥皂。"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当时盛行的个人崇拜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
自人群被区分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两部分以来,服从的意识、原则就产生了。被领导者要服从领导者。没有服从就没有领导,没有服从就形不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任何事情都难成就。乐队演奏员不服从乐队指挥,军队不服从指挥员指挥,工人不服从厂长指挥,民众不服从领袖指挥,后果都不堪设想。从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角度讲,社会就是在领导与被领导、权力与服从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周恩来认为在革命队伍中,下级与上级,被领导者与领导者,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上下级关系中的"服从"虽有强制性,但没有统治和压迫的性质。这种"服从"的强制性完全是维护人民利益的需要。因此,作为下级领导者,坚持服从原则,服从上级组织,服从上级领导者,不是奴性的表现,而是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理性行为。
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由周恩来的下级变为上级,周恩来就一直是毛泽东最忠诚的部下,不可缺少的助手和亲密战友,真诚辅助、努力工作,一直到1976年逝世。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心悦诚服地肯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正确的。他说:"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在讲话的结尾,他明确地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才使得党和红军在"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头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周恩来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工作中坚决服从毛泽东的领导,服从毛泽东的指挥,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长征中,打胜仗靠的是毛泽东战略方针路线,周恩来则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具体组织落实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保证了长征的胜利。解放战争中,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事实上成了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主要助手和总参谋长。在这个阶段,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
他做事事无巨细,只要毛泽东需要,他总是尽心尽力去办,而且办好。周恩来从重京回延安时,毛泽东嘱咐他带一些重庆出版的国民党报纸回延安,作为分析形势的参考资料。周恩来率领的车队途经简阳县时,遇上雷阵雨,将车上的行李物品全部打湿了。雨过天晴后,周恩来马上命令汽车停下来,亲自一辆一辆地检查。周恩来看到一捆捆的报纸全淋湿了,十分焦急,立即动手往下搬。他带领大家把报纸一份份小心地摊开晒到河滩上,并和邓颖超一起坐在旁边守护着,直到报纸晒干了,周恩来才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整理好,打成捆搬到车上,并嘱咐大家注意,保护好报纸。
毛泽东定下的路线、方针,作出的指示,周恩来更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并且以身作则,宣传教育广大指战员,引导他们执行毛泽东定下的路线、方针,服从上级的命令、指示。
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来到毛儿盖。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整筹粮,准备过草地。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反对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方针,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公然向党争权,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要求由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对此,周恩来一方面苦口婆心地做张国焘的思想工作,劝张国焘改正错误,执行毛泽东的北上抗日方针;另一方面,向中央建议,把自己原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
然而,张国焘仍一意孤行,并阴谋挑拨红四方面军战士和党中央以及毛泽东的关系。对此,周恩来除了天天参加会议外,还不得不找四方面军的官兵谈心,不辞劳苦地亲自到部队去做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贯彻毛泽东的北上抗日方针。
周恩来从不培植个人势力,不搞小圈子,并从来不搞反对毛泽东的活动。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他从来没有自己的帮派,虽然他拥有为数众多、不是组织起来的追随者。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一批红卫兵把周恩来称为"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头子",还想要揪斗他时,毛泽东表明态度说:"可以,不过要由我去陪斗!"因为他深知:周恩来始终是一个坚决拥护、服从他领导的忠诚部下!
周恩来真诚辅助、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不仅受到党内外同志称赞,同时也在国际上传为佳话。英国记者约翰·美德施在《周——中国传奇式人物周恩来非正式传记》一书中写道:"周、毛的合作关系,无论就经历年代、亲密程度、历史重要性来说,在中共党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他们的伙伴关系长达40年之久,这种关系是坦率的,也是有创造性的。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人民共和国诞生和存在下来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原则上讲,下级服从上级是一般人都能接受的。但是,当对上级的决议、指示有不同意见时,怎么办呢?周恩来的做法是:一方面积极向上反映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在上级领导者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修改决议指示之前,仍要按原指示决议执行,在执行中积极采取措施,把可能造成的损失减到最低程度。三十年代初期,周恩来担任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那时正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盛行的时期,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博古等人,大都是些脱离实际的书生,对革命实践尤其是对军事斗争几乎是一窍不通,作战指挥上的事,都由李德说了算。而李德虽然是苏联军事学院的高材生,但他除了会背一些外国军事教条外,只在苏联指挥过骑兵,对我国国情及我军作战特点等等都不甚了解,再加上李德等人仗着有共产国际和王明的支持,专横粗暴,目空一切,从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同志,到初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很多人都受到过他的挑剔责骂,甚至处分判刑。在他手下工作的许多同志都非常生气窝火,称李德为"帝国主义分子"。对于这样的上级,周恩来仍然保持对他们组织上的服从和尊重,但从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他又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设法弥补博古、李德等瞎指挥造成的漏洞,尽量减少以至消除可能的损失。正像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所说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周恩来同志这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高度品德修养的人主持日常工作,形势发展很可能更坏。"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又被推到了一个类似30多年前在中央苏区时那样相当为难的境地。他同党内绝大多数同志一样,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反动行为和罪恶勾当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这场运动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和领导的,他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不得不在组织上表示服从。特别是林彪、江青之流抓住他在遵义会议以前一度服从、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要挟他不能再"反对毛主席",他只得尽量克制自己,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尊重他作出的决定,为顾全大局而暂时委曲求全,力求缓和可能引起的党内冲突。他的一贯的善良厚道也曾经被别有用心之徒所利用。例如江青,此人本来缺德少才,党内早有规定不许她干预政治,但是,康生、陈伯达和林彪等人,企图利用江青达到自己的目的,便用各种方式为她吹捧抬轿,处心积虑地要将她推上政治舞台,迫使周恩来接受并同意他们的主意。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时只得违心地表示了认可。结果林彪和康生等人就用政治局大多数同意为名,取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使江青跳了出来,致使在我党的光荣历史上留下了她肮脏的印迹。
服从与盲从虽一字之差,意义却大相径庭。盲从是对上级的指示、决定,在不理解领导意图的情况下一味附和,一概听从,一律执行的盲目行为。盲从往往给上级帮倒忙,因为任何天才的上级都难免犯错误,下级的盲从只能使这些错误得不到改正,出现错误,反过来必然影响上下级关系。
早在二十年代,周恩来就提出: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受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只知盲从的党员。1928年,为了贯彻党的六大的决议,他提出要坚决反对"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的封建家长制形式。指出:这种命令委派的家长制,"会使党的肌体日益腐化,永远没有生机",还会形成由私人感情的结合,或部落的观念形成的小组织倾向,分裂和涣散党的组织。所以,周恩来处理与上级关系的做法是:坚持服从原则,绝不盲从,即使上级领导者的指示是正确的,也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不做"传达室"、"传话筒"式的领导干部。
五十年代中期,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三大改造也进展得出人意料的迅速和顺利,使毛泽东和党内许多领导的头脑发起热来。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并强调在各项工作中反对所谓右倾保守,反对"小脚女人"。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写道:"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总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总是止步不前,总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后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毛泽东进而提出要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工业、农业、交通等各行各业都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导致了1956年的冒进。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并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做,相反,他却一再告诫全党"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应小心谨慎","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特别强调指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工业化不能提早完成。"周恩来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深刻指出: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也"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还需要工业化这个根本条件。工业化则"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而只有实现了工业化后,三大改造的成果才能"真正巩固"。"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能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周恩来认为,要"建成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和贫困","照列宁说的还要消灭愚昧,还要文化的高潮"等等。可见,提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