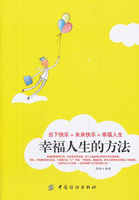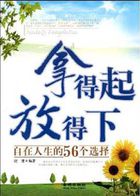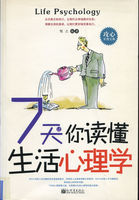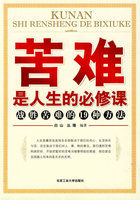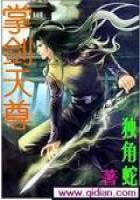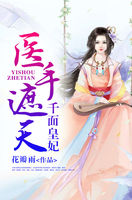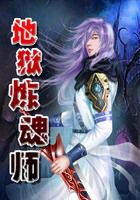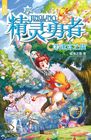毛泽东不停顿地促"进",周恩来并未盲从,而是根据客观实际促"退"。1956年2月,周恩来着手解决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存在的冒进问题,他说,既然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不切实际,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对严重脱离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削减。周恩来称之为"二月促退会议"。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磋商编制一个符合实际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新方案问题。在这之前,已经制定过两个方案,周恩来提出,第一个方案冒进了,第二个方案也冒进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提出一个"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新方案。这是又一次把高指标大幅度往下降的"促退会议"。结果才有一个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至1962年)的建议》和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不断冒进的大趋势下幸运地诞生了。它们为二五计划期间的建设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正是由于周恩来一再"促退",不肯盲从,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被毛泽东指责为"反冒进",并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离右派相差只是五十步、一百步。"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被上升为政治路线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并不一意孤行,背着组织另搞一套,而是服从上级,服从组织的决定,写出书面检查,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在接着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虽然无法从正面大刀阔斧地抵制这场错误运动,但他仍利用一切时机缓解"大跃进"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在"大跃进"已经造成了极端严重的不堪收拾的后果,并逐渐被全党所认识的情况下,他挺身而出,力挽危局,纠正错误。他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使国家经济建设重新走上正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年代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并不完全都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是坚决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正确指示,并尽可能加以发挥,对错误的部分则不盲从。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自己手中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的"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使这一口号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成为"抓生产"的同义语。对毛泽东"左"的思想,周恩来总是在可能的限度内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尽可能从积极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专门找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说是"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么?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周恩来就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减少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击力。
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处理与上级关系时,坚持服从,但又绝不盲从的原则,才使我们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识大体、顾大局,使局部服从全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小原则服从大原则,这是周恩来在处理同上级关系时一贯遵循的原则。遵循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就是要积极支持上级的工作。首先,想问题办事情不能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把局部、眼前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应从全局出发。当局部利益与大局利益发生矛盾时,要舍得放弃局部利益,甚至牺牲局部利益以顾全大局利益,要有"舍车马保将帅"的精神。其次,要努力做好自己所领导的工作,以局部工作的成绩和取得的良好效果为上级领导全局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全局工作。其三,要正确维护上级的权威。对上级的指标,只要没有原则错误,都应当贯彻执行。要正确对待上级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背后议论上级,贬低上级。要积极支持、热情帮助能力比自己弱的上级。只要他没有离开领导岗位,就应从全局出发,执行他的正确指示,尊重他的领导地位。
同时作为领导者,要不仅善于处理和上级观点一致时的上下关系,还要善于处理和上级观点不一致时的上下关系,这也需要下级领导者识大体、顾大局。周恩来在处理与共产国际这个特殊上级的关系的事实,就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高贵品质。
1930年,周恩来、瞿秋白按照共产国际7月指示信,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稳当妥贴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弯子,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全党可以再图恢复和发展了。
然而,就在中共中央8月1日、3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送到莫斯科后,共产党国际执委会对于李立三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到要把苏联卷入战争等内容,十分恼怒,一反前态,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并于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指责李立三是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反国际路线,进而批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这样,周恩来、瞿秋白一系列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措施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就处在了被批判的地位,正确变成了错误,忠实贯彻共产国际的7月指示信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周恩来所受的委屈够大的了,然而,还没完。共产国际的10月指示信,中共中央是11月16日收到的,而在此之前,王明就通过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盛荣、陈昌浩获知共产国际对立三错误和中共中央的新看法,于是王明一改原先支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态度,认为时机已到,大有可为,在党内发动一部分人与中央对立,攻击党中央和六央三中全会,制造派别斗争,搅乱党的思想和组织,并和何孟雄、罗章龙等联合一致,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因而,周恩来的工作更加困难。
尽管周恩来认为前段工作是实事求是、正确的,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仍承担了责任,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是"取了调和态度",但申辩说:"三中全会一般地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会议对王明等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进行抵制,批评他们先于中央知道10月来信的内容后,不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和请示,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立三路线问题和调和问题,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然而,王明由于有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反中央的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厉害,中共中央已不能有效地对全党实行领导。周恩来到处谈话,做工作,还是不能平息风波。王明一伙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对准瞿秋白、周恩来,企图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当时党确实陷入了一场即将分裂的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一旦出现这种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此时,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成为当时党面临的全部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他没有再做什么辩解,不是去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他为避免党的严重分裂,一方面承担了所谓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并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对于王明反对中央的非组织活动,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要求党员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来做工作,不允许采取搞分裂的方式。他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劝他们不要义气用事,而应转变态度,在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避免党的分裂,帮助党渡过难关。出于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的考虑,周恩来还和瞿秋白一起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
然而,对于周恩来、瞿秋白的辞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采取了拒瞿留周的方针。米夫说:对周恩来是要批评,但不是要他滚蛋。王明也就宣称:为的是实际工作便利和给周恩来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不是米夫、王明对周恩来的偏爱,而是党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正如六届四中全会上有的人发言说:周恩来是党内的人才,他的艰苦耐劳的精神,他在军事上、组织上的才能,是否还有第二人呢?
周恩来的辞职未获批准。瞿秋白对他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为了党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处境维艰,周恩来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忍辱负重,继续工作下去。当时,立三错误已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党亟须稳定团结,再图恢复,而王明等人又搞得党内一片混乱。由于王明等人上台,有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党员十分不满,自动离党了;有些党员动摇了;有些党员变得消极了。在此严重形势下,周恩来内心充满苦闷,为了党而拼命苦干。有他在,由于他的威望,一些党员才认为党中央是真的中央而留在了党内。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尽管自己处境艰难,他仍然发言指出:如果认为"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点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他极力保护和团结尽可能多的同志,使党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对此,周恩来又做了大理工作,找他们谈话,要他们立即停止分裂党的活动,承认错误,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并告诫他们,分裂党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经过艰苦的努力,党终于从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中摆脱了出来。在1930年这段极其复杂艰难的历程中,周恩来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表现出他坚强的党性。1972年,周恩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仍痛定思痛地说:那时的情况已是中央破产、党内分裂,自己工作得焦头烂额,舌敝唇焦,当时的心情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没有人不想处理好与上级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处理好与上级的关系。周恩来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处理与上级的关系,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方法艺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而巧妙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除了坚持尊重而不崇拜、服从而不盲从、局部服从全局之外,还要体察入微,巧妙处事。
下级领导者主动关心爱护上级,也是处理好与上级关系所必需的。上级领导者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需要关心,需要感情,所以,下级领导者如果尽可能地关心上级,以"情"来感动上级,这无疑对融洽上下级的关系很有益处。当然,这种真诚的爱和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之类是毫不相干的,他们的区别是前者从大局出发,经得住考验,后者从自己个人利益出发,经不起时间考验。
周恩来与毛泽东均堪称中国和世界杰出的领袖人物,然而在一个国家同一代领导人之间,像周恩来对毛泽东那样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全身心地保护毛泽东,确实是极少有的。
自从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从实践中确信毛泽东是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他便甘居辅助地位,以自己的整个身心来维护毛泽东的领导,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并为此创造良好的条件。
长征途中,有一次周恩来发现有几个人在吃白面,他就问:你们从哪里搞来的?毛主席几个月没有吃过一口白面了,你们还有没有?赶快给毛主席送点去。毛泽东骑的小黄马到陕北后不久就病死了,贺龙得知后,就从蒙古族人民送给他的好马中选了一匹枣红马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看这匹马性子很烈,就叮嘱警卫班战士用心调训。直到调训好了,他自己亲自经过试骑,才完全放心把马给毛泽东送去。
1945年8月,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要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行前,周恩来就电告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对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饮食习惯等都作了具体的指示。登机前,周恩来又要警卫人员到机上检查毛泽东的座位和安全带,后来自己又检查一遍,并交待警卫人员:到重庆后,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一点疏忽。到重庆的当天晚上,国民党当局把毛泽东和周恩来安排在两个住处,周恩来非常警惕,他坐在毛泽东卧室隔壁的房间里,以办公为名,亲自保卫毛泽东,彻夜不眠,直到天明。在重庆期间,只要毛泽东外出,周恩来都要亲自选定行车路线,一同前往,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
在公开露面的场合,周恩来总是寸步不离毛泽东的左右。一次,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里住了一天。一到那里,周恩来就嘱咐警卫人员:要仔细检查,各个角落都要查到,看有没有爆炸品和易燃品等等。警卫人员检察后,他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床上、床下、枕头下都看过,在椅子上也先坐一坐,然后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住下后,他又嘱咐警卫人员,保证房内不能离人,不要让别人进来。在宴会上,人们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怕毛泽东健康受影响,就毅然代替他,饮完一杯又一杯盛情难却的酒。在重庆,周恩来除了帮助毛泽东处理日常繁重的工作,每当毛泽东睡下后,他总要召集会议,检查布置第二天的工作。为此,他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决定返回延安,蒋介石要用他的专机送毛泽东,周恩来对此十分担心。当张治中先生无意中透露蒋介石要他11日乘飞机去兰州时,周恩来感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请张治中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延安,再去兰州。张治中答应了。这样,毛泽东在周恩来细心周到的安排下顺利地回到了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每次检阅、开会或有重要活动,凡是毛泽东要出席的,周恩来总要对场地、道路、设施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连地毯平不平、地板滑不滑、椅子稳不稳……都要亲自走一走、坐一坐,直到万无一失才放心。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发现毛泽东要经过的一个门槛有暖气回水管,便立即嘱咐身边的警卫人员守在门槛边,防止毛泽东到这里绊倒。周恩来走了后,警卫人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服务员,自己就跟周恩来去了。周恩来一见他,就赶快让他守在那儿等候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