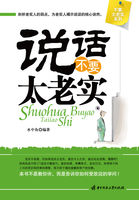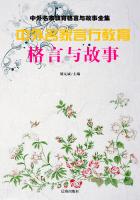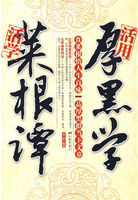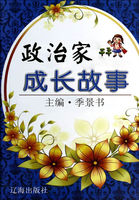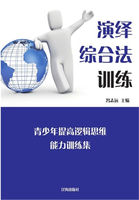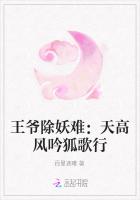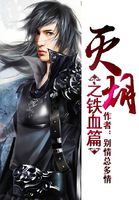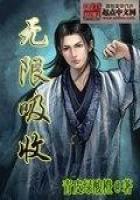美国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强国,手里握有原子弹,充当着国际宪兵的角色。1950年他纠集了十几个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气势汹汹地越过三八度线,直逼鸭绿江边。而中国经过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一直没有喘息机会,真正是"国是弱国,兵是疲兵"。对于美国燃起的直逼家门的侵略火焰,怎么办?是放任不管坐视不理,还是起来应战,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先是发出警告:我国和邻邦朝鲜是"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对于美国的侵略"不能置之不理"。警告无效,中共不惧敌人的强大,果断地派遣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这叫"行于所当行"。抗美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体现了爱国主义;援朝则是协助邻邦赶走闯进家门的强盗,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任务。于情于理,于人于己,都是义不容辞。如果在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软弱怯懦,迟疑退缩,则朝鲜不保,新中国不被侵略者所扼杀,也将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协之下,无法进行和平的建设。针锋相对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予以打击,让他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
中朝英雄儿女并肩作战,使侵略者伤亡惨重,他们被迫求和停战。中国怎么办?是继续打下去呢?还是把战争停下来?毛泽东、周恩来等审时度势,考虑到侵略者已遭到沉重打击,而我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进行经济建设,应该适可而止。于是通过和美国进行停战谈判,最后实现了停战,这叫"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果当时不止,战争长期延续下去,我国人民长期承受战争的负担,是不符合我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意愿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的。
在处理错综复杂的事务时,有时不能在行与止、为与不为、说与不说中作简单的选择,还有一个行到什么地步,为到什么程度,说多说少的量的掌握问题。只有进一步掌握量的分寸,才能真正做到行止适宜。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一方面积极起来抗战,另一方面仍在坚持和实行许多错误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在负责处理国共关系的过程中,既坚持和其错误的方针政策作斗争,斗争时又善于掌握分寸,做到了恰如其分,适可而止。
1937年10月下旬,日军占领武汉后,继续驱兵南下,十一月十日岳阳沦陷,长沙告急。在长沙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及要员,纷纷从长沙撤退。正在长沙的周恩来,准备十三日离长沙去湘潭。谁知十二日深夜,长沙城突然四处起火,火焰蔓延全城。周恩来等从火海中冲出,步行出城。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长沙大火"。
蒋介石不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抗战,在一败再败之后,大肆宣传所谓"焦土抗战",并于十二日上午密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要求焚毁长沙城。长沙军警负责人根据这一部署,又误信了日军已逼近长沙的谣传,下令纵火。其实,当时日军尚在几百里之外的岳阳,没有什么动静。据不完全统计:大火毁房五万余幢,约二、三十万居民无家可归,死二万余人,伤者无法统计。
十四日,周恩来、叶剑英赶到南岳,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周恩来就长沙大火问题,对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进行了坚决而又有分寸的谴责。国民党宣传机器把长沙大火说成是中外战史上最常见的"坚壁清野",因此,"坚壁清野"成了掩盖蒋介石罪行的遮羞布。撕掉这块遮羞布,长沙大火的罪责该谁承担,就不难看清了。周恩来没有直接点明蒋介石是长沙大火的主犯,而是从正面驳斥把长沙大火粉饰为"坚壁清野"的荒谬说法。他说"坚壁清野"是一项最深入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同仇敌忾共同制敌的工作。必须极端关心和照顾群众的利益,关心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必须尽量使他们少受损失,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使他们愿意牺牲个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现在放火烧长沙,事先不动员,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起火,烧死多少居民,焚毁多少公私财产!侥幸逃出火海的人,深冬腊月无处安身,无衣蔽体,也将冻死饿死。这种便宜了敌人,牺牲自己的做法,绝不是什么"坚壁清野"的做法。最后他提出了三点善后办法:拨款救灾,安置灾民,惩办放火首犯。
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蒋介石面对周恩来义正辞严又留有余地的谴责及合理的要求,虽然羞愤和不满,但也无力辩解,不得不采取了一些紧急处理措施:拨款五十万元,救济灾民;调集五千民工清理街道,搭盖窝棚,安置灾民;几天后下令枪毙了他的替罪羊——长沙警备司令邓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三人。
从南岳回到长沙,周恩来亲自领导政治部三厅人员所组成的善后工作突击队,投入灾民的救济和安置工作。当他发现有的同志写标语、出壁报不愿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时,他问:"为什么不愿意写呢?蒋介石不抗战到底,我们就不拥护他嘛 ,现在他还讲抗战,又枪毙放火的邓悌、文重孚、徐昆,拨款救济灾民……对打击投降派,支持抗战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嘛。"
蒋介石是下令放火者,是罪魁祸首,周恩来不公开正面地揭露和谴责,而侧重于驳斥"焦土抗战"的谬论,并要求"拥护蒋介石抗战到底"。多数同志能领会并佩服周恩来高超的斗争策略,但也有少数同志不理解。叶剑英对他们解释说:"没把蒋介石揭出来,是为了继续拉他抗日,孤立投降派。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就希望我们和蒋闹翻,他们好从中得利。要是把蒋介石揭得太厉害了,他恼羞成怒,我们连长沙的善后条件也争取不到了。那样做,对全国抗战更不利。"周恩来也简明地道出了他从抗战大局出发的一片苦心。他说:"为了继续团结蒋介石抗日,才没有戳穿是他下令放火的。"
对顽固派需要斗争,又要团结,斗争不能一斗到底、逼得他无路可走,而必须留有余地,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一斗争艺术,周恩来在抗战初期已运用得十分出色。
和顽固派的斗争要适可而止,说话写文章也要讲究分寸。说与不说,说到什么程度,要看对象和条件。该说不说,无法成事,不该说的说了,则可能败事。周恩来在重庆曾给《新华日报》提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办报原则。
那时,正值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中共代表团及《新华日报》的工作受到严厉的监视和限制。如何在这国共关系面临破裂的危急关头坚持办报,坚守阵地?周恩来认为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说:"《新华日报》要成为"大后方"人民的喉舌,要敢于说出真理,也要善于说出真理。"他指出:凡是宣传马列主义,报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斗争,颂扬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揭露国内外反动派破坏抗战的阴谋的,就坚决"有所为"。要是敌人想利用我们报纸来为他们说话,我们就坚决抵制。有时考虑到策略上的需要,一些话需要等待时机再说,就坚决"有所不为"。
周恩来对《华华日报》的领导非常具体,他亲自审阅报纸社论和重要新闻,并自己动手写社论、专论及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同时他又讲究策略,注意分寸,斗争时不忘联合,揭露是为了抗战。蒋介石视《新华日报》为眼中钉,但始终找不到将它扼杀的把柄和藉口。
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因此不能搞绝对化。必要时,静中有动,止中有行,不为中有为。周恩来处理中日贸易问题时,就曾提出"断而不断"的斗争策略。
1958年3月签订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受到了岸信介政府的破坏,岸信介本人曾到台湾、美国等地活动,多次公开攻击中国,甚至扬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58年5月,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日本暴徒撕毁中国国旗。对这一侮辱中国国旗的政治事件,日本当局竟作为"毁坏器皿"案件草率处理,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愤慨。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停止签发对日贸易许可证,中日贸易一度陷于中断。
但是,中日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中日经济贸易是相互依存的,将来是要发展的。周恩来指出:"这个大势是不可逆转的。现在看来免不了要争论、要吵架了,可是你们绝对不要把这个窗口堵死,不要把话讲绝。"
为了孤立日本反动势力,争取广大日本人民,在贸易中断期间,周恩来仍然时常去会见日本朋友,关注日本形势的发展。当他了解到日本某些依靠中国产品维生的中小企业,例如漆器行业、糖炒粟子零售商等,由于中国商品货源断绝,企业濒临倒闭,生活十分窘迫,热望中国给予照顾时,就指示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以"照顾物资"方式,对日本中小企业进行适量供应。这就是对日本贸易"断而不断"的策略,从整体看,中日贸易中断了,但又保持着一股涓涓细流,当后来形势变化,正是这股细流,经过日积月累,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立友好关系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