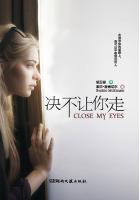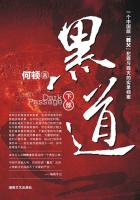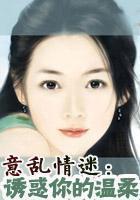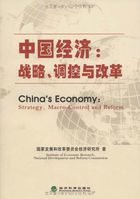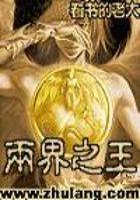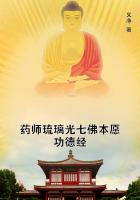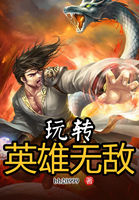那群女人笑闹着走了,段良弼总感到她们中间有自己熟悉的某个女人的影子。
早上一出门,他就有这种感觉,现在越来越强烈。他不知是祸是福。从遥远的江西到上海,他应该是举目无亲,难道是中央派出来暗中保护他的?他惶然了,他不值呀。
天还是那么蓝,海还是那么蓝。天空蓝得透明纯静,浅浅的云在上面飘,海蓝得深沉中带着种神秘的黑色,海天相接处一片混沌,间或有一两只鸥鸟鸣叫着飞起,叽叽喳喳尖锐的叫声像婴儿病中的啼哭,有气无力的抽泣中不时杂几声尖嚎,平静就被打破了。
从那天起段良弼就养成了每天看海的习惯。在海滩一混就是半天,下午就回去等消息。
他不知道,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在他到达上海之前,中央已经根据其他方面传来的信息,在2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过一项决定。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他们决定停止一切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这个“一致”,当然指的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总前委和江西地方党和军队的“一致”。他们还采取了限制毛泽东的组织措施。
不过到了2月23日,随着李立三在中央失去职位,中央又推翻了以前的决定,重新支持毛泽东,支持他肃清“AB”团。
前前后后总共只有10天时间对江西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有利。
从张国焘写的回忆录中间,我们可以发现李立三的沉浮对江西问题的解决关系很大。他在书中写道:
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向忠发一直担任总书记,因为他无能,他几乎被人忘记了。李立三任宣传部长时,中共中央的大事大多由他决定……
李立三得着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励,也在中共内依样画葫芦干起来,他开除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以请共产国际纠正蔡的右倾为理由,将蔡送到莫斯科。
……
十一月中旬,李立三开除了陈独秀先生的党籍。
也许,他还计划着开除不听话的毛泽东。
李立三也许是自负无敌于中国了,他的剑锋又指向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起初是指德国籍的两个代表为右倾调和派,接着他的刀光剑影又落在米夫头上,他对米夫在政见上虽然无显著的冲突,但对米夫所卵翼的陈绍禹等人,则视为是右倾的敌人,不客气,给予打击。到最后,图穷匕现,他竟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是他所要反对的右倾对象。
从江西发生的一切和段良弼所交的申诉材料分析,他们当时执行的所谓中央指示就是立三路线,主张攻打大城市南昌,“以一省乃至数省的革命暴动的胜利换取全国的胜利”。而李立三的“天才计划”就是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外蒙进攻京津,来配合他夺取武汉。这个计划当然激起了全党同志的反对,共产国际也极为愤怒。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对于这个“省行委”,没有现代历史知识的人是不会重视的,普遍认为不过党的一级组织而已,读书时一晃而过,没有引起重视。
“行动委员会”是立三路线的具体产物。
李立三在一九三0年的六七月间,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大好,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临,就命令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各种组织如中共、少共、工会、农会等混合起来,打乱原来的组织系统,重新组合成行动委员会。所谓“行动委员会”,说白了就是“暴动委员会”或“暴动指挥部”。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它的领导成员全部由李立三自上而下指定。
中共部份同志认为:李立三根本违反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等于取消了共产党的经常工作,此风波及少共和工会等组织。
张国焘说:“不少同志形容李立三粗枝大叶,他从前搞职工运动时候,老是打冲锋,放大炮,刘少奇总跟在后面替他收拾烂摊子,发今他坐上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宝座,仍然一味唱黑头,周恩来跟在他后面埋头苦干。”
一九三0年九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李立三也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
三中全会表面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实际上李立三瞿秋白等仍然控制着中共中央,当权如故。共产国际觉得立三路线很顽强,采取了进一步干涉中共的手段,一方面调李立三到莫斯科,一方面策划举行四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
此时的王明(陈绍禹)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四处积极活动,力图进入中央。
那已经是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事了。
三一年一月也是段良弼带着黄金和告状材料到达上海的日子。
他根本不了解中共中央上层正在进行着的变化与改组,依然老老实实在租界里那家旅店等待着,期望中央对富田事件有个公允的说法,他好回去对同志们有个交待。
十来天无人过问使段良弼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心里微微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外滩成了他唯一寻找藉慰的地方。
背后是川流不息的汽车,尘土遮天蔽日,各种各样的汽车喇叭声时断时续,象征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那幢银行大楼富态地立在那里,象个永远不知饱足的饕餮汉子,腆着大肚皮双目望着海滩上游人的后背。那一大片连在一起的建筑物露出黑洞洞的窗户,象农村人在土墙上贴的一个个牛屎饼子,天一黑,那些牛屎饼个个发出亮光,又变成了墙角里倦曲不动的癞皮狗的眼睛。
最引人心动的还该是那片水平如镜的大海。
吴松口风平浪静,要流入海的流量那么大,水下的激流的力量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段良弼感到自己处在一种暗流之中。
背后那片黑压压的大厦使他想起了故乡的屋子,那些一般不装窗户室里黑漆漆的房子。小时候一读到古书“瓮牖绳枢”,他就会想起邻居们那些在屋顶安装的亮瓦(实为曲体玻璃片)天一阴就黑沉沉的房间,总感到象蹲在监狱里一般,就问大人为何不照古人说的用瓦器做个窗户,爷爷就捋着胡须笑,笑完了就说:“傻小子,古人还说过‘黑暗纳财’哩。”
看来古人早就说过,要想整弄钱,须得是在人看不见的地方,你看不见别人,别人同样看不见你,金钱交易中难免带着血腥和肮脏,眼睛看不见过程,钱也就算干净了。最好是交易时闭着眼连自己也看不见自己,那才叫干净,彻彻底底的干净。
段良弼不知道自己带给中央的钱干净不干净,它们反正来自当地的土豪劣绅,收缴时带点命债是常见的事,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嘛。使他感到不安是这些金子是红二十军的命根子,他们几个干部是硬从广大战士和干部嘴巴里抠出来的呀。他把黄金捆上身时几个头头看着他,大家都没出声,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这叫献金赎罪,背后有人说这叫向中央交罚款,反正是希望从轻处理的意思。段良弼觉得很不舒服,可又不得不做,所以他觉得自己很脏,很卑下,他原本不是这样的人,近来不知怎么就变了。
小时候他的爷爷和教书的先生从来就教的是另外一套。《百家姓》、《三字经》即便倒背如流,也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先生照例是不解释的,只是拿红笔在书上画圈儿,规定当天要背的任务,完不成或背不到就挨手心,打得手心的肉肿起老高,那个痛呀,至今想起还撕心裂肺的。
当然也有欢喜的时候。
他忘不了七岁那年的中秋,那年的月光特别明亮,他和七八个小伙伴悄悄走到竹林里,捡了好多烂瓦片,小心翼翼砌了个瓦塔。你可以想一想,用不规则的瓦片轻手轻脚地搞整,你一片我一片,倒了又建,建了又倒,搭到后半夜才弄成,他们那个激动呀,又是唱又是跳的。后来记不清是谁出的主意了,孩子们又捡了好多枯黄的竹叶堆在塔身上,点火一烧,瓦片又恢复了原来在瓦窑里的样子,全身透亮通红,通塔散发着金黄透红的光芒,漂亮极了,简直成了道壮丽的风景。
这是家乡的风俗,年年中秋都有小孩玩,一拨小孩长大了,自然有下一拨接着干,大人说那能去晦气,来财运。
那年他们和往年玩的都不同。
孩子们不断地添竹叶,可是竹叶毕竟有限,后来添的叶子少了,火就小了,瓦塔也不那么亮了,他们就怂恿良哥儿去偷他家的煤油,全村有煤油点灯的只有几家,其他的人家晚上不点灯,偶尔点一下也就是就地取材的桐油果、松明子等。他记得摸回屋时全家都睡了,他就拿家里过年盛炖鸡汤的大盂盆偷偷装了一盂盆煤油,一到竹林坝,就有孩子争着用破瓦片去舀油,油一倒在烧红了的瓦片上,“哄”的一声火焰冲天,孩子们不停地倾倒,火就不停地燃,火苗不停地跳动,火焰阵阵上窜,不一会塔身就变得通红,经永不变。从那以后,等到所有孩子长成了大人,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过那么亮的塔。
爷爷说那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用煤油烧过瓦塔。
爷爷说只有干惊天动地的大事的人才有气度用洋油烧瓦塔。
当段良弼从省城念书回来把已不富有的家产散给穷人组织游击队的时候,爷爷已经病卧床塌,奄奄一息了,他仍然捋着胡子笑,说我孙儿有出息,他又在用家里的洋油烧瓦塔了。喝醉洒的父亲要放泼阻止,爷爷叫住儿子,说良哥儿天生一个异物,你莫去拉,如果改朝换代,他要大红大紫哩。
爷爷到死都记着良哥儿抓周抓了个红顶子。
母亲看着儿子的所作所为却另有顾虑,清亮的眸子里总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云翳,爱怜和关切明明白白写在脸上,却一句话也没表达出来,她一直怕孩子出事。打小良哥儿体质就弱,母亲怕他养不大,好容易读了书成了人,又干的是反官府杀头的事,真是拿到手上怕摔了,含到口里怕化了,儿行一步娘担忧呵。
娘的担忧也是有道理的。
记不得是几岁了,大约是刚学会走路不久吧,也是一个风清月白的中秋之夜,娘说良哥儿乖,良哥儿回家去拿个碗,娘口渴,要喝水哩,良哥儿乖,去吧。
良哥儿从小就听话,回身就甩起胖乎乎的小手蹒蹒跚跚从家里取了个茶杯回来。娘从乌黑的头发上取下一枚亮晶晶的针,交给儿子说,把针找个地方放下,然后把茶杯翻过来罩住它。
良哥儿找了个有野花的地方,把针插在颤巍巍的花朵上,再把茶杯盖住野花。
娘抱起良哥儿轻轻地摇晃,唱起了从她的母亲口里流传下来的儿歌,儿子在娘的怀抱里象坐上了只顺水飘流的船,只觉得月亮好大好圆,在母亲的歌声中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早晨星星消逝得差不多了,娘推醒熟睡中的儿子说:良哥儿乖,是时候了,你揭开茶杯看一看。
良哥儿还没醒,闭着眼还要睡,无奈娘一直在拍在劝,只好揉着眼去揭茶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