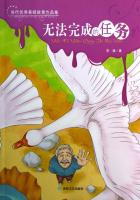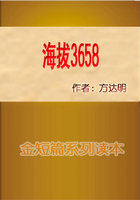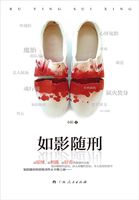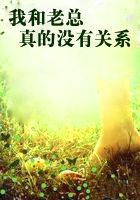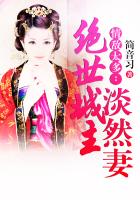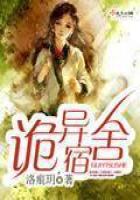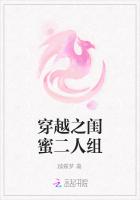段良弼向中央汇报,从胯裆时掏出充满尿臊味的黄金。
中央的决定十天之后竟然判若天渊。
段良弼得女人指点消逝在历史深处,中断了他的革命生涯,却免除了杀身之祸。
上海。一月的冷风从海面吹来,易尔士觉得很冷。天上的云一团一团的聚集,令人想起刚在南方听到过的谚语,“天上砣砣云,地下白骨生”。那片被血与火洗过的贫脊土地上常常有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在唱,有垂死的老人扁着没有牙齿的嘴在念叨。易尔士有些无奈地对分手告别留下等交通员安排的段良弼道了声珍重,说富田发生的情况我会原原本本向中央写出汇报,我这方面你放心,你自己把省行委的汇报材料整理好,估计要不了几天,中央自然会派人来找你的。
后来易尔士果然做到了他说的话。
不过事过境迁,他说的什么写的什么都不重要了。
易尔士临走时还给段良弼买了个柳条箱,就是那种用藤条编的漂得白白生生的箱子,又大又轻,表面很华丽,各种阶层的人都可以用。
有人带着他走过大马路,绕过很多石库门插进一条横巷,到中共中央在重庆路英租界租的一层楼的房间里安顿下来。
没几天房间里来了两个人。
领头的那人三十岁的样子,一幅厚底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鼻子下边是刚刚刮过胡须的上唇,由于原来的髭须浓黑,在上唇留下隐隐可见的淡色的粗毛孔,因此显得老成持重。他就是刚从敌人监狱里出来不久的任弼时同志,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当时简称少共书记,最近新增补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紧跟进来的是个单薄瘦削的青年人,一看就斯斯文文的,有幅学者或者诗人的作派。他刚从俄国中山大学留学归来,担任全国总工会干事,正在编《劳动报》,中央有意让弼时同志带带他,所以他也来了。他叫秦邦宪,就是后来党史上大名鼎鼎的博古,不过他当时锋芒未露,是作为任弼时的助手来的。
房间里一共只有两只老式茶杯,有一只还没有盖子,段良弼为了礼貌,两个中央大员一进房就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开水,一人一杯白开水。段良弼没有钱买茶叶,茶叶从清初起就是一种奢侈品,一个等待中央处分的干部是不敢享有的。任弼时本身就有肺病,又两次坐过敌人的监,因此理解段良弼的处境,很带同情地看着段良倒水时有点颤抖的手,看他小心翼翼轻手轻脚的样子,任弼时心底升起阵怜悯与同情,冷冷的目光里却什么也没有表露出来。
秦邦宪年轻,又刚从俄国回来,他有点计厌那旅店的带油渍的家什,他不习惯唱白开水,他吃惯了俄国的黑面包干,喝惯了红菜汤,虽然说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毕竟习惯了的,汤里头总浮着几片菜叶,开水里什么也没有。
段良弼一个人在讲。
他感到了天堂里最后的审判那种逼人的气息,虽然还谈不上审判。面前的铁面人进屋自我介绍以后就没开过口,他们只是听。
段良弼就讲。讲得他自己浑身不自在,全身有汗不知不觉涌出来,像虫在身上爬,难受极了,一点也没有受了委曲见到母亲那种感觉。在没有见到中央来人以前,段良弼确实感到满怀委屈,像在外受了欺负的孩子,千方百计要回家寻找母亲,寻找庇护。见到中央来人,他才清楚地意识到他不是母亲唯一的儿子,与他斗争的另一方同样也是母亲的儿子,母亲决不会因为哪个儿子抢先告状就偏袒他,护佑他。他甚至感到母亲的处理不一定会依照公允、天理,而是会想方设法照顾两个儿子的利益,不会让其中的任何一个吃亏,心里又祈祷但愿如此。
他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正确不正确,只是感到讲得很难,几次无意识地停下来,把混乱的思维整理得有条理了再讲。
秦邦宪用本浅绛色的拍纸簿记录着,鼻头上微微冒出汗来。
任弼时佝偻着腰,双手缩在棉衣袖口里,脸上毫无表情,只有一双眼睛在厚玻璃瓶底一样的眼镜片后发着后人叫着睿智的光。
段良弼感到口干舌燥,嘴里象充满了白沫,舌头在费力地搅动,嘴唇像裂开一道一道的口子,空气中布满的沙尘一点一点填了进去。
他不由自主,大脑一片空白,目光死死盯在秦邦宪身前那杯白开水上。
他知道房间里再也找不出空杯子了,真的连能盛水的器皿也找不出来了。他太想喝水了。他嘴唇在动,心在动,只有目光死死盯着那杯水一动不动。
段良弼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出于生物本能地伸出手,端起眼睛里的那杯水一饮而尽。
随后就盯着空杯子忘了讲话。
听的人就盯着他看,不明白讲的人怎么会这么渴,渴得忘了应有的礼数。
段良弼接着又讲。
任弼时不动声色,把自己身前那杯有盖子盖着的水轻轻推了过去。
西窗出现一片暮色的时候,老段的陈述终于告了个段落,秦邦宪已经合上笔记本,估计应该汇报的东西也差不多该讲完了。任弼时却发现老段的手不时去搔裤裆下部,一抓一搔极不雅观。老任回头一看秦邦宪,秦邦宪也注意到了,眉头一皱就说:老段,平时注意点卫生,不要惹了一身虱子,这床以后还有人住的。
段良弼干脆就没听懂秦邦宪的话。
他完成了在大脑里酝酿了很久的东西,好象刚把发酵的酒糟一点一点从脑海里抠出来,抠得他费尽了最后一点精力,酒糟倒腾空了,该填补的地方却没有东西去装填,留下的是一片空白。
他只是感觉到还有什么事没做完。
同时感到下身沉甸甸的有种坠胀的感觉,就不由自主动手去搔,明明知道有人看着,他还是忍不住,那是种抵挡不住的诱惑。他终于摸过那团鼓鼓囊囊的东西,在裆下接触到了那堆捆扎得整整齐齐的坚硬的物品,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件还没干的大事。
当着中央领导人的面解开裤头掏出那个黑油油脏乎乎的黄布褡裢时,黄布已经变成说不出是什么颜色了,斑斑点点中汗渍和尿液浸成了地图样的不规则图形,带着一股强烈的臊气。任弼时和秦邦宪怎么也搞不明白老段裆下会像女人一样藏有个物件,就见老段“咚”地一声把褡裢扔在桌上,震得茶杯盖也“咚”的一声滑在桌面上。老段就动手去解褡裢上的疙瘩,有两个疙瘩实在解不开,老段就俯下身用嘴去咬,牙齿咬得紧,腮帮子就一鼓一鼓的。所有的结都让他捣开了,他就望着两位领导古怪地笑,笑得毫无感情,令人毛骨森森的。
老段提起褡裢的一头一抖,几块黄橙橙的金砖“咚咚咚”掉在桌子上。
“八十两”段良弼长长出了口气,一下子瘫坐在小床上,“我的任务完成了。”
当时中央正处于财政艰难时期,江西老表的黄金不异于雪中送炭。随黄金同时上交的,还有封段良弼亲自写的《富田事变前后详情》。
任弼时铁板一样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暮色很浓,远处亮起了昏黄的街灯,房间里的尿臊味很重,借着天边的那抹白光还可以看到人们相互间模模糊糊的轮廓,墙角的木装板有些潮了,发散着朽木的气息,门窗外的云很厚,不清不楚在浮动着,象重重地压在人心上。
任弼时和秦邦宪踏着黑暗的边沿走出屋间时,客气地和段良弼握手道别。这也许只是人际交往间的礼数,也许是有教养人的一种习惯,从大山里来的段良弼却深深地感到一种温暖,似乎看到了天边那丝曙光。
以后几天便是蛮有信心的等待。
段良弼想起两位领导看到金子便发出金子般闪光的眼睛,心里感到一下子就亮了。他后悔路上失却了的那批黄金,不得不暗暗责备自己的失职,不得不感到万分痛惜,他想情况也反映了,易尔士的报告也应该交上去了,明天也许会有一个崭新的天地。
中央不久就开常委会讨论这件事。
中常委之一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 1998年版)中是这样写的:
当年三月初,我看到一份赣西南少共区委控告毛泽东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指责毛泽东一贯违反中央指示,一意孤行,走到了反党反革命的境地。内容是陈述赣西南中共区委和少区区委以及不少将领,大多拥护中央的领导(即立三路线),而毛泽东却不敢和敌人战斗,不遵守中央进攻南昌的命令,带着部队逃跑,显然是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三0年冬,毛泽东不仅不改正错误,反利用肃清AB团的名义,杀害了大批同志,因此,赣西南少共区委要求中央对毛严予处分。
少共中央书记秦邦宪被邀参加中央常会,报告这件事的经过。他说明:一、据赣西南少共区委来人的口头报告,与文件内容是一致的,不过有些补充。二、这个来人系赣西南少共区委委员,曾来过上海数次,少共中央的同志们都认为这位同志可以信赖。这次他还带了几十两金子和其他文件来。三、据来人解释,中共赣西南区委对于控告毛泽东这个文件的同意的,至于没有共同具名,是惧怕毛泽东知道了,会将他们当作AB团清算掉。秦邦宪根据这些情况,认为这个文件和来人的口头叙述大体都是真实的。
秦邦宪接着陈述:赣西南中共和少共同志以及军队中一部份同志,早与毛泽东有许多意见上的分歧。在反毛斗争中,他们曾提出“拥护朱德,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但朱德在毛泽东挟持之下,表示支持毛;彭德怀则是不满毛的,在他的第三军内,不满毛的干部也占多数。赣西南少共区委认为,可能有少数AB团份子,混进了我们内部,这些人在反毛斗争中也可能兴风作浪。因为他们发现了AB团的破坏活动,毛泽东便不会青红皂白,将大批不满他的同志,也当作AB团逮捕起来,任意刑讯杀戮,在富田一个地方,便杀害了以百计的同志。……
秦邦宪认为毛泽东确实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指出毛泽东反对李立三的指示可能是对的,但他自己也不免右倾……在富田事件中,毛泽东可能有意无意地将反对他的同志清算掉,这更是不可宽恕的。
中常会听取了秦邦宪的报告后,觉得事态严重,不能立即作出决定,乃要求秦邦宪先行通知赣西南少共区委来人,暂时严守秘密,听候中常会处理。
张国焘的回忆基本是可信的。秦邦宪的汇报也是平和的,中常会的处理是慎重的。
旅馆里的段良弼心情一定不错。心头的包袱放下了,人一下就轻松了。
他决定上大街上走走。
一连转了两条街,总觉得有个穿裘皮大衣的女人跟着他。有次甚至在个买布匹的小店里和她朝了面。那女人面容很美,是那种大家闺秀很有气度的美,美得令人不敢正视。段良弼根本不认识她,她却朝段良弼嫣然一笑,抿着嘴就出了门。
段良弼心想,哪有一出门就被人盯梢的道理,忍痛叫了辆人力车,一口气跑到了外滩。
段良弼每次到上海都要去外滩,不管多么忙多么累。他对外滩有股天生的亲切感。他爱的不是那十里长堤沿岸的洋房高楼,从山区来的人也不爱川流不息的车流,甚至不大爱那海派风味十足的景致,他爱的是滩上那韵味很浓而节奏感又很强的海浪拍岸的声音。
海浪的有节奏的拍打声使他想起故乡和故乡那片蓝色的天空下经久不散日日夜夜响起的织布声。他不知道怎样去形容故乡的那片熟悉的古建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忆起粉白色的墙,墙上那些简练的飞檐和灰砖黑瓦砌成的防火墙,错落有致一家接一家的。小城并不大,却以产青布著名于江淮和两广。他记得有次查阅古县志,他很为有几句话感动,到如今都还记得书里的原话:“居民多务耕种,兼及纺织,妇女亦多从事于田间,否则即居家织布,无一闲者。阖邑机声相闻,所谓吉安青布者,为出产大宗,销行广东之南雄、佛山间,名著江淮。”他感到从各家各户传出的织布声组成了很多动听的曲子,从儿时的摇篮里他就把这些曲子当成了催眠曲,嘴里含着母亲的乳头就听惯了他们,长大了念书时听老先生讲失散了的广陵散,老先生讲得一摇三晃老泪满襟,他就自己告诉自己广陵散没有丢失,它已经溶进了小城上空那一片织布声里,溶进了那片清彻透明的天空中。
上海滩的江水拍岸多象故乡的机杼声。
还有大海上空那片纯白如棉的云。
他出生时家境还算富裕,爷爷是个不大不小的粮商,一家人住着四开间庭院的房子,中厅又深又静,庭前有两株岁月很久的梅,疙疙瘩瘩的老树占了前半个院子。院里有雕兽刻花的石缸,缸里养有血红色的鱼,用手一搅,鱼就忘命地跑,象一阵散落的枫叶。
最令人解不透的是他的“抓周”。
几十年后记得他的人都说他的命运还在儿时就显出了迹兆。
母亲的床上摆了几块银光闪闪的龙洋、大头和毫子,靠枕头放的是书、算盘、刀剪,床中间放的是大米、瓜子,各种东西琳琳琅琅摆满一床。已经把婴儿抱上床了,隔壁的石和尚赶来了,还牵着他那五岁的儿子。他大叫不忙,快把良哥儿抱开,还有一样东西没放哩。
爷爷问他差个啥?他摊开紧捏的手心,说还差这个。
那是一枚红透了红得发黑的枣子。
爷爷说石和尚你这是干啥?那边床上代表粮食的东西多嘛,你的意思是多一种粮食我孙子以后好当庄稼汉?
石和尚叫他独生子给爷爷磕头请安,然后说我这不代表粮食,它代表朝珠,老爷,就是清朝大官帽子上的顶子,你孙子若是运气好抓了它,将来要当中央大员,这小子顶平额宽的,我不忍心让他当个士农工商呀。
一席话吹得爷爷安安逸逸的,心上那朵花不知啥时候就开了。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一抱上床的婴儿爬过了洋钱,对书和算盘也不屑一顾,他径直爬到床中间,一把就抓住了那颗透着邪气的枣子。
接下来的动作更令人吃惊。
那胖乎乎的小手直接就伸向小嘴,周围的大人们没来得及做任何反应,他小嘴一张便把那枣子吞了下去。
典型的一个囫囵吞枣。
一家人就目瞪口呆地望着石和尚。
石和尚也慌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呆了好久把个光头抠了又抠,才说:此儿顶子是戴稳了的,就是心大,他怕官帽被人夺走,干脆吞进肚里,保险哩。恭喜老爷,添了个栋梁之才,保证今后一路高官,一直做到宰相,首辅呢。
于是爷爷给他取了个大吉大利的名字:良弼。弼者,辅助也,良弼者,一代名相也。
可能误就误在石和尚身上。
石和尚不姓石,俗家姓张。
段良弼长大以后读了书,才想到石和尚的“石”应该是“释”,那字本身就是和尚的意思。
吉安一带风俗也怪,县志上说“庙宇遍村市,僧道不剃发,有妻子,亦多经生意,为苏皖所未闻。”
坐在海边闲看孤云的段良弼想起了吞进肚里那枚红枣,心里就有点好笑,心想出了这么大的事,这顶子藏在肚子里,恐怕也不稳当了。
难怪爷爷后来说:你要信佛,要见佛就拜。
段良弼后来果然信了佛,他信的洋佛,马克思和列宁。
海滩上又走来一群妇女。
她们一边踏浪一边唱歌,经过海边独望的段良弼时,她们中间有个少妇望他一笑,无意中说了一句:海水好冷,先生跳不得呵。
段良弼知道她们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生活失意到海边寻轻生的外乡人,就点头应了声:人间多事,死不是唯一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