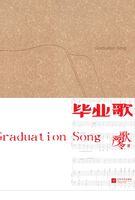红二十军独立营兵变东固,刘敌调来一七四团机枪连率众一举杀奔富田。跑了李韶九和曾山,捉曾父抵账。
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正在屋里以诚意治色盲,遭误捕。
十二月十三日,段良弼、刘敌在富田广场召开士兵大会,被捕者现场讲肃“AB”团经过,控诉李韶九的罪行,近现代史上军内第一次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
两封送上海中央的申诉信。
事变者送上海中央黄金二百斤,求易尔士回上海从中转圜说情。
七里岗。
二十军独立营。
刘敌一直在做梦。
骑在马上进入溶溶月色,四周有灰色的甲胄骑士在马上护着他,刘敌从那个时候就走失了自己。他不明不白恍恍忽忽就回了七里岗营地,警卫员小林是如何把他扶上床的也搞不清了,他一会在梦中,一会生活在现实里。
他不明白,在二十军堂堂一个军部,除了偶尔看到军长刘铁超以处,其他首长如肖大鹏、曾炳春等一个也没露面,反倒是一个毫不相干的李韶九在那儿耀武扬威,他凭什么?难道军部有变?变又是怎么变的?最近地方清“AB”团特厉害,难道有人把手伸向了军队?刘敌想不通,他忘了人已回到七里岗,心还留在东固,脑子里反复演练着和李韶九那场充满耻辱的对话。气是受够了,可他还记得李韶九拍着他的肩嘱托他好好干,今后二十军就是他的。那些话一直在他耳边响,一直没停过。这些话意味着什么?二十军的正副军长政委都不行了?中央要对二十军大换血!这可就不是一般问题了,梦,肯定是梦。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这么荒唐的一幕。
可是他又不相信那是梦。
他看到彦来笑嘻嘻走进来,说老刘,再来战一盘,我不信就杀不赢你。他苦笑一下,问你就不累?半夜三更下什么棋哟。一个硬要下,一个偏不干,两个缠了半天,刘敌无法,顺手在桌下布袋里抓了一把东西,说:“咱们打个赌,你猜中了我手里的东西我就下。”彦来看看天,天色已近破晓,就说:清晨八早猜啥子哟,有啥子猜头嘛。刘敌一惊,打开手掌一看,手心里摊着八粒枣子,青皮的。心想这小子神了,一下猜出了“青皮八枣”,叹了一口气,说“下吧”。话一说完,彦来就不见了。回头一望,桌上摆着局残棋,正是他和彦来去东固前留下的。
还是一场梦。
刘敌睡不着了,或者说根本就没睡着,翻身下床去找水,一边摸索着床前的布鞋,一边扣军衣的纽扣。
说也怪,从来不会下盲棋的刘敌脑子里清清楚楚出现了那局残棋。
彦来也是,那棋还有什么走的,就是天王老子亲自来,也无法帮你挽回败局了嘛。
“不”,一个神秘的声音附着耳朵说,话声里回音极重,“破解之法神已昭示了。”
刘敌一惊,“哪里?破法在哪里?”
棋盘上那颗红色的“马”一跳,吃掉了红色的“车”。
如果来的是天王老子,一切游戏规则自然作废,天王老子当然可以用刘敌自己的棋子吃掉自己的棋子。
如果来的是总前委的干部,二十军的游戏规则还有效吗?
自己不就是那枚红色的“马”?
谁又是红色的“车”和红色的“帅”呢?
刘敌吓出一身冷汗,梦彻底醒了。
大胡子营长张兴兴冲冲闯进门,人未到声音先到了,他高叫:“回来了?上头同意补充多少兵员?你咋就没顺便把他们带回来?运来多少粮草?叫那些新兵蛋子背也背回来了嘛。”说话之间,营政委梁贻也来了。
刘敌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把两人都搞糊涂了:
“游戏规则要变了。”
刘敌解说到几句,两人都呆了。
他们两人以至大多数的红二十军的干部战士都是江西人,而红四军的人大多数是湖南和湖北人。两方的人一直有矛盾,这谁都清楚。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当时主要是由当地革命武装建立的,当时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根据地人口二百多万人,拥有九座县城。
1929年11月底,毛主席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特委,成立新的特委。这个建议的实质是将原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立红六军,而红二、四团大多是江西地方游击队改建的地方部队。赣西南方面认为事关重大,毛泽东个人说了不算,必须经过在上海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
1930年1月,毛泽东硬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领导,遭到当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这一揽子党政军矛盾,毛泽东于1930年2月6——9日在江西吉安陂头村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方面负责人联席会议,而两个月前,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权。在著名的“二·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无疑为日后肃反“AB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2月16日,红四军总前委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
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
10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入吉安。
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队里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多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毛泽东这些做法,遭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与反对,但他们不敢言而敢怒。一九三0年五月,赣西南的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力量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乃至数省革命的胜利,批评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李文林回赣后,8月召开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精神。会上不点名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消了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被毛派来的特委书记刘士奇的职务,建议上海中央开除他的党籍。当时,李立三代表中央,赣西南特委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10月中旬到月底,李文林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的指示,与毛泽东的冲突全面激化。
1930年11月底,毛泽东认定的“AB团”头子李文林在宁都黄陂被拘押,一场肃整与李文林有关的“AB团”份子的斗争山雨欲来。
七里岗二十军独立营当然了解这些情况。而且由于事实经过民间流传更富于斗争色彩,给军队和战士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刘敌详细说了东固的遭遇。
梁贻沉思良久,捻着稀疏的虾米胡说:看来中央出了奸臣,有人发出十二道金牌召岳飞,陷害忠良嘛。
别看张兴性子急,大是大非问题看得准。他猛喝一口酒,说:政委你别乱说,中央还是好的,李韶九不是中央派出来的嘛,这跟岳飞不岳飞无关。老子打个不准确的比方呢,就像……就像李自成杀张献忠:贼杀贼狗咬狗,争地盘争势力范围嘛。
梁贻反驳说:你把你自己当什么人了?当李自成可以,当张献忠也要得,怎么能当贼当狗呢?营长你这政治态度也太不严肃了。
两人越争越说不清,越说不清越要争,闹个不可开交。
刘敌叫小林把早饭开到屋里来,和营长政委一边就着老酸菜喝红米粥,一边分析情况。他说:咱们也不用找比喻了,直接说吧,李韶九是总前委派出来的,不是中央派的,中央在上海,他们还是支持我们的,我们二十军和四军都是中央的儿子,十指连心,手板手心都是肉嘛。母亲怎么会狠心把自己的儿子整成“AB”团?至于李韶九来富田,来东固,可能还会来七里岗下狠手把干部往死里整,我看他的目的是要消灭我们江西的党,要整跨江西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
调子定下来了。
怎么对付呢?军人都有一腔热血,不能伸长脖子等四军来人砍脑壳。你刘敌不是答应投降接手二十军的工作了吗?咱们不如将计就计。
三人商定:假装顺从李韶九的安排,让刘敌再回东固,说是独立营听从总前委的命令,请李韶九来七里岗训话。
张兴说:只怕他龟儿来得去不得了,老刘,你放心大胆去请,俺老张负责在帐下伏下刀斧手,到时你举杯为号,俺只下手,立马砍了李韶九这个狗娘养的。
梁贻说老张你别满口唱戏的胡话,要干,咱们就要干得谨慎,干得滴水不漏,你我一定要清楚:搞砸了你我人头落地事小,红军内部起了窝里斗我们就罪大了。
梁贻的顾虑的对的。
事预则立。
如果他们考虑预谋周到,事情也许就成了。李韶九也许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不管杀与不杀,都可能被当成一步闲棋永远抛置在历史的角落,让他蒙上层厚厚的尘埃。
即使是考虑不周,只要照预谋发展下去今后的历史也将是另一个写法。
张兴反驳梁贻说:老梁你紧张个啥?那李韶九不过一个书生,带的兵又少,就算个挑个打,俺老张保险单刀赴会,一只手就把他擒了回来见你。
政委一笑,说好,咱们就这样定了。
刘敌收拾停当,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是给部队做工作的时间和召开干部会的时间都算进去,大约就该到时候了。他出发前想给张兴和梁贻打个招呼,让他们在家里作好扣人的准备,以免临时慌了手脚。
可是张兴却不见了。
和张兴一起不见了的还有他的酒壶,再就是张的通讯员张苞。
他到哪里去了?有人说他可能去了东固,上军部去了,是骑他的大黑马走的。
可以想象刘敌和梁贻那个急呀,这小子真是个猛张飞,关键时刻乱下矛子,也不问是不是时候该不该出手。
你问他会不会出于自身利益去军部自首?去邀功请赏?不,绝对不会,这一点请你放心,黑老张不是那种人。
一个战士说,早晨从东固来了个老乡,说军部正在大清洗,(哦,忘了告诉你,那老乡在军部工作,看风声不对上哨后就没回来营,脚板擦青油溜来了。)连肖军长都遭抓了。
营长急了,就问“政委呢?曾炳春政委呢?“
曾炳春是军中出名的精细人,与营长同乡。有次张兴遇险全班人战死只剩两人了,是当时的师政委曾炳春亲自带一连人把他救出来的。曾政委救过他的命,对他有知遇之恩,张兴常说知恩不报非君子,自己颈上这颗人头就许给曾政委了。何况政委这次有性命之忧哩。那老乡本不知内情,心想连军长都遭了,难道不跑得了政委?就点头一口咬定“政委抓了”。
张兴一听急得火烧屁股一般,立时也没顾及刚刚定下的计划,也没想到个人的安危,急忙叫“备马、备马”,以后就带着通讯员张苞飞身上马,急奔东固而去。
他真的做到了单刀赴会。
他要去救他的恩人。
这下独立营乱了套。
刘敌和梁贻急忙命令全营处于战斗状态,一边准备对付前方来进剿的国民党鲁涤平的第九路军,一边准备对付从后方东固来的红四军可能发动的袭击。
说这时的独立营是“箭上弦,刀出鞘”是表扬他们,其实此时的独立营已经乱了阵脚,不知适从了。
刘敌与梁贻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锅沿上爬来爬去越爬越不自在,只要烧锅的再加一把火,他们就灰飞烟灭了。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张苞匹马落荒而回,颈子上还死死挂着营长的酒壶。
“遭了!营长被李韶九扣了!”
刘敌一看事败,立即和梁贻集合部队,杀气腾腾扑向东固。
东固本是红二十军的总部,当兵的都是江西的子弟兵,对于总前委派人来清洗军部本来就有一股怨气,见一七四团政委刘敌前来清君侧逼宫问罪,立即大开营门,刘敌兵不血刃进了军部。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刀兵一动,立刻成了阶级斗争。
刘敌镇压反革命毫不手软,立即抓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押的张兴与谢汉昌等人。
李韶九见风使舵,刘敌带人一进前门,他立刻从后门逃走了。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此次行动倒还不会酿成太大的恶果。李韶九逃回富田后也只是想把兵权抓紧,以便继续追查“AB”团成员,把以上刘敌的行动也只当成红军军队之间的磨擦而已,他做梦也没想到刘敌胆大包天,一举率人杀向富田。
刘敌后来说,他之所以赶到富田,是怕李韶九恼羞成怒,动刀杀害被他关押的省行委的同志。当时他们只知道李韶九已经杀了二十多人,而关押的共有一百多个人,刘敌以其亲身经历,知道姓李的心毒手狠,他不得不为在押的省行委同志着想,他认为那些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干部,是江西省乃至全国的一笔宝贵财富,决不能毁在李韶九手里。他认为那些人根本不是什么“AB”团的成员。
考虑到富田已经不是红二十军的辖区,刘敌派人飞马调来一七四团机枪连,带上独立营全营人马,马不停蹄奔向富田。
富田的李韶九正在迎接一行神秘人物。
这些人的到来也是李韶九没有料到的。李韶九不敢动他们,还得假装积极热情款待着。
他们是闽西来的参观团。参观团不可怕,老实说面子也不大,李韶九不敢得罪的是团长,中共中央派来的提款委员刘作抚,当时化名“易尔士”,他是以中央大员身份来江西省行委巡视并提款的。
在上海白区工作的中共中央穷,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便是到全国苏维埃地区收缴,主要是各根据地打土豪时没收的黄金。另外一部份活动经费就靠共产国际提供。张国焘后来著书《我的回忆》(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1)曾说到这个问题:
“李立三似没有根据各地呼声要求过共产国际接济,反将各游击队秘密运到上海的金银,留作中共中央之用,一时成为李立三的主要财源。米夫似也没有接济过游击队,老是强调应由游击队自身设法解决。”
——第二册·P、482
在文革中有材料报道,说当时身为白区地下活动领袖的刘少奇,就曾将活动经费让人铸成黄金皮带头和带钩,随时捆到腰间,以防敌人搜查时遗失。据称:那些黄金便是根据地交缴给中央的党费。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当时把收缴活动经费当成一件大事,因此易尔士以中央提款委员会的身份到富田,任何人都不敢小视,不敢怠慢,又因为本身涉及经费的携带与运送,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迎送。所以易尔士一行显得特神秘,他们只想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最先在那群谨小慎微的参观团人员中发现卓尔不群的刘作抚的是彦来。那人接人待物十分有分寸,客气有礼中自然透着一股目高于顶的王者之气。彦来就想那人不是一个一般人物。
最先在工作人员中发现彦来的却也是刘作抚。他看彦来整天无所事事,却从这失魂落魄的人身上闻到了一种书卷气,发现他是个做学问的人。
说来也怪,两人只是无意之间看了几眼,一下就确认了对方的人品。
当天下午参观团的人都出去活动了,刘作抚径直走向紫苏的小屋敲响了房门,手里提了副楠木象棋。
应声而开的大门后站着彦来,一眼看到来人手中象棋就明白了他的来意。
“废了。”他客气地摇头,有点抱歉地说。
“废了?此话怎讲?”
“色盲,红色盲,连红绿也分不清了。”
刘作抚就笑,说分不清颜色是暂时的,只要老兄精于此道,颜色不是障碍,我自有法消解,就看老兄有无诚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