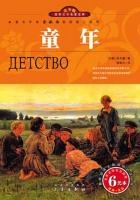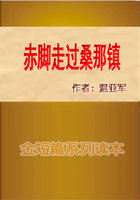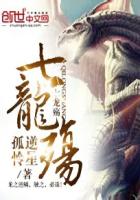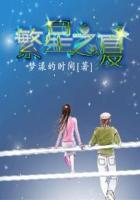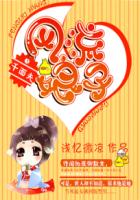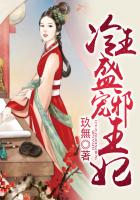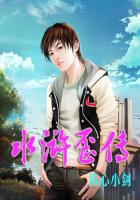两个兵架着女人飞跑。一个喊累,说:“还跑个球,就在这里弄死算咧,你看那满地坝的死尸,有几个是拖出去打整的?”老王不理会,只管跑,说累是累点,等一阵让你看好看的。边说边淫笑。两个兵有了劲,飞快把女人架到后山脚下,脚手没力不听使唤了,才扔下绑成一团失了颜色的女人。姓王的拿把早就备好的刀去割女人脚上的绳子。另一个看他把女人翻来翻去的,知道他不怀好意,把枪上了膛说:“王二,你也别造孽,让开,等老子一枪毙了算球。”王二是个犟人,牛卵子眼睛一鼓,“毙了?没那么容易。”边拦阻边加紧割绳子,把身上的绳子割完了,就拍了一下女人的屁股说还不快跑。另一个兵没反应过来,女人当然也没跑,王二才说:嘿,这女子是连长看上了的,将来要和连长成亲咧,这是连长亲口给我说的。女人不敢跑,或者说跑不动了,另一个兵也不敢放,说让李主任晓得了我有三个脑壳也不够割,还是毙了吧。王二一巴掌打歪他的枪,骂:“李主任管得了你几天?要想在连长的血盆里抓饭吃,手就不要伸错了地方。”那兵倒不是想通了,他是怕王二那血丝暴暴的眼睛,怕他个龟儿毛了乱来,他手上那把攮子锋快哩。
王二指着不远的半山一个岩洞说:你先进去躲一阵,连长搞空了来接你。说完拉着另一个兵就走了,也没顾那女人进洞不进洞。
张忠良开始不信,换哪个人来也不会相信,经过反反复复地问,才基本相信了,他不懂,照王二的为人,怎么会干出如此义气的事,干脆挑明了问:“王二,李主任不是叫你监视我么?”王二嘻嘻一笑:“俺王二也是个忠臣,卖主求荣的事决不会干的。”另一个兵揶揄道:“李主任管不了几天,若把连长搞毛了,保管哪天枪一响哪儿要命就把你往那儿送,这条命也不值钱了。”王二还是笑,说俺还要在你的血盆里抓饭嘛。
好不容易等到李韶九带人离开,王二领着张连长到后山时,只看到几截割断了的绳子,女人早已不知去向。
久不住人的山洞里也没人。
这一切不但不能对疯子讲,还得把他控制起来。张连长一声命令,立即有人把“AB”团嫌疑犯彦来关押了。
彦来对囚禁他并不意外,只是一再要求把他关在紫苏的寝室里,他反复说自己是来结婚的,莫要关错地方新娘回来找不到人,那才叫鸡飞蛋打冤枉死了。有好多战士感到了这疯子有趣,常借有事围着门口逗他,说你来迟了一步,新娘子等不得前几天就嫁了,嫁了个大胖子军官,你还在这儿傻等。彦来就问结婚喝酒没有?喝了?好,好,唱歌没有?没有,那我唱几句给你们听,说着他就扯开喉咙唱,别看他装疯卖傻的,其实是想搞出点响声来,如果紫苏在附近肯定是会有反应的。
唱久了就累了渴了,就干脆不唱了,他心里苦得很,知道紫苏一定出事了,回不来了。脸上还得装笑,他也没办法了,想来想去,心想一直没见张忠良连长露面,他到底在哪里?是不是不想见自己呀?闹这么大的动静,这儿的最高军事长官早该出来了呀。
张忠良也在想那个叫紫苏的女人。
他不相信那个被又捆又拖的女人能跑好远,她肯定还在山上。考虑到女人肯定又冷又饿,他在炊事班拿了几个馒头挟了自己的被子就摸黑上了山。
紫苏确实没跑好远。
她不敢走,也走不动。
她听到了彦来的歌声,一听那杂夹着几个俄文单调的国际歌,她就知道彦来来了,可是她不敢出去,出去自己被抓不说,一定还会牵扯到彦来。他救不了人,自己反而容易被搭进去。
她也看到了放她走的兵领着张连长来找她,她对张连长有股天生的怕,更怕他把自己抓回去,反正那个人她解不透。
天黑了,又冷又饿的她再也顾不了许多,见连长拿包东西放下东望西看就做贼一样走了,赶紧奔下山抢了东西就走。
她晓得两个男人都在找她。
关于紫苏,后来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专文专著介绍她的很多,特别是国外,文革以后国内宣传部门开放了很多禁区,这类文章也逐渐多起来,国内有句套话叫“雨后春笋”,也许因为她的经历特殊,也许因为她是女人,对她的遭遇各种各样的描述都有,一般都是无妄之谈,根据史实写出来的严肃文章也有,还有香港和美国、加拿大出版的,正是由于无人统一口径,当然也没法统一口径,文章仍然难免各说各异,当然,照毛主席的说法就是阶级观点不同,看问题的方法就不同,有人把红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青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反之亦然。但是具体收集材料写作本文时,作者在材料取舍上还是很难。
我看了能收集到的所有材料后,感到尽管关于紫苏众说纷纭,描金泻赤应有尽有,有一点是真实可信的:她经历了生活和人生中最大的苦难,并且把苦难当成了一种信仰,后来像皈依佛门一样皈依了并不存在的主掌苦难的神。
她的这段经历颇带传奇性。
第一部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本香港龙联书局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书,书名叫《赤都记事》,作者黄之宪先生,书中有提到富田事件的内容,并把“紫苏”写成“苏子姑娘”,明眼人看后得出这个结论不难。到了二00二年,我经多方托人去电去函联系,终于和黄先生联系上了,并在同年九月专去香港拜会了老先生。见面后老先生非要送我一套地道的法国名牌皮尔卡丹,说是谢谢我为民族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说是凭我的胆气与劳作,十件皮尔卡丹也不算什么。我坚辞致谢,说什么也不收,他笑着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既然你是九月来的,我受古人之托赠你,望你不要推辞。
老先生谈吐文雅,文字功力深厚,交谈中不时引证一两句古诗文,他对晋时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先生和明末清初的王阳明先生十分崇拜。他三十年代前参加红军闹暴动,三十年代后脱离革命经商,从小生意做到棉纱,后来又做煤油钢铁,终于成了香港一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企业家。当我听到他说他亲自见过紫苏时,就有点怀疑他的身份,他又说他亲自主持了开释那个女红军干部,我就问他是不是他就是后来文献中提到的张忠良连长。他惊异我对那段历史研究的深入,却摇头说他不是张连长,张连长另有其人,我就叫黄之宪,当时入伍登记和士兵名单上都是这个名字。
他能极其详细地说出省苏维埃与附近山体、建筑及四野的地理地貌,甚至还记得山后那座土地庙,庙前的对联被改成了“铁锤镰刀开天地,裂土分田争未来”,他说当地人为去病免灾不求医问药,爱搞一种“打杨四”的迷信活动,还有声有色讲起从“请杨四将军出庙”到“打四将军回衙”的过程,生动极了。
我相信他当年一定在富田一带活动过,极有可能在富田事变时曾参与其事。他却主动对我讲了句令我大吃一惊的话:“我就是那个亲手放了紫苏的人,当时人们叫我王二。”
见我极不相信,他又说:“当时革命队伍里的人很杂,全国各地的都有,我们那里的人‘黄’、‘王’不分,我就成了‘王二’。”
且不说七十年风云变幻,物是人非的故事实在令人吃惊,我却怎么也没想到我根据实际接触过黄之宪先生(王二)的人的陈述写出来的王二,原型会是一位如此文雅的道学先生。
是造化弄人?还是历史无情?我说不清楚,为弄清楚当时的情况,现将《赤都纪事》有关章节摘录如下:
民国一十九年春三月,李文林、李韶九所率之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军,总指挥黄公略,政委陈毅。当是时也,红三军与林彪红四军及由朱培德之民团哗变组成的红十二军共建红军第一军团,总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朱、毛曾一度不知,为争领导权一事也。后拥朱之陈毅亲赴上海,经中共中央最高层讨论决定,第一军团成立总前敌委员会,毛任前委书记,辖万余人,十个师。中央之政策沿革一贯是党指挥枪,自是,毛泽东成为党军第一人。
红军入江西,下吉安,毛泽东有诗赞曰:十万工农下吉安。然而,此时党内发生所谓“立三路线”者,红军内部分裂,三军团及一军团部分人思谋另寻出路,刘铁超所率红二十军反。
此为革命之最紧要关头。
余随李君韶九所率一连人赴富田镇压。
黄先生在文中叙述了富田肃反经过,叹惜说“余为非党之成员,亦惊悸惶恐不已,其刑罚之毒,涉及无辜之泛,几十年来不敢再想,夜深人静之时一旦念及,犹自心跳不已。”一段文字专门说到紫苏,我暂抄录作为一家之言:
“(富田事件中)被捕之无辜者有一苏子姑娘,彼系四川人氏,留俄归来,被一林姓诬告为AB团,备受拷打折磨,余奉命执行其死刑。余怜其少艾,叹其无辜,私下牵到省府后山释放之。
连长张忠良闻之,不但未见责于余,反有嘉赞之意。后余曾率张连长往后山寻之,欲助其逃脱,竟全无人迹唉。
极富传奇性的是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紫苏注定了还要遭受更多的磨难。
第二日中午,忽有乡人子来告林姓家藏留一外乡妇,疑是AB团成员逃匿者,促吾等五人往。到林家,果见余纵之女孝袍披身,作痛失亲人状哭泣于一亡灵前。
张连长故作不识,问主人妇,妇一口承诺此女为丈夫之妹前来奔丧者,乡人不识,故有误会。张连长怒责邻人子,率队空手归,再次放苏子姑娘一生路。
嗟夫张君,生于乱世,苟活于战时,竟有一幅菩萨心肠,不胜造七级浮屠者乎!
从这篇文章看来,张忠良良心未泯,对紫苏姑娘有再生之恩。可以想象得出,如果当时把她揖拿归案,等待她的唯一出路定是受尽凌辱而死。
我手中还有一本加拿大环球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书籍,书名叫《红旗漫卷西风》,作者也自称是富田事件的知情人和专家,她是个女人,即本文主人翁彦来的妹妹。书前的署名写的是笔名“铁笔”,真名叫莘来,她说有关紫苏的描写部份是紫苏逃到上海以后亲口告诉她的,可信度极大。她在书中写道:
“把我拖到省苏维埃后山时,押解我的士兵用刀割断脚上绳索,把我翻来覆去地拖,双手乱摸我的乳房,上衣纽扣全被扯光,胸部几乎裸露于外,地上的草根乱石好扎人。突然又有敌机低空飞过,看样子又要投弹轰炸,两个押解我的行刑人才匆匆忙忙跑了,看来不是谢天谢地,倒该感谢那架去而复返的蒋军飞机。
半夜时分那位企图在牢中强奸我的连长摸黑送来了军被和馒头,我猜他大约是想用来引诱我让我从躲藏处出来吧?他不是想置我于死地,他是想霸占我的身体。后来我躲藏在林家,果然他又带着人来搜查。幸亏我当时穿着孝服当孝子,还抓了好些锅烟墨把脸涂花,有了林家嫂子死口掩护,才算蒙混过了关。他那又眼睛好毒,在我全身扫来扫去,估计我当时怀有身孕他也看出来了。他要抓的是个等待结婚的大姑娘,绝不会是个怀孕的妇人。这次逃得性命,要感谢的是肚子里的儿子。
同是当事人的两种陈述,得出的竟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涉及到其他文章,则大多采用比较笼统中性的说法,即人们常说的哀而不伤,含而不露。我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张忠良,问他对两篇文章有何看法,是否同意其中一篇的观点。他说总的说来,他觉得两篇文章的描述都是可信的,都是极力想站在客观的观点反映历史的事实,不同之处在于各人带有或者情不自禁地带有自己个人的感情色彩。王二那人我了解,不管他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的人物,他总是想突出他自己,他想把他打扮成救世主,我也沾了他的光。至于紫苏的自述,或者说通过第三人转述的自述,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刚刚脱离苦海的后怕心情。她永远不可能了解和知晓我释放她的原因,从而不可能理会我一系列的作为,何况我当时粗野地冒犯了她,她对我误解太深,七十年前她对我就有了定论,惶论七十年后哩。
正当我对这段历史的观点看法及取舍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位江西作协来的朋友说,南昌某区文化馆有位老先生当年在吉安工作过,有年为了参加全国的戏剧汇演,曾专门到富田蹲点搞创作,后来根据当地群众冒死掩护一个女红军的故事写过一个剧本,在文革前的戏剧汇演曾获一等奖,你不妨到南昌去采访他。我当时就笑,说人急了乱投医,你教我临时抱佛脚,抱的却是个泥菩萨的不中用的脚。你下细想一想,当时是毛泽东时代,哪个有日天的狗胆去塑造群众救“AB”团份子的群象?除非是鸡脚神脑壳上拍蚊子,活得不耐烦了。他说你老兄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正是因为这段史实相当生动感人,作者实在割舍不下,就换了一个背景,没写红军清洗红军中间的“AB”团,改成了白匪搜索红军。省里知道内幕,评价极高,给了他一等奖,后来要到北京汇报演出,省里怕翻盘出事,就压住没让这个剧上,反而让获省二、三等奖的作品进京了。哦,这个剧当时叫什么来着?让我想一想,嗯,叫《赣江血泪》,作者叫魏兴仁,当时也就二十郎当三十出头。
老魏听我一提到《赣江血泪》就非常激动,他说当时如果没有政治偏见,他的剧本不改历史背景的话,绝对不止获省一等奖,获全国的也当之无愧,剧本的题材远比后来获奖的《红嫂》深刻,当然,他不是说《红嫂》不行,他是说他的《赣江血泪》与《红嫂》反映的是同一个主题,他的素材同样来自史实来自民间,那是他亲自去老乡的口中一点一点抠出来的哟。
对,老乡救的是从肃反运动中逃出来的女红军干部,她真名叫紫苏,剧中人叫红妹。
以下是老魏讲述的真实的事。清注意,并不是改写过后的剧本,是历史的真实:
山后半坡上荒草萋萋,林家在自己的土地边挖了三座坟,同时埋葬了自己的三位亲人。
和他们相邻的杜家也正为一座新坟培土,坟里埋着他们唯一的亲人。
林家和杜家是世仇,争土地争出来的。
林家死的是林子方、林子明兄弟,还有兄嫂田桂花,是被当“AB”团成员处决的。
杜家死的叫杜召水,就是他舍出性命死咬林家在省苏维埃工作的家人是“AB”团,后来他自己被当着“AB”团清洗了。理由很简单:你不是“AB”团,怎会知道“AB”团的事。
紫苏躲藏的山洞挨那片坟地很近,她正在小心啃着张连长半夜送的一块馍。
林家坟头跪着林子明五岁的儿子磨娃。
磨娃太小,并没搞懂三座新坟严酷的含义,妈叫他跪他就跪,就是不明白为哪样跪了那么久还不叫起来,大人只顾烧纸钱只顾哭,磨娃就偏着脑壳看蚂蚁搬家。他觉得饿,觉得饿得喉咙里伸出爪爪来了。
一阵令人流口水的粮食的清香就是这时候顺风飘过来的。
饥饿难耐的孩娃顺着香味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山洞和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