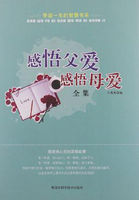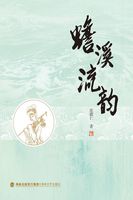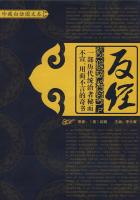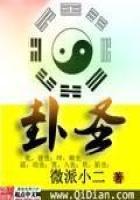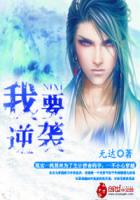六十五、好一个上海滩
在南京逗留的一个月中,我和家人逛了镇江、苏州、上海和杭州。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领略江南美景,虽是冬天,也比东北要婉约得多。
走过几个城市,上海最令我震撼。我觉得上海是全中国“都市化”最彻底的地方,而且有一股异国情调。
最吸引我的是外滩,我在上海几天,天天都要去外滩一趟,流连忘返。
那时候,中国人时兴出门带个旅行袋,人造革面的,上面印有图案,最流行的图案,就是上海外滩和北京天坛了。外滩的景色,虽是“万国建筑博览会”,但也是中国的骄傲。
上海南京路上,有一个著名的地方,叫国际饭店。这地方因为“文革”前的一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而名声大噪。电影里,一个城市新兵因为“吃吃国际饭店”,而受到领导严厉批评,成了迷恋资产阶级生活的典型。
我这次去,当然要去“吃吃国际饭店”。当时吃的什么、滋味怎样,都忘了。据我的小弟后来回忆说,是肉饼,极香。我没有这个印象,只记住了国际饭店。
那时候上海给人以“异国”的印象,除了建筑有特色之外,还有人们的时髦。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上海小伙子,几乎个个都那么有款有型。一身笔挺的铁灰色“涤卡”制服,还要围一条围脖。围脖也有公认的标准花色,是黑底带红点与白点,非常雅致。
“涤卡”是化纤制品,那几年特别流行,取代了棉布,要是放到现在,谁也不会穿。可是每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很不同,是无可理喻的。
别的城市,虽然年轻人也讲究穿戴,但惟独上海青年最用心。
上海人,在任何时候,对细节都很注意。
我那时在上海,跟母亲去拜会了一位“舅公”,他解放前是一个私营厂的老板,公私合营后变为职工,那年他最多才50岁,单位却让他“下岗”,成天没事干,待在家里编汉日词典。
我去,他就跟我讲他编词典的创意,很有成就感的样子。
我问他:能有出版社愿意出吗?”
舅公神色黯然下去,说:编出来再说吧。”
一谈到当下,他立刻嗤之以鼻,咕噜着骂了一句,意思是“瞎搞”。
他叫他的女儿出来,给我们端茶倒水。他的女儿是“宅女”,中学毕业后,不知享受了什么政策,没有下乡,大概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做。
她是我的一位长辈,可是年纪比我小,我注意到她神态娴静,十指纤纤,很像我想象中的“大家闺秀”。
他们住的地方,是老式的高层公寓,虽然旧,但底气还在,有落地钢窗,院子里有绿化。从窗户看出去,是浩瀚的城市。外面很鲜亮,屋子里却很暗、很沉静。
从舅公家里出来,母亲很困惑,说:舅公编这个词典,有什么用呢?”
六十六、春之涌动
从南方万里漫游归来,我又站在了东北的黑土地上。不久,春耕开始,我重操旧业,在漫长得没有头儿的垄沟上点种。
此时再想起大巴山的人和崇山峻岭,我很伤感。
——别梦依稀。
也许有读者要问,那时候的知青,能像我这样随便漫游吗?
可以。我们是插队,不是到生产建设兵团,没有纪律约束。你如果不想干活儿,就不干,没人管。可是,不干活儿,搭上的是什么?是前途。
知青无论是被招工招兵,还是被推荐上大学,都要看“表现”。长时间不干活,表现怎么能好?
就像现在,人人都红了眼地赚钱,你偏要在家里当宅男宅女,法律并不禁止,但你能受得了“落伍”的压迫感和别人的白眼吗?
所以我再怎么漫游,过了半年,也还要乖乖地回来。
乏味的春耕尚未结束,忽然公社来了一个美差。县水利局搞水利设施普查,到了我们公社,需要一批文化较高的知青帮助抄表格,大队在这上面不敢糊弄,就把我推荐了去。
我们一群知青,住在公社招待所,俩人一屋,天天抄表格。
这次抽调上来的,都是各大队知青里的顶级精英。跟我一个屋的,叫老韩,是“文革”前的初二学生,勤奋好学。在公社抄表格的那半个月,只要一闲下来,他就手不释卷地看一本《唐诗三百首》。
我俩挺有共同语言。我们互通了一下消息,都知道今年招生是要凭考试,数理化若不及格,没门儿。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老韩说:我家没权没势,招工上不去。让我一辈子在农村也行,但起码要上一回大学吧。不然活在世上,就一个初二的水平,不甘心哪!”
我们互相鼓励,一定要争口气。每天工作完毕,就发疯似的温习数理化。
这一拨人里,有一个女孩,是公社所在地镇上的知青,是个狂热的美术爱好者,没事儿就画钢笔速写,已有了自己的风格。女孩姓徐,名字很好听。
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也不喜好交际,但我们同时发现了对方。那么勤学苦练的人,我以前从没遇见过。我们有过简单的交谈,只几句话,可说是一见倾心。
那时候,我刚在重庆读完《沫若文集》第一卷,对郭沫若的诗集《星空》佩服得五体投地。《星空》是一组短小、轻灵的情诗,恋爱中的青年读起来,觉得句句都说到了心坎里。
我萌发了第一次真正的爱情,有时候抄着表格,就情不自禁地在桌子上写开了郭沫若的诗句。以前我的恋爱,都是我暗恋人家,现在这次,是我与她心心相印。
那时候,自由恋爱不能公开,否则舆论上认为“作风不好”。我们交谈得很有限,但时时都在牵挂对方。
在抄表活动结速后,徐姑娘又介绍了镇上一大批青年才俊给我,他们各有擅长,有练书汉的,有画连环画的,还有酷爱文学的。我没想到小镇上竟然这么大批量地藏龙卧虎。他们不甘心命运给他们安排的角落,尽可能地要发展自己的才艺,以求出路。
这些人当中,有知青,有青年农民,有工人,还有中学老师。大家相谈甚欢,就倡议办个文学杂志,我连刊名都想好了,就叫《雨花石》。不过后来幸亏不了了之,否则还不知会惹出什么大祸来。
春光灿烂中,我们互相拜访、恳谈,有如现代的“竹林七贤”。这样好像还不过瘾,其中有一个人的哥哥比较有活动能力,就组织我们去了一趟吉林小丰满水电站,游览了闻名已久的松花湖。在去松花湖的路上,那位大哥忽遇熟人,那人很惊讶,问他:你这是干什么?”那位大哥答:都是朋友,出来玩玩。”
那人看看我们一行,都是人中龙凤,不由得夸出声来:浪漫啊,太浪漫了!”
后来,我和这一批人,保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联系。我曾经把他们当做难得的知己,但后来发觉,想在人海中找到这么多知己,是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很快就会大过共同点。
当时代发生变化后,这一批人的命运很不相同,有当了公务员的,扶摇直上,住四房两厅;有下了岗的,变得愤世嫉俗。
然而他们年轻时的蓬勃朝气,无一例外都没有了。
六十七、集体户的老兄
我的插队经历,要是细说起来,比较曲折。从1969年1月起,一共下乡8年。第一年,是在延边的一个县。我们家是南方人,按理说跟这个靠近山沟的县没有任何关系,奇怪的是,我的外祖父壮年的时候,组团考察到过这个县,目的是看一看原始森林。我的母亲也在“文革”前来过这个县,是参加“四清”工作队。然后就是我和中学同学组成集体户,一头扎到了这个县。
跟中学同班同学在一个集体户,还是比较有乐趣的,尽管是瞎混了一年.后来,我的父母下放到离省城不太远的农村,那时的术语,是走“五七”道路。那个年代类似的术语太多了,我这里就不解释了。
我在延边瞎胡闹,干不下去了,就转户口到父母这边来,但身份仍是知青。这样过了两年,国家形势有变,“科技干部”陆续被调回城,父母带着家属就走了。我的身份是知青,回不了城,在生产队也不能独立门户,只能转到当地的一个集体户。
这个集体户,主体是镇上的知青。他们年纪比我略小,出身贫寒,和我大异其趣,我算是勉为其难地和他们相处了5年。
这里说说这个集体户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位哥们儿。
一位是青山兄,笑口常开,但他可不是一个弥勒佛,这种笑,是技术性的笑。
青山兄为人极精明,跟大队干部是能勾肩搭背的。他身上,有一股霸气,一副“没有我不知道的事,也没有我干不了的事”那种劲头儿,古话讲就是“舍我其谁”。
青山兄,镶着两颗金牙,一笑金光灿灿,看到无能的人,能把人家嘲笑死。我在他眼中,基本是废物,他无论说什么,最后都要拐到“我是英雄我怕谁,你这废物还活着干吗”上来。
青山兄不但擅长人际关系,干农活儿也是一把好手,冬天夜长,他没事儿就到农民家聊庄稼经。下乡不到两年,就成了顶级劳动力,所有农活儿,没有他不会的。最后,一半以上的农民干的农活儿,都要被他嘲笑。
我和他关系一度很紧张。在他眼里,学知识,基本跟吃屎一样,他不能容忍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人!
后来我跟他有所缓和,也是不咸不淡吧,他毕竟很难接受世界上生存着一些废物。
青山兄是那个时代的骄子,文武双全,后来大队果然给了他一个机会,到南方当兵去了。到了驻地后,来了信,极为兴奋,说南方兵都叫他“阿山”。
此人后来命运不知怎样,如果转业当了干部,前途会不错。
还有一位是大海兄。
大海兄是一个善良的人,有一点儿窝囊。他被青山兄歧视,自然跟我比较亲。一来二去,成了我的死党。
一次,公社抽调劳力,为石油管道工程挖土方,派去的人有我一个。
大海兄对我说:这活儿太吓人,你干不了,我替你去干吧,豁出来了。”
挖土方,是就连庄稼人听了也要打颤的苦活儿。
干了一个星期,回来后大海兄说:累稀了!这活儿,站在冷水里,一锹要扔上去一米多高,干完活腿都木了,一掐不知道疼。”
大海的小腿因此坐了病,一到阴天就疼。他经常叨咕:这都是那年替你干活儿落下的。”
他是说者无心,我听了每次都很内疚。
大海兄确实有点儿缺心眼,啥事都敢出头,集体户想偷老乡的鸭子吃,也是他出头去偷。
有一次我给本公社一位熟悉的天津女知青写信,谈了谈有关自学的事儿,正好他回家,我就托他寄了。几天后,我们户一位女生忽然给我看一封信,说:这是男生写给我的信,你看看,这写的是啥?”
我一看,愣了——这内容不是我写的吗?再看落款,怎么成了大海?
这小子,把我的信拆了,照抄一遍,写给了心仪的女生。
胡闹吗不是!
我把他叫来质问,他挠着头一笑,没什么解释。我追问:那我的信呢?”
“我重新写了一个信封,给你寄了。撒谎是犊子!”
“你抄那信,她能看懂吗?傻呀!”
他只是嘿嘿地笑。
那年头,《红楼梦》解禁,出了新版,大家偶尔谈起,都说看不懂。大海不服:不就是一本《红楼梦》吗?有啥看不懂?拿来我看!”
我从箱子里拿出《红楼梦》给了他,坏笑着说:你能看下去10页,我管你叫爹!”
他抢过去:“不就10页吗?”“说着翻开,大约是翻到了“贾探春协理荣国府”一段,头绪繁多,才看了两三行,就扔了书,“唉呀妈呀,这是啥呀!”
大海兄看《红楼梦》,就成了众人的笑柄。青山兄笑得直抽冷气:“你还能是那个虫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