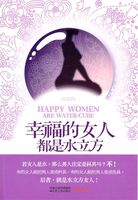会不会就是因为教皇们知道这个不远的结局从而骄奢淫逸地生活呢?他们因此就不再相信他们自己的和他们教会的学说?他们大吃大喝、淫逸无度,是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哥白尼计算出来的那个末日?上帝啊,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解释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座教堂的教皇建起自己的妓院,使他每年赚到八万杜卡特?如何解释他的侄子红衣主教皮耶特罗·里阿利奥,这个有着四个主教辖区、一个教祖管辖区的人最后死于嫖妓?如何解释他们为什么把巴尔达萨莱·考萨推到教皇位置上,虽然明知他与他兄弟的妻子睡觉,还同二百个寡妇和处女交媾?怎么解释亚历山大六世教皇陛下——像萨沃纳罗拉说的那样——搞起来超过畜牲,和他自己的女儿鬼混,还组织纵欲的狂欢会,让五十个女人光着身子跳舞,像小狗一样在地上爬,然后在他眼前被他的皇宫内侍们强奸。怎么解释克雷芒五世连酷刑都不怕,保禄四世连恐怖都顾不上,怎么解释这一切都不是一时的出轨,而是惯例,是令人发指的罪孽呢?
两条强有力的胳膊从后面抓住了雷伯莱希特,把他拉回到现实当中。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一个身穿红色长袍、体格壮健的教皇卫士便将他的胳膊拧到了后背上。另外一个大块头高高在上地冲他吼道:“你在这里干什么勾当,狗东西?”
雷伯莱希特结结巴巴地说出几句道歉的话,说他只顾欣赏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把时间都忘了,说他现在马上就离开。
两个卫士却连听都不要听。他们一个继续按住雷伯莱希特,另一个则在他浑身上下摸了个遍,检查他有没有携带武器。最后,他们便扯着他的衣袖,推推搡搡地带他走过一条没有窗户的长廊,来到一扇门前。门是双重的,进去以后便是一个光秃秃的大厅,令雷伯莱希特恐怖地想起了宗教裁判长巴托洛梅欧修士给他父亲亚当定罪的那个大厅:正面是一张又长又宽的桌子,上面摆着两根蜡烛。
桌后是三张有棱有角的黑色椅子。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一个寂静无声、与外界的一切隔绝的世界。
两个卫士一言不发地消失了,雷伯莱希特惟一能安慰自己的是,他这一生中已经克服过比这更没有出路的困难。他就这样站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厅中央,两扇窗户开向一个窄长而空无一人的内庭。门上没有门把手,这令他害怕。
无休无止的等待。雷伯莱希特没敢在椅子上坐下来。门突然开了,一个肥胖的主教由一个书记员陪同走进来。那个书记员一副超凡脱俗的样子,至少也是升过好几级的,他会把接下来就进行的审讯中说出来的每个字都记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基督兄弟?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有什么目的?”那位主教大人一边辛苦地把自己肥大的身躯落到一张椅子上,一边单调地念出一串问题来。对雷伯莱希特,他连一眼都没瞧。
雷伯莱希特说出了他的名字,讲出他是从德国来的石匠,是圣彼得大教堂所有石匠的工头儿。他是由他的师父卡尔瓦奇先生及其朋友洛伦佐·卡拉法红衣主教带领着从一个侧门进入梵蒂冈的,至于侧门在哪儿,走的是哪条路,他说不上来。
提到卡拉法的名字,显见地引起了肥胖主教的不安。他向那个书记员不凡的耳朵里说了些什么,后者就不见了。
“阁下,”雷伯莱希特用请求的语气说,“我没做任何不好的事情。我的愿望只是看到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没有别的。”
穿着镶红边法衣的教士无动于衷。他的脸上毫无表情,直视前方,目光穿过雷伯莱希特,就好像他是空气。雷伯莱希特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话,他担心那位可能是没听懂,可一切照旧,还是没有回答。
不过,没有雷伯莱希特以为要等的时间那么长,门就开了,又有两个教士走了进来,极为贴切地体现着上帝在创造世界第六天时的情绪。一个是巨人,比雷伯莱希特还高,却又瘦又是一副禁欲的样子。另一个是敦实的小个子,矮得好像人还在尘世上,却已经开始受炼狱里的罪了。
这小矮子颐指气使的声音显示出上帝赐给了他比另外两人更高的级别——那两个在桌边一左一右,像是做弥撒时的助手。
“这么说你是卡拉法红衣主教那一伙儿的喽?”那侏儒喝道,“而你竟然还敢承认这一点!”
顿时,雷伯莱希特知道自己提到红衣主教的名字显然是犯了个错误。洛伦佐被认为是他叔叔的继任者的死对头。现在他也知道为什么红衣主教和卡尔瓦奇两人突然之间就跑掉了。
“大人,”雷伯莱希特又开了口,“我……”
“闭嘴!”侏儒堵住了他的话头儿,“你和那个扬言上帝告诉给他一个秘密的恶棍贝内蒂托·阿克尔蒂穿一条裤子。上帝只跟他在尘世的代言人说话,而不是跟一个走旁门左道的。”
“我不认识什么贝内蒂托·阿克尔蒂!”雷伯莱希特反抗道,“我从弗兰肯来。在那里,我师父卡尔瓦奇先生教会了我石匠手艺。几个月前我和我妻子才刚刚来到罗马,而卡尔瓦奇让我当上了圣彼得大教堂所有石匠的工头儿。”
“哈!”小个子教士叫道,“你又把卡尔瓦奇的好名字端出来,好把你的脑袋从绞索套儿里褪出来。你就放心吧,我们会从你嘴里挤出真话来的,凭所有圣徒的名誉!”
“这就是真话!您去问我师父卡尔瓦奇!”
“已经去问了,可怜虫!他这就来。”
不长时间,卡尔瓦奇就激动地出现在门口了。三个教士友好地向他问候。没等那个侏儒教士说出话来,卡尔瓦奇就开始激烈地指责那些把米开朗基罗大师的意愿用脚踩的教会仆人。而雷伯莱希特是参加大教堂建造的最能干的艺术家,是米开朗基罗大师亲自派到这里来研究西斯汀天顶画的人物结构的。把他说成是异端邪说分子的党徒,实在是不光彩——他实际上是教皇庇护四世狂热的拥护者,千里迢迢从德国赶来罗马,就为了不计报酬地把他的艺术奉献给圣彼得大教堂啊!
三个教士阴郁的面部表情随着卡尔瓦奇说出的每个经过推敲斟酌的句子越来越明朗。雷伯莱希特惊讶极了,看来,师父在教廷里享有很高的声望呢。
侏儒大人边听卡尔瓦奇的话边从头到脚地打量雷伯莱希特,似乎在说:“你等着吧,我们还会再抓住你的!”他画了个十字,急急地说出一句:“以我主的名义,您自由了。赞美耶稣基督。”
像来时一样,三个教士飘然而去,穿红衣的卫士又出现了,引着雷伯莱希特和卡尔瓦奇穿过梵蒂冈迷宫似的走廊,到了那个他们进来时走的那个侧门。暮色笼罩着圣彼得广场,火堆已经点燃。雷伯莱希特呼吸着冬天寒冷的空气,对卡尔瓦奇说:“师父,您做了什么啊?您说的话里,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卡尔瓦奇讥讽地笑了,指着他们的来路道:“墙里面才是虚假的家。谎言、违约、假誓、骗局、分裂、伪装在那里大获全胜。一件教袍不能造就僧侣,教皇的袍子也不能造就教皇。在圣彼得的陵墓之上,魔鬼和他的帮凶大摇大摆,横行霸道。”他啐了一口,口水划了道长长的弧线,落在沙地上。
雷伯莱希特对他师父这种大胆的言论并不感到惊奇,他了解他的观点。让他惊讶的是卡尔瓦奇在教廷享有很高的声望。
“声望?”卡尔瓦奇针对雷伯莱希特的问题这样答道,“谈不到什么声望。那些教士需要我,更胜过弥撒需要敲钟。自从教宗犹利二世一五零六年为这个庞大的工程奠基,有八个教皇都自以为能够完成它,以自己的名字建造一座纪念碑。庇护四世看到自己比他所有的前任都更接近目标。说到建成圣彼得大教堂,他像一条狗那么贪婪。最挂在他心上的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天顶。我想,要是我能向他保证他能看到穹顶的建成,他能把他的灵魂都卖了。”
“您认识教宗?”
“不直接认识他本人,但是每天晚上都可以从近处看到他。”
雷伯莱希特难以置信地望着师父。
卡尔瓦奇注意到了他的将信将疑,便拉住他的袖子说:“跟我来!”
雷伯莱希特本想挣开,说他今天对梵蒂冈已经够烦的了,但当他发现卡尔瓦奇是往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大广场上走,他便不由自主地跟他走了。
广场上像平时一样充满忙忙碌碌的气氛。放在滚子上运输的巨大石块掀起团团灰尘,让人直流眼泪。口令号子响彻整个广场,其间夹杂着在这里寻找残羹剩饭的野狗的吠叫。还有不安分的骡子驴子的嘶叫声,大车、小车被牵引着压过千疮百孔的地面。
“看那儿!”卡尔瓦奇指着右手方向的教皇皇宫。
黑暗之中,二楼的第二个窗户里显出一个光秃秃的头顶。那老头儿像尊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地望着未完成的穹顶方向。
“每天晚上你都能看见他这个样子。他有时候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谁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他在祈祷。”
“你说教皇?”
雷伯莱希特耸耸肩膀。
他们一同走回建筑工棚的路上,刚才在梵蒂冈那场突如其来的经历让雷伯莱希特一时还消化不了,他问:“那三个可怕的教士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卡尔瓦奇回答,“迄今为止我没见过他们,这毫不奇怪。教廷里的每件事都有一个专门的高官显贵在负责。然而,绝不是说,他们配得上那些高贵的称号,只是那些称号把他们抬举了起来。”
“这该让我如何理解呢?”
“就是说,在教廷里谋得职位的人,很少是真的对那个职位上的任务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不过是得到那个职位后就可以得到的利益——从卫士到红衣主教都是如此,而且,教皇也是如此。”
走进建筑工棚之前,雷伯莱希特叫住师父,冷不丁问出一个问题来:“谁是贝内蒂托·阿克尔蒂?”
“阿克尔蒂?你怎么想起问他?”
“审讯的时候,那个侏儒似的教士说,我跟这个贝内蒂托.阿克尔蒂穿一条裤子。”
卡尔瓦奇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浓黑的眉毛弯成了半月形:“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把你当成贝内蒂托·阿克尔蒂身边的一个阴谋家了!”
“您都知道他的什么事?这是一个怎样的神秘人物?”
“曾经是,我的孩子,他曾经是一个神秘人物。宗教裁判所今天把他在火刑堆上烧死了。”卡尔瓦奇做出个鬼脸来,像条狗一样鼻子在空气中嗅来嗅去,“今天中午,在鲜花广场上,台伯河的另一岸。”
师父的话令雷伯莱希特打了个冷战。他轻声说:“宗教裁判所要追着我追到地球的最后一个角落吗?”
卡尔瓦奇笑了:“首先,罗马肯定不是地球的最后一个角落,另外,你得理解教廷的气愤。阿克尔蒂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他走过燃烧的煤炭,以此证明上帝就在他体内。他宣称,上帝委托他把天主教会和那些背叛者重新结合统一起来,庇护四世不适合做这项工作,所以他想要教皇的命。他最信任的亲信安托尼奥·卡诺萨告了他的密,他被抓了起来,宗教裁判所判他火刑。现在教廷里的教士害怕每一张陌生的面孔也就可以理解了。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教皇被暗杀了。”
雷伯莱希特沉默不语。他觉得很难相信卡尔瓦奇的话,怀疑他讲的是不是真话,他是不是只不过想安慰他。他的被抓真的只是因为他们搞错了人,还是新的危险又已经在他的头顶上聚集了起来?
不过总之,米开朗基罗和他的西斯汀巨幅天顶壁画使雷伯莱希特更加相信,肯定有更多的人知道那颗星,那颗正势不可挡地接近地球、在不远的未来将毁灭一切生命、抢圣经和其中预言的上风的星,比他到目前为止设想的人数还多。米开朗基罗大师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他为什么只借助画上那充满暗示、只有很少人能理解的场景呢?更主要的是——雷伯莱希特自问——大师是怎么知道那颗星呢?
他越是思来想去,就越是明白自己非得给哥白尼的那本书找一个更安全的藏匿地点不可。他房子的屋顶下面并不安全。他先是想到把书砌进圣彼得大教堂的墙里,肯定不会有人到那里去找它。但转念一想,每天都有新的图纸要求新的增建、改建,他还是得找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最后,一个偶然机会帮了他的忙。
米开朗基罗大师的学生迪奥梅德·雷奥尼肩负着一个任务,他每天两次从建筑工棚出发,经过地下宫室,绕过西斯汀教堂,沿着扎蒂尼大道前往梵蒂冈的秘密档案馆,取当天需要的局部图纸,晚上再原路送回去。这是大师的愿望,因为他总是担心艺人和石匠中的某个恶棍可能会盗窃复制他那些细致入微、能装满一辆大车的设计图纸,到别的地方去建造宫殿。所以,雷奥尼每天晚上都把用过的图纸送回到档案馆的密室里去。
大概是魔鬼令雷伯莱希特想起了以前鲁伊特格修士在米歇尔山的本笃会修道院图书馆里对他说过的话:“对一本书来说,有什么地方比混在其他书之中更安全的呢?”宗教裁判所的那些密探们再怎么猜,恐怕都不会猜到哥白尼的那本书会藏在梵蒂冈的秘密档案馆里。
于是,雷伯莱希特开始思索他该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到秘密档案馆里去,大师的图纸保存在那里的卷宗、文件夹总汇里。大约也是那同一个魔鬼给了他如下的主意,他想出一个借口:为了继续石匠们的工作,某一张图纸他需要再用一遍,便和雷奥尼一起去秘密档案馆找——其实根本不存在那么一张图纸。对大师的图纸再熟悉不过的迪奥梅德·雷奥尼去找雷伯莱希特想要的图纸,而甫伯莱希特呢,则趁他不留意,把哥白尼的书从他的外农下面抽出来,插进了一个叫做《关于自由》的文件夹里,并且牢牢记住了这个题目以及“哈德良六世元年”几个字,这指的是教皇哈德良六世当上教皇的头一年,即公元15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