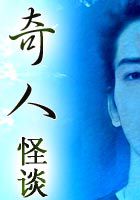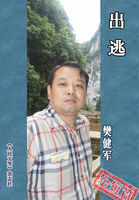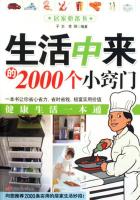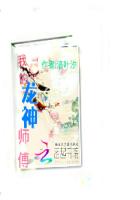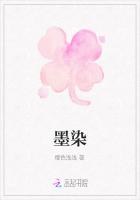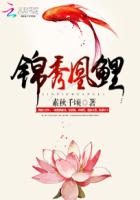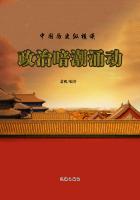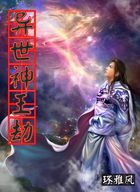海华德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了。昏黄的灯光下,她辨别出这里是有一年自己曾经患急性痢疾时住过的岳阳塔前街普济医院,也是一家由教会方面创办的医院,是当时岳阳最好的医院。这里的首席医师琼·汤姆生先生是她的好朋友,一个瘦高个子红脸膛的美国人,这次担任了抢救她的主治医师。
病房不大,但房间里除了厕所以外什么都有,卫生也很好。而门外的走廊上,就有能够放水冲洗的公共厕所,还有开水和热水供应,有公共浴室。医生护士大多是金发蓝眼的欧美人,也有少量的华人职员。
醒来的时候,豆豆、邱惠敏正站在她的病床前,俯身看着她。方婶娘在床对面一把躺椅上睡得鼾声如雷,估计是累得够呛。海华德知道,方婶娘的鼾声越大,表明她越劳累。好在她已经习惯方婶娘的鼾声了,正是这熟悉的鼾声,混合着来苏尔的刺鼻气味,将她从深沉的昏迷中唤醒。
据豆豆讲,大岛正川和海华德被同时送到普济医院,大岛没有抢救过来,而海华德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在赫尔威利大主教的严正干预下,日本军方也只好将这件事确认为一起感情纠葛。考虑到海华德德国人和教会职员的特殊身份,没有再找她的麻烦。唯一的遗憾,是她的子宫颈被军刀切断,修复手术失败,她再也不能生育了……
醒来一会,她伸手示意邱惠敏扶她起来上厕所。豆豆连声道:“校长躺着,校长躺着,千万莫动,千万莫动!”说着就将一个搪瓷便盆熟练地塞到了海华德身下。
经过这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她与豆豆之间,也没有那么多顾忌了,大家都很坦然,只有邱惠敏的眼中闪现出一丝很复杂的神情。
在接下来的漫长的病床上,一种深深的自责总是在困扰着海华德。特别是一想起深爱着自己的冯·李斯特不能与自己生儿育女了,她就感到非常地对不起他,就后悔分别时的犹豫,没有为他、也是为自己留下一点骨血,这是自己和爱人永远的遗憾。她想将来需要有孩子的时候,只能从别人那里带养一个了。她甚至开始向豆豆表达这样的意思,想让他帮着自己到乡村里去带养一个孩子。“我知道冯·李斯特很喜欢小孩子,”她说,“我也一样,很难想象一个家庭要是没有小孩子的话,会有多少欢乐……”
豆豆对她的要求,一开始还有点热心,可是当她在漫长而寂静的病床上,想确定这件事情的时候,豆豆却变得沉默不语了,像是不大愿意给她帮忙,又像是无法帮这样的忙。那时候因为出生率高,弃婴与过继,在地方上很普遍。她对豆豆的态度很不理解。自己牺牲了宝贵的生育能力来为豆豆杀了大仇人,为什么这么点子事豆豆不愿意办,办不好……
直到住院期满,回到学校,她才揭开了谜底。
住院近两个月后出院,在师生们的欢迎仪式之后,她有点兴奋地走进了自己已经被方婶娘擦洗得窗明几净的绿楼校长办公室。日本人全部从这里撤走了,这也让她感到莫大的欣慰,悬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到了地上。
在出院的前一天,她对赵阿勇和方婶娘说:“要把绿楼给我彻底打扫干净,一丝丝日本鬼子的气味都不能留下!”从血与火的噩梦里走出来的她,现在也像每一个被侵略的中国人那样憎恨日本鬼子,同时也为日本鬼子终于从学校里滚蛋而庆幸。
可是,她在办公室里待了不到五分钟,就用巨大的哭叫声,将早有所备而守候在屋子外面的豆豆召唤进来——
桌子上摆着一封电报,电文内容是这样的:“尊敬的汉娜·海华德小姐阁下,我们不得不万分沉痛地告知您,您的未婚夫克劳斯·冯·李斯特将军,已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九日在埃及的阿拉曼战役中为国英勇捐躯,我们谨代表德国元首和政府,对其致以无比深切的哀悼。请您原谅并保重。”
落款是德国陆军部。时间是半个月前。
“这就是命运吗?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命运吗?”她扑在豆豆怀里,紧紧抱住豆豆的肩膀,哭得天昏地暗,“上帝呀上帝,你为什么把我的亲人一个一个都夺走呀?你为什么把这么多的灾难降临到我一个人身上呢?”
她再一次想起那句母亲写给父亲的话:“你要是死了,那我也不活了。”同时她想起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是的,是的,”她在心里对自己说,“生命的确是宝贵的,可是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你,我的爱人,我的灵魂,我的心肝宝贝,生命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躺在阳光与月光交替徘徊的窗棂下,她只想静静地等待着死与消亡。
整整一个星期,她没怎么进食,躺在床上不愿意起来,两只眼睛像盲人一样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眼圈黑得像戴上了一副深色框的眼镜。她气若游丝,宛若一个行将就木之人。豆豆事后说,那几天她的样子,看上去比在普济医院时还吓人得多。
要不是方婶娘和豆豆日夜不停地苦苦哀求她保重身体,分分秒秒与巨痛中的她不离不弃,她也许就不会再进食了,也许就这样在自己的床上告别了人世。
海华德家族的精神传统再一次唤醒了她,挽救了她。活下去!活下去!简洁而固执的理念,帮助她再一次战胜了自己。她在天堂充满诱惑的门槛前逗留了片刻,就被现实世界的强大魅力给拉了回来。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怎么可以就这样轻易离去?
又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在豆豆的搀扶下,她拖着轻飘的身体,登上了龟山的山顶,在那里亲手为冯·李斯特建了一座衣冠冢,放进去了三样东西:冯·李斯特曾经穿过的黑袍校长服,冯·李斯特在校园里风华正茂的留影,再就是冯·李斯特生前最喜欢的那支瓦尔特牌手枪。冢的顶上,按欧洲的风俗,竖立了一只小小的十字架,用月山特产的青石刻制,上面镌刻了克劳斯·冯·李斯特的名字和生卒年份。
秋风掠过湖山,湖水波翻浪涌,山树枝摇叶舞,共同发出哀声,像是在与海华德小姐共同诉说着人间的不幸。伫立山巅,时年不满三十岁的海华德小姐,觉得自己已经流尽了给冯·李斯特的眼泪,心中那道感情的闸门早早地、早早地封闭起来了。
——海华德怎么能想到:此时的冯·李斯特,正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中,摩挲着那少半截红玉手镯,一刻不停地思念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