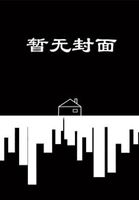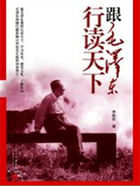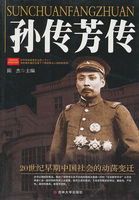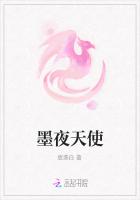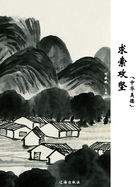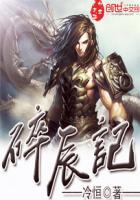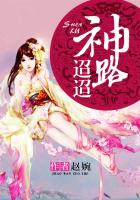陈先瑞(1913~1996),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手枪团班长,鄂东北游击司令部特务4大队分队长,红25军手枪团中队长,224团营政治委员,223团政治处主任,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司令员,红74师师长。坚持了鄂豫陕边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留守处主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警备第4团团长、警备第1旅副旅长,豫西抗日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豫西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豫中军分区司令员,桐柏军区副司令员兼独立第3旅旅长,中原军区第2纵队15旅政治委员,豫鄂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副军长,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陕南军区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19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陈先瑞出生在河南省商城县(今属安徽省金寨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家里贫穷,父亲终身务农,为人善良,勤劳朴实。陈先瑞从幼年时起就经常上山割草、砍柴、放牛,九岁那年上过一段时间的私塾,后因家境贫穷而辍学,一直在家里劳动。在幼年的生活里,陈先瑞就经历了地主和富人欺压穷人的日子,深感世道的不公。
1929年5月,立夏节起义的烽火在商城县南部燃起,陈先瑞报名参加了儿童团,并被选为团长。在当地群众积极支前报名当红军的热潮中,陈先瑞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来到红32师第98团,当了一名勤务兵。次年,陈先瑞所在的红32师改编为红1军第2师,陈先瑞成了红2师师部的一名通信员。他工作积极,作战勇敢,于1931年6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1932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的苏家埠战役中,陈先瑞被任命为特务队的红军班长。他带领全班战士,广泛开展侦察和情报搜集活动,摸清了合肥方面敌人的详细情况,为红军作战奠定了基础,由于陈先瑞这个班的情报及时准确,红军以少击多,巧设埋伏,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活捉了敌人的总指挥。陈先瑞经历了战斗的磨炼,迅速成长起来。
1932年9月,红四方面军经过第四次反“围剿”战斗,转移到皖西一带的金家寨地区,与红25军会合后,将红25军第74师分编到其他主力师中,陈先瑞仍担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手枪团班长。在几次战役中,陈先瑞带领全班打得很出色,成为英雄模范班。不久,陈先瑞被任命为1分队队长。
年底,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为了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中共鄂豫皖省委重新组建了红25军。陈先瑞所在的特务4大队编入红25军手枪团,下辖三个中队,直接归红25军领导指挥,担任保卫军部的作战任务,陈先瑞被任命为手枪团第1中队中队长,成为手枪团中的战斗骨干。
1934年4月,红25军和在皖西的红28军在商城会师。两支部队改编以后,红28军编入红25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红军力量有了很大加强。11月16日,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大旗,由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征。
出发前,陈先瑞听说军部首长正在研究转移中的干部配备和人员去留问题,他怕领导把自己留下,不让参加长征。因为陈先瑞在几个月前的长岭岗战斗中,正指挥部队后撤时,敌人的子弹打在他站的小坡上,有几名战士负伤,他只觉得脚下突然很酸,便倒下了,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脚左面进去右面出来,负了重伤,被送到群众家里隐藏养伤。按照他的伤情必定是在留下的名册中。
陈先瑞坚决要求参加长征,他知道在这关键时刻,自己不去亲自表明态度不行。他走进军首长正在开会的会议室时,把拄的木棍一丢,“啪”,一个立正报告说:“我伤已痊愈,要求归队!”他报告完后,故意往前走了几步,表示可以走路了。其实,陈先瑞的伤情军领导已查过了,心里有数。军政委吴焕先拍了拍陈先瑞的肩膀说:“坚强的精神可嘉,但伤未好也是事实,你哄骗不了我们。”
陈先瑞看到军首长对自己的伤情非常了解,只好如实地讲了自己的伤情,但坚决要求随军行动。
徐海东军长了解陈先瑞,怕他再纠缠,说:“你先回去准备一下,待我们研究后再决定。”停了一下,他又说:“谁都不愿意留下,还真要认真一点做工作哩!”说完,他向陈先瑞挥了挥手,意思是让陈先瑞放心回去。
陈先瑞回到营里,见大家都在积极准备,每人准备了两双草鞋,三天的干粮。当时,大家不知道是长征,只知道是“打远游击”,到新的地方开创根据地。
第二天,吴焕先政委找陈先瑞谈话,正式通知陈先瑞调到第223团任政治处主任,带伤随军行动。为保证不掉队,还给陈先瑞配了一头毛驴。
俗话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尽管陈先瑞坚决要求随队远征,可是眼下部队出发了,他和大家的心情一样,有一种惘然若失,依依不舍的心情;有一种流离失所,一日九迁,无家可归的感觉。
红25军远征之路,虽然没有雪山,没有草地,但有自身的独立的特点,同样经历了上下交困,左右为难,山高水险,荆棘塞途,艰难险阻,坎坷不平之路。
革命不会有平坦的路,也不会有直路可走。红25军从桐柏山向伏牛山开进中,为了躲避敌人堵截,舍近求远,选“之”字形或“弓”背路走,哪里敌人防守薄弱往哪里突,看起来走的是冤枉路,但保证了部队的安全。陈先瑞骑着毛驴,随着部队一会儿东奔,一会儿西跑,终于走出了山区,到了豫西的平原地区。从泌阳以东向北开进,沿途地势平坦,凡是山水好的一些地方,都有围寨。一些大的围寨,高墙耸立,壁垒重叠,为地主豪绅所盘踞。他们有相当数量的武器,如土枪、土炮,能攻能守。有的寨墙筑有几米深的护寨河,四周深水环绕。寨子的出入口,用可以升降的吊桥过河。一些寨子,可以遥相呼应,遇劫寨者,烽火告示,相互支援,俨然成为一座座易守难攻的堡垒!是一座座难以通过的村寨!
陈先瑞看到进入平原后,部队常遭到围寨武装的阻拦,遭冷枪冷炮的打击,不时有人伤亡,部队又不能还击,大家有意见。当听到许多战士叫骂声、怨恨声时,陈先瑞也很着急,但他还是尽量做大家的思想工作,稳定部队的情绪。
军政委吴焕先针对部队遇到的新问题,不仅积极做部队指战员的工作,而且积极做地方群众的工作。他要求部队张贴布告,广泛开展宣传工作,把党和红军的政策编成口号、快板:“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寨,奉劝乡亲,切勿阻拦!”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群众了解了红军,再经过村寨时,能顺利通过,还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红25军为了摆脱敌人追击,早日进入伏牛山区,而疾速前进。11月26日,正遇寒流突然降临,先是下小雨,后是漫天雪花,真是雨雪交加。昏暗阴沉的天气,把无遮无拦的中原大地搞得浑浊迷茫。因为视眼不开阔,陈先瑞所在的团担任后卫任务,为了安全起见,部队采取交替前进的战术,一部分部队占领阵地后,另一部分撤退,以防敌人突然追至而不及防。部队在交替前进中,听不到大的动静,只听到风在吼,只见到雪花在飘、雨在下。这突如其来的天气,像一张无形的巨网,把红25军严严实实地笼罩了起来。
陈先瑞见指战员们衣着单薄,饥寒交迫地在泥泞的路上挣扎,行进十分困难,心里很难受。这时,许多战士的草鞋和袜子都被烂泥粘掉了,在赤脚行军。陈先瑞看到病号和重伤员行动非常吃力,就坚持把毛驴让给比自己更困难的人骑。
中午时分,先头部队到达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时,突然枪声大作,国民党军第40军115旅和骑兵团预先在独树镇一带设了埋伏,红军如盲人瞎马,毫无所知。遭到敌人突然打击,红军措手不及。战士们因手指冻僵,一时拉不开枪栓,零星地打响几枪,不能有效地反击敌人,又处于平坦地形,红军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红军处境危险,进退失据,天台路迷,被迫后撤。敌人乘机冲击,从两翼包抄而来,形势更加险恶!
在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军部参谋主任薛仁阶(绰号“金大牙”)临阵怕死,大嚷大叫:“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公路过不去了,大家各自逃命吧!”许多战士把“金大牙”看成是军部参谋中的小头头,以为他是代表司令部说话,不明真相,在“金大牙”的煽动下,队伍中出现骚动,松散的人群,四处乱跑,失去了战斗力。正在这关键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跑步赶到,一眼就识破“金大牙”的鬼脸和阴谋,命令人把“金大牙”绑了起来,然后带领部队冲向前,并高喊:“就地卧倒,坚决顶住,绝不许后退!”在吴焕先指挥下,红军很快稳住了阵脚。原来不明真相、慌乱失措的班长、排长,很快清醒过来,指挥战士们利用地形地物,摩拳擦掌抗击敌人。
敌人虽遭到反击,仍气势汹汹地向红军扑来,必须打掉敌人的气焰!吴政委伸手从身边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声:“共产党员冲啊!”冒着敌人的射击,带领部队冲入敌阵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一时间,刀枪碰撞声、喊杀声,震天动地。这一反击,鼓舞了红军战士杀敌勇气;这一反击,为红军争得了短暂时间,使后续部队及时投入战斗。
徐海东随后卫行动,听到前面激烈的枪声,知道形势危急。军人以枪声为命令。徐海东立即命令223团团长带一个营断后,自己带团主力跑步向前冲去。这时,陈先瑞虽然走路伤还生疼,仍强忍着疼跑步前进。当他跑到前面,看到吴政委正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反攻。
徐海东带领陈先瑞所在的团投入战斗,红军战士群威群胆,披坚执锐,临危不惧,浴血奋战一次又一次地将敌人反击了回去。经过了几次恶战,敌人暂时停止了冲击。红军也停止进攻,就地固守,一场恶战转为僵持状态。
这一仗,敌人伤亡惨重。红军伤亡近300人。1营政委负重伤,军首长立即决定由陈先瑞兼任1营政委,因为1营是223团主力,必须加强领导。
红军一直坚持到天黑,这时天气状况更加恶劣,特别是雨很大,红军乘机转移到十几里外的杨楼一带村庄休息,躲避风雨。进村后,准备做饭吃,可是一进村,还没有吃上饭,又来命令,要准备走。军领导考虑必须连夜突出重围,否则,天一亮,后敌追上来,前敌再一堵,红军腹背受敌夹击,又是孤军奋战,后果不堪设想。
陈先瑞和营长立即集合部队,可是部队经过连续几天急行军,加上这场恶战,战士们已经疲惫不堪,饥饿难忍。陈先瑞感到最难的是安置伤病员,他给营里几名重伤员做工作,他们死也不愿留下,后来只好采取了强制措施。
部队连夜不顾风雨、道路泥泞,不顾一切困难,浴血奋战,经叶县保安镇以北的沈庄附近,穿过许南公路,突出了重围。
1934年12月2日,红25军由嵩县境内的东村、孙店、栗树街等地,向卢氏县的栾川(今为栾川县城)开进。
红25军长征时,没有地图,主要靠手枪团侦察、请当地群众当向导,向大的方向前进。程子华军长到后,他从中央苏区带了一本袖珍地图,后来全靠它来判断地理方位。地图虽然比例尺很大,但它仍是全军之宝物。
3日,陈先瑞和营长带领全营尚未到卢氏县城天色已晚,当他们到了城南时,已经是深夜,到了城西,要过一座木板搭的桥,陈先瑞带一个班是最后过桥的,当他上了桥后,突然从桥边山上打来一梭子弹,陈先瑞觉得左腿一颤抖,身子一歪倒下了桥,幸亏桥不高,水也不太深。几名战士立即把陈先瑞抬上了岸。与陈先瑞同时受伤的还有两名战士,都是伤在腿上。陈先瑞要大家立即过河,于是几名负伤人员被连拖带抬过了河。
陈先瑞到了河西岸,要求全营立即做好战斗准备。这时,吴焕先和徐海东等军领导来看陈先瑞的伤情,看到陈先瑞伤得走不了路,一面安慰陈先瑞,一面指挥部队撤退。第223团团政委赵凌凌也走到陈先瑞身边,看到陈先瑞躺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提出让陈先瑞留下隐蔽在老乡家里养伤。陈先瑞坚决不同意,还和赵凌凌吵了起来。
吴焕先和徐海东听到陈先瑞闹着要跟着部队行动,走过来也劝陈先瑞留下,让他安心养伤,等部队打回来时一定把他带走。徐海东怕陈先瑞还不放心,进一步对陈先瑞说:找的人家如果对你有一点不好,我们回来和他算账。
陈先瑞完全理解军首长的善意,也清楚部队在急速转移的情况下,让自己这样一些重伤员随部队一起行动,会有很多的困难,会有很大的危险!
陈先瑞是第二次负伤了,所以,不管谁说什么,他也不同意留下。陈先瑞流着泪恳切地说:你们实在要我留下,请求你们再给我补一枪,否则,我是不肯留下的!
军领导看到陈先瑞态度非常坚决,最后终于同意他随队转移。
经过红军长征那血与火的考验之后,从1935年夏到1936年底,陈先瑞独立坚持了鄂豫陕边区的游击战争。由于与上级失去联系,在斗争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陈先瑞转战于鄂豫陕三省边区的几十个县,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取得了鄂豫陕边区游击战争的胜利。他率领的部队,成为一支军政素质好,作风顽强,善于游击战争的比较正规的红军部队。
陈先瑞率领部队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原则和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实行灵活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和巩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牵制了国民党军十几个团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主力红军的长征,敌人无可奈何地感叹:“红74师真是一支神奇的部队!”
经过土地革命战争的锻炼,陈先瑞从一个普通的放牛娃,逐步成长为一名能征善战的红军将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华北,平津失守,上海危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境地。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74师合编为陆军第115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下辖第343旅、344旅、独立团等,陈先瑞任115师留守处主任。后来,115师留守处又改编为陕甘宁留守警备第4团,陈先瑞任团长,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光荣任务。
陈先瑞随部队来到三原县城执行改编任务,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彭总亲切地称赞红25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特别是红军主力离开陕南后,这支部队单独坚持了陕南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鄂豫陕边牵制国民党军,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也配合了陕甘边区的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后,红25军成为党中央与国民党谈判的一个很重的筹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