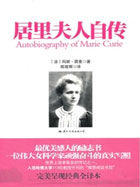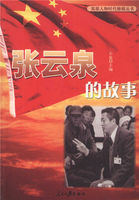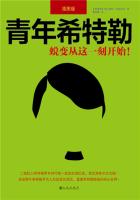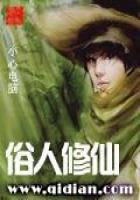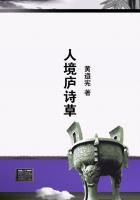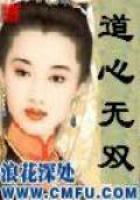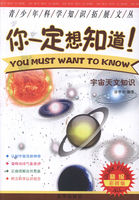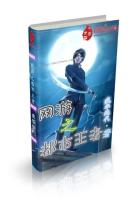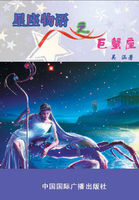中国的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可谓是历史悠久。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上具有一定历史优越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渐暴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1895年,清军惨败于日本。1900年,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城。堂堂中国四万万同胞,难道就没有一个可用之才?惨痛的教训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反思自己的人才选拔方式:不是大清国没有人才,而是大清国选拔人才的制度出了问题。改革科举制度已经是迫在眉睫。
1901年,从西安返回北京的慈禧太后决定实行“新政”,张之洞被任命为参预政务大臣,和刘坤一、袁世凯以及众位军机大臣一起参与这次改革。张之洞和刘坤一积极响应朝廷变法的号召,两人联名上书三折,这就是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
“江楚会奏三疏”的第一疏讨论“育才兴学”,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主张设学堂、变科举、停武科、奖游学;第二疏讨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第三疏讨论“采用西法”,主张向西方学习。以上内容,朝廷几乎全部批准,这也拉开了张之洞废除科举的大幕。
最早被废除的是武科举。武科举始创于唐代,盛行于明清。不过,武科举的受重视程度不如文科举,而清代对武科举的重视要超过前朝。武科举考试,主要是考骑马射箭一类。在冷兵器时代,这些技能确实大有用处。然而,西方新式枪械传入中国后,武科举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了。另外,全国各地早已开办了大批武备学堂,用于培养新型军事人才,这也使得武科举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张之洞在“江楚会奏三疏”中强调,要改革文科举、废除武科举。
关于废除武科举一事,大臣荣禄早在1895年就已经提出。当时,荣禄指出,军队装备新式火器以后,旧式武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继续保留武科举,必然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要。荣禄主张各省应该设立武备学堂,用西方新式军事理论培养军事人才。然而,朝中上下并没有多少人响应荣禄的提议。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武备学堂尚未盛行,许多人担心一旦取消武科举,会断了很多人的官路。其实,这是很多官吏为自家的晚辈后生留出路。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朝中官员在明知武科举已经毫无必要存在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举行武科举。由此可见,既得利益集团维护旧制度的决心是何等的坚定。
戊戌变法时,维新派再提废除科举一事。不过,他们的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他们废除科举制的设想也不可能实施。
1900年的惨败让清政府下定了“变法”的决心。趁此时机,深感科举误国的张之洞再次提出科举改革。张之洞的提议属于渐进式的改革,他只要求先废除武科举,对文科举进行相应调整。这一次,废除武科举的提议再也没有遭到大规模反对,一来是清政府在与八国联军的较量中惨败,而参战人员不少都是武科举出身,事实面前他们无力狡辩;二来是武备学堂的大规模兴起,使得许多有志于投身军旅的年轻人进入武备学堂,此时武科举的作用已经逐渐被武备学堂取代了。终于,在1901年,清政府下令废止武科举。
同样是在1901年,文科举也开始改革。在文科举改革中,变化最大的一项莫过于废除八股文,改为考策论。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拼凑成文。这种文章考的不是考生的思维能力,而是死记硬背的能力,同时,又极大地限制了思想的独立和自由。梁启超评价八股文时指出,学子为了做好八股文,只知道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所谓的“四书”,其他一概不看,结果竟然都不知道刘邦、李世民是何人。所谓策论,是指议论当前政治问题、向朝廷献策的文章。也就是说,考生再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想要在科举中取得成绩,就必须了解时势,而且还要有自己的见解。这一改革,对于那些只知道读死书的腐儒来说当真是灭顶之灾。
但是,此次科举改革并没有改到预期的程度,清政府害怕一旦科举大改会让读书人寒心,所以最终仅仅调整了考试的内容。对于张之洞等人提出的把科举取士的名额分出来一部分给新式学堂一事,朝廷并不同意。不过,让人欣慰的是,朝廷并不反对新式学堂的发展。
对于兴办新式学堂,张之洞也非常热心。他借此机会在湖北建起了不少学校。然而,随着新式学堂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弊端不仅没有因为改革而消除,反而日益明显。科举重在功名,考中就能进入官场;而新式学堂重在培养可用于国家建设的知识型人才,而不是培养将来的官吏。面对进入官场的机会,大批在新式学堂求学的学子不再专心于学术、技术的学习,而是全力应对科举。这样一来新式学堂里绝对是走不出工程师、技术员的,如此下去,张之洞培养新型人才的计划就要落空了。
看来,只要科举还在,学子们就不可能去搞研究、学技术,没有技术型人才,国家又如何强盛呢?基于此,张之洞不再对科举抱有幻想,废除科举已经成为他唯一的选择。
同样体会到科举弊端的还有袁世凯等人。1902年底,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会见了张之洞,两人商议改革科举一事,并约定联名上奏朝廷。1903年3月13日,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及山东巡抚周馥、署湖广总督端方等奏请朝廷加大科举改革的力度。
但是,此时依然有人不愿意放弃科举制度。军机大臣王文韶(1830—1908)就是一个科举制度的坚定拥护者。王文韶当时担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做臣子做到这个等级,已经是到了极致。这么一位朝廷重臣,本来并不是什么“倔脾气”,反而是个老滑头。当时,有人送他外号“油浸枇杷核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枇杷核本来就很光滑,再用油浸泡一番,肯定是更滑了。他还有个外号,叫“琉璃蛋”,也是滑不溜手的意思。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老滑头,反而坚决反对废除科举制度。对于废除科举这件事,王文韶声称,只要他还在朝廷当官,他就会以死相争。为了维护科举制度,连命都愿意搭进去。
张之洞、袁世凯他们这几位在当时的人气确实很旺,可是,人气再怎么旺他们也是地方官,只是奉命参与变法一事。这时的王文韶,绝不是他们这几个地方大员可以撼动的。王文韶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势力呢?这要“归功于”八国联军。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而逃。一路上,他们狼狈至极,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把基层生活。皇帝、太后逃命,按理说朝中大臣也得跟着去,可是,军机处的八位大臣,居然有七个都没能与皇帝、太后共甘苦。只有71岁高龄的王文韶不畏艰辛,拖着自己衰老的身体,坚定地跟在皇帝和太后身边。此事之后,慈禧太后对王文韶更加信任。而且王文韶出身正途(咸丰进士),久经考验(历任道、司、抚、督及北洋大臣),谙练政事(历官户、兵、礼三部),政治过硬(戊戌政变后取代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再加上这分患难君臣的交情,王文韶的发言,对朝野上下来说,实在是极具分量。
有王文韶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反对继续改革科举制度,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提议肯定不会被通过。此外,军机处其他成员对于科举改革也不热心。比如庆亲王奕劻,此人眼里只有“油水”,只要能看见油水,他什么都敢做;看不到油水,神仙也难请动他。改革科举并不是一件有油水的事,所以,庆亲王对此事不会有什么热情。其他军机大臣虽然赞同科举改革,但是,他们的地位不及王文韶和奕劻,所以起不了决定作用。
总结起来,想要推动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关键点就是王文韶,搞定他,科举改革一事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王文韶已经放出话来,只要他还在位一天,他就不会同意继续改革科举。张之洞等人不能硬来,只好侧面迂回、缓慢推进。
在慈禧太后1901年的“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办学堂。为此,朝廷让当时的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拟定了一个学堂章程,但是,这个学堂章程有很多问题,难以实施,只好暂时搁置。1903年3月,张之洞要求加大科举改革力度的提议被王文韶否决,于是,张之洞转而参与到制定新的学堂章程一事中,并且希望能够通过制定新的学堂章程来间接地推进科举考试改革。1903年6月,张之洞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了学堂章程。新的学堂章程解决了旧学堂章程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于是,在1904年1月,新的学堂章程公布,即《奏定学堂章程》。这一年是旧历癸卯年,所以又称“癸卯学制”。
学堂章程的成功让张之洞信心倍增,他觉得有必要再次提出科举改革了。1904年初,张之洞又一次上书朝廷,要求将科举取士的名额减少,并分配各学堂。张之洞建议,从1906年起,将科举考试录取名额减少三分之一,并依次递减,每三年减少三分之一,这样的话十年后就可以完全停止科举考试了。
这一次,朝廷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复。一方面,朝廷同意了张之洞的提议,另一方面却又说要等到各级学堂都办齐了、证明确实可用了,再考虑停止科举。这样的回复简直就是一张空头支票,甚至是自相矛盾。科举的存在严重影响学堂的发展,而朝廷却要求学堂有了发展再废除科举。如果学堂能够在科举存在的情况下顺利发展,那还有废除科举的必要吗?主次不分、因果颠倒,这样的回复根本就是在敷衍张之洞。所以,张之洞推进科举改革的努力又一次白费了。
就在张之洞为科举改革一事难有进展而苦恼时,中国的东北发生了一件大事。1904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爆发了一场恶战。交战双方为日本和俄国,但是战场却是在中国的东北。战争让当地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当地的民房、工厂被炸毁,就连寺庙也未能幸免。耕牛被抢走,粮食被抢光,流离失所的难民有几十万人。日、俄都强拉中国老百姓为他们运送弹药,服劳役,许多人冤死在两国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更有成批的中国平民被日俄双方当作“间谍”,惨遭杀害。这场战争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使中国东北民众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人身伤亡。此时的清政府既不敢得罪日本和俄国,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民,只能宣布“中立”,任由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妄为。第二年5月,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
这一仗中国损失惨重,也使得清政府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形势的紧迫,国内政局也因为这一仗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对立宪的态度。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独裁的俄国,这让清朝统治者不得不考虑立宪的问题,还有就是科举改革一事。此时,在这件事上已经沉寂了一年多的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旧事重提,他们以日俄战争为契机,再次呼吁推进科举改革,而且他们对科举改革的态度更加坚定,要求朝廷立即废除科举,不再要求朝廷逐年递减。
张之洞等人借着日俄战争重提科举改革,为了说服慈禧太后,他们简直就是“连哄带骗”外加“恐吓”。一方面,他们强调科举阻碍国家选拔人才,而要想培养人才,只能通过学堂;另一方面,他们结合日本战胜俄国的事实,总结出日本的强大与学堂的发展密不可分,进而告诉慈禧太后,中国如果再不重视学堂的发展,必然要继续受洋人的欺辱。
八国联军早就把慈禧太后打怕了,她已经不敢轻视洋人了,从西安回到北京的她还主动和洋人搞好关系,经常在颐和园里招待那些洋人。张之洞等人搬出洋人来“吓唬”她,让她改革科举制度,她已经不敢多想了。很快,朝廷决定废除科举制度的圣旨便昭告天下了,从1906年起,各个级别的科举考试全部废除。而在此之前,曾经坚决抵制科举改革的王文韶则被免去了军机处的职务,这就为废除科举铺平了道路。
科举制度虽然废除了,但是,大清国还是在1911年时走向了灭亡。张之洞试图通过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来挽救大清国,结果却在无意间给大清朝以沉重的打击。科举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封建势力控制人民思想的武器。在科举的束缚下,读书人失去了判断的能力,变得麻木不仁,只知道一味地服从。科举制度废除以后,读书人的视野得到了拓展,思想也随之开放,对腐朽的封建王朝也更为不满,推翻清政府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
张之洞想要拯救国家,但是,他始终不愿意面对让国家陷入困境的根本问题——封建专制。不解决封建专制问题,中国的富强就毫无可能。可是,出身于封建官僚体系的张之洞,又怎么可能自己把自己给否定了呢?所以,只要张之洞不触及封建专制,他的一系列所谓“改革”,包括废除科举在内,就不可能实现他富国强兵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