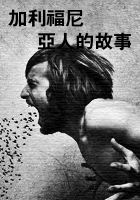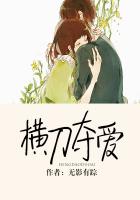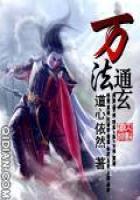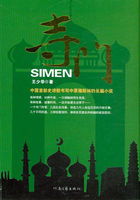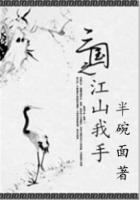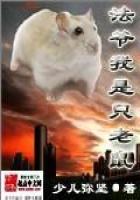十年前,我和谢泳、高增德、智效民、赵诚在太原几度雅集,以沙龙的形式产生了一本名为《思想操练》的谈话录,二〇〇四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厚爱。其中最年长的是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他读到这本书,先后邀我和赵诚、智效民到后拐棒胡同家中叙谈,由此而成为忘年交,让我们受益匪浅。还有《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等先生,邀我和谢泳到《冰点》周刊的平台上,继续进行了长达五年时间的对话。因这本书而结识的各行各业的朋友就更多了。近日,又有青年朋友问起这本书。我们参与对话的五个人,生活轨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难再聚到一起了。
谢泳离开《黄河》杂志,到厦门大学教书。他原毕业于晋中师范专科学校,厦门大学根据他的学术水平和成就,聘请他出任教授,成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美谈。其实,谢泳在七〇年代末参加高考,当时全国大专生的人数比现今的研究生还要少。他在八〇年代已经是全国知名的评论家,只是原单位没有按照他的资历和成果晋升高级职称,让他在编辑一职上徘徊了二十年。他远赴厦门,获得应有的社会承认,也是出于不得已,并非刻意制造新闻。
高增德已年逾八旬。他因眼睛有疾,不能使用电脑,被拦在了互联网的门外。因接受外界信息受限,关注当今的思想文化动向力不从心。他后半生孜孜以求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工程,汇集的文稿逾千万字,和一家出版社订了合同,交稿以后再无下文,实际上是永远地搁浅了。一年多以前,湖南朋友向继东打来电话,和我探讨当年与高增德合编的《世纪学人自述》可否再版。这套由二百位现代学者自传形成的六卷本丛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后,学界虽然评价不错,但市场效果平平。出版社是企业,策划选题,当然不能忽视发行。我说,可以形成另一个选题,叫《当代学人自述》。寻找最具公共影响力的当代学者,集中他们回忆人生经历和求学甘苦的文字,汇编成书,可以得到较多的读者。目前这套书已经出了两辑,第一辑为《望尽天涯路》,第二辑为《灯火阑珊处》。
智效民已经在七年前退休。他唯一的儿子到北京传媒领域发展,他和夫人也来到北京居住,渐渐融入京城文化界的一些圈子。随着当今高校体制性弊端进一步突显,他对民国大学校长和民国教育家的研究越发耀眼。他对晋绥土改的研究,也引起人们的关注。
赵诚一直在山西省委党校教书,不久前也退休了。其间经历了妻子不幸去世等人生坎坷,但他关注公共事务的热心一直未减,他撰写的黄万里传记《长河孤旅》,则一版再版。
我们这个小小的沙龙,因共同的趣味而相聚,由共同的追求而切磋。本来想争取组成一个成型的研究机构,继续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但终未如愿。二〇一二年,我和智效民等朋友一起到欧洲旅游,走进佛罗伦萨,产生了很多的联想。佛罗伦萨作为一个城邦,面积不大,人口不到十万,在文艺复兴时代却涌现了但丁、薄伽丘、彼德拉克、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伽利略、马基亚维利等一大批照耀人类文明进程的巨人。这种奇观的产生,固然有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复杂原因,离不开美第奇家族的庇护、赏识和资助,但也要看到,他们之间,有的是师生关系,有的是朋友关系。可见文化人互相之间启发、帮助、切磋、激励之重要。我们当然不能和这些文化巨人相比。但想通过某种方式,形成一个类似学派的群体,还是未能如愿。
后来我看到华东师大教授张济顺,趁自己担任大学党委书记之职期间,陆续请来沈志华、李丹慧、杨奎松、韩钢等一批史学翘楚,组建冷战史研究中心和当代史研究中心,还有意请高华加盟而未果。现在,华东师大在当代史研究方面已经蔚为大观,成果迭出,居于学术领先地位。可见同样的大环境之中,还是有可能营造小环境,事在人为。
《思想操练》在二〇〇四年初问世以后,得到不少学界人士中肯的批评。其中伦理学家萧雪慧的批评最见功力。她在肯定本书优点的同时,指出了两点不足。一是考察的对象偏重文史,对社会科学和哲学关注不够。二是考查了“文革”中的民间思想,就说到了九十年代,而跳过了重要的八十年代。她这两点批评完全正确。前一点,说出了我们知识结构上的局限。后一点,说出了我们经历上的局限。都可谓一语中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八十年代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有人说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我觉得八十年代是整个民族猛省,挣脱迷信与僵化,重新拥抱人类文明的时代。一代人唤醒了梦想,启动了独立思考,整个国家重新找回了健康向上的力量。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些正能量,阻止着民族精神的下墜,某种程度上还是得益于八十年代的惯性。虽然八十年代的新锐已经步入老境,向上的力量已经日趋衰竭。我们不是不懂八十年代的重要意义,但我们评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又确实力有不逮。因为当时我们都在山西,对北京隔山相望,不掌握其中一些深层次的脉动。后来,查建英推出了《八十年代》,柳红推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还有不少当事人撰写了回忆文章,那个年代许多激动人心的细节才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