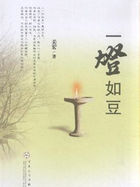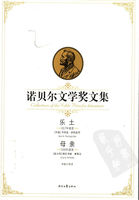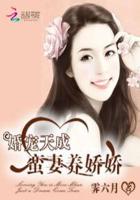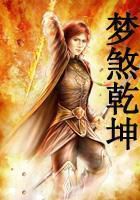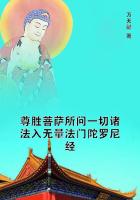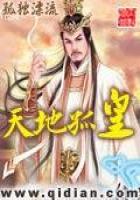33年后,这里迎接她的何止是鲜花,更多的是北大荒人的热情和20年发生的巨大变化。人生易老天难老啊!在与老连长默默地拥抱中,张抗抗流泪了,泪水中浮起了她脑海中多少的往事啊!
在北大荒的八年,张抗抗曾扛锄头种过菜,压过瓦,上山伐过木,搞过科研,当过通讯员,也有过恋爱……引起了她极大兴趣的是伐木工人的号子。她曾搭车走了好长的山路去听伐木工人的喊号。那悠扬、豪放、充满活力的声音,在大山深处、在她的作品里,也在她的心头回荡。
如火如荼的北大荒生活感染了她,促使她拿起笔。在一张小炕桌上,她铺上鲁迅先生的画像,再蒙上一层塑料布,四周钉好,就修饰成了一张不错的新桌子。“我每天在上面作笔记,好像鲁迅先生在看着我。这张桌子居然一直用到我离开农场。”
有一次下大雨,宿舍漏得稀里哗啦,张抗抗用一块大塑料布撑起了一个“临时屋顶”,坐在那块塑料布下继续读书。结果雨水又从“屋顶”上漏下来,钻进鲁迅先生的头发里,叫她心疼了好久。
张抗抗从那时起一写就是30年。从她1972年在《解放日报》发表处女作《灯》至今,已有五十多部作品问世。也是在这个小炕桌上,她写就了长篇小说《分界线》的提纲。她说:“从我第一次往外投稿到我去上海修改长篇,到后来上学,所有的成就确实同黑土地的养育分不开。对苦难、对人生的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使我写作的这条河越来越广。”她又说:“我的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意味着对我下步创作的挑战,你不能重复自己,应该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发展每一部作品。你呈现给读者的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是新的。作家是内容,不是皮儿。作家创作的内容大都是在自然状态下得到的。一个好的作家就在于能够用一种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把蕴藏在生活中的‘核’提炼出来——一部文学作品就像一个果子,丰满的果肉和甜美的汁液固然可爱,但藏在其中的果核才是最有生命的东西。”
在张抗抗眼里,北大荒给她的印象最深的,是那长长的地垄沟,总是望不到尽头。面对那长垄,她恐惧过、厌烦过,而今再回到这里,望到那镶嵌在浓绿玉米地间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金黄色麦田,她激动了,她兴奋了:多像一幅巨大的油画啊!她忍不住弯下腰去亲吻麦穗,去咀嚼那成熟麦子的新鲜味!好像在寻找一种当年的感觉。
经过几十年风雨的摔打,张抗抗自豪地说:“我很幸运,每一次都是我主动选择生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1979年,我从编剧班毕业,再次面临回杭州还是留下当专业作家的选择时,我没有犹豫,再次选择了文学,选择了黑土地。”
张抗抗从80年代初期成为专业作家开始,她的小说创作进入了高峰,她先后创作的《夏》、《淡淡的晨雾》等小说都获得了全国文学奖。但她创作的第一部反映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情爱画廊》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她说:“我觉得中国文化缺乏对爱神和美神的崇拜,‘文革’中制造了一个政治上的神,然后到90年代开始崇拜起财神来,所以我觉得应该创作一部比较美的爱情小说,来告诉人们,爱情是一个人追求的高尚的情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我完全是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去写,结果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就是这种争论,使我觉得我写对了。”前些天,张抗抗又把一部长篇新作《作女》呈现在读者面前。她说:“这是我继《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之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我把我的‘作欲’都通过文学表现出来了。”这是张抗抗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张抗抗认为,好看的小说也并非就是商业小说,“人们总是认为,好看、好卖的东西就是商业性的,其实很多经典名著读起来也很美。追求文字的精美、表达方式的大众化,绝不同于商业作品的低俗和功利。”
“你回来干啥?”张抗抗好久没回北大荒了,这次突然回来,很多人都问她。她回答说:“我不干啥,就想看看朋友,看看这儿的人现在怎么生活。”
二十多年了,本来很熟悉的第二故乡,她突然觉得有些陌生。一个“看”字,拉近了她和北大荒人的距离,体现了这位江南才女的柔情与率真。
在北大荒活动期间,张抗抗应《农垦日报》之约,到报社为编采人员讲了一堂“生活与创作”的课。张抗抗来到报社,看到当年的《兵团战士报》已变成对开四版、彩色印刷的《农垦日报》时,心情格外高兴,她向大家回忆了当年给报社当通讯员的经历。还为《农垦日报》写下了“《农垦日报》是哺育北大荒作家的摇篮”的题词。
张抗抗说:“我已经整整20年没有回北大荒了,但我没有忘了当年农场职工群众对知青生活的关心和爱护。更忘不了农场的工作与生活。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是我创作的一部分,但简单地说我是知青作家又是不准确的。因为后来我创作的反映其他方面的作品则是大量的。”
张抗抗成了名人了,可她还深深眷恋着北大荒。199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长篇回忆录《大荒冰河》,详细记录了她在北大荒八年的经历与感受,她在北大荒的苦乐与得失。
在宝泉岭分局逗留期间,张抗抗还为第二故乡的近百名文学爱好者讲了文学创作课,有些远在百里外的青年,也都早早搭车来听课。最后,张抗抗还回到了当年生活工作过的新华农场,看望了仍在那里工作生活的老职工们。
怀念傅道春老师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那天,一个同学从九三局打来电话说傅道春老师走了,这怎么可能呢?
年前,我在省里参加一个会议,听哈师大的一个朋友说:“傅道春老师在杭州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从那以后,我虽然未能和他通上话,可一直惦记着他,关心着他的病情,没想到再次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时,传来的竟是噩耗。
傅老师真的走了,走得是那么地突然,走得是那么地令人伤心。每当我想起他对我的帮助,我的心就难以平静。几十年前的校园生活,历历在目。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刚上初中时,傅道春老师参加工作不久,刚从九三局砖厂调到中学,担任我们初一·二班的班主任,还给我们讲语文课。我那时候就愿意学语文,语文成绩自然就好一些,傅老师也喜欢我。
我愿意听傅老师讲课,不光因为他讲的是我喜欢学的语文,更重要的是他讲课时教法新,同学们可以畅所欲言。课余时间,我也愿意去他家里求教。记得他家当时住在老“十一户”,有时候他很忙,可我去了他都认真地对待我,认真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几乎是有问必答,他的知识是那么渊博。从那时起,傅老师是我心里最佩服的人之一。
后来,傅老师被九三中学选送到齐齐哈尔师范学院进修去了,我们刚一换老师时还很不适应,一直想等他回来还能教我们。1974年,傅老师毕业回来时,我们已经高中毕业了。他先后担任九三分局一中教导主任、九三分局一小校长、九三分局教师进修校副校长、九三分局一中校长。1986年他被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6月,调到黑龙江农垦师范专科学校任副校长。调入师专后,他从当教师、用教师的职业的岗位,变为培养教师。使他能够从里到外,从微观细节到宏观背景,对教师问题进行探究与思考,深感许多现行的教师行为需要理论上的说明和解释,乃至矫正和完善。他在从事高师教育学的教学中,涉猎了一些行为科学知识,寻找了一些开掘这一领域的工具,终于在教师与行为科学的结合上找到了问题研究的切入点。
参加工作不久,我一直坚持自学中文,不满足于当工人,非常想到局宣传部从事我热爱的工作。一天我到他家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后,傅老师略沉思一会儿便婉转地跟我说:“社会是不埋没人才的,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你目前重要的不是找单位,而是抓紧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从那时起,我牢记老师的教诲,默默地学习,1979年9月,我就从修造厂被选拔到九三分局的公交党委办公室。
1991年我从九三分局调到总局工作后,在佳木斯市我们多次见面。记得1994年5月29日,我在总局办公楼里见到傅老师,他送给我两本他的教育学研究专著。一本是《教师的组织行为》,一本是《教师的教育行为》。1991年,他的“教师行为研究”的理论成果,应用于高师培训上,被列为省“七五”期间教育科研重点课题,次年得到世界银行贷款的支持。我真为他取得这样的成绩而感到骄傲,他三十多年的汗水没有白洒。
从傅老师身上,我不仅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如何做人。他出身工人家庭,全凭自己的刻苦努力,取得了令人折服的成绩,后来成了博士生导师。就在他事业上飞黄腾达的时候,工人出身的妻子一直陪伴着他,这与当今许多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没有因为取得了成绩就固步自封。如果说我到今天能在创作上取得点儿成绩的话,是与傅道春老师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1997年3月2日,我和总局机关在哈尔滨参加公务员培训的几位同事,来到了傅老师担任副校长的阿城师专。傅老师见我们来了很高兴,看到我后也很亲切。我单独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嘱咐我要抓住北大荒这块富饶的宝藏不放,多研究研究北大荒文化。给我出了许多题目,还把石方先生著的《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移民概要》等送给他的书给我选了几本。后来,又把他新编著的《教师行为访谈》、《中国杰出教师行为访谈录》、《情境教育学》等签上他的大名后送给我,这几本书我一直保存着,我将永远保存下去。他的研究成果,分别荣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优秀成果二等奖、黑龙江省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我曾经为我有这么个好老师、有取得这么大成就的老师而骄傲,九三分局也为他的成就而自豪。
记得我们见的最后一面,大约是1998年春天。一天晚上,他从家中打来电话,说明天一早就到总局(所在地佳木斯市)来取档案,因为浙江师范大学要调他,他怕熟悉他的人宴请他耽误工夫,嘱咐我千万不能跟别人说他到了总局。第二天,他给我打来电话,我匆匆忙忙赶到他住的站前招待所,我给他点了两个炒菜,可他坚决不同意,只要了一个炒榨菜,匆匆忙忙地吃了一碗面条。但他没有忘了鼓励我,没有忘了给我的写作出题目。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没想到那次分手,竟成永别。
去年六月,我和妻子去南方休假,在杭州待了一天,那一天总是阴雨连绵,就连游西湖也是顶着雨。我突然想起了傅老师,我就一连打了几个电话,询问他的电话号码,都没有找到。据说,那时候他的病已经查出来了。
2002年12月8日,52岁的傅道春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他在远离北大荒的南国,悄悄地走了。一切都没来得及告别,一切都没来得及安排。我和我的同学们,只好在布满星辰的夜晚,向着南方的星空,遥寄对他的哀思。
“生正逢时以至此”——悼念吴祖光先生
看到新华社发的《著名剧作家吴祖光逝世》的消息后,我既感到惊异,又深感悲痛,不由得回想起当年吴先生回访北大荒时的情景:
那是1994年8月的一天,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接待并全程陪同回访北大荒的文化名人吴祖光和丁聪。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领导们去佳木斯火车站,把他们接到了农垦大厦。
当天下午,总局有关领导就陪同他们参观了农垦科学院、肉联厂和三江食品公司,所到之处都准备好了笔墨,请他们给留下墨宝。吴老给三江食品公司题写的是“弘扬硕亚文化,生产大豆精品”。
北大荒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都看在眼里,因为他们与北大荒是有着深厚感情的。1958年3月,吴祖光和国务院各直属部、委、局的六百多名“右派”乘“专列”来到了北大荒。在这里,他劳动了三年。这次来到北大荒,吴祖光来到了当年劳动过的“右派队”——八五三农场二分场六队,见到了阔别34年的队长李富春。这个当年从杭州转业来的上尉参谋长,见了吴祖光分外亲热。吴祖光双手紧紧握住李富春的手说:“你还认识我这个战士吗?”“认识!认识啊!”李富春激动地说:“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当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来建设北大荒的,没啥区别,王震部长开会时还称你们同志呢。”
其实本来就该称同志,更是难得的人才。吴祖光原籍江苏常州,1917年生于北京。他做过南京国立戏剧学院的教员,主编过上海《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和《清明》杂志。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电影导演工作,先后拍摄了戏剧艺术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荒山泪》等。20世纪60年代转向戏曲创作,他一生创作了四十多部剧本和大量散文、杂文。20岁时创作了全国第一部反映抗日的戏剧作品《凤凰城》并轰动一时,被周恩来称为神童剧作家。
三年的北大荒特殊生活,为吴祖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北大荒他除了帮助话剧《北大荒人》修改剧本外,还与人共同创作过大型话剧《卫星城》、《光明曲》,还为牡丹江农垦文工团写了京剧剧本《夜闯完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