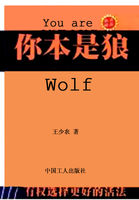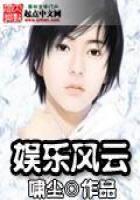“这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和合先生说,“他那寨子,去年在日本人来时,被占了……我这次听人说,他那后娶的女人,也被日本人那个,那个糟蹋了,他和后头女人生的崽,才几岁,被日本人扔进火里……唉,他去年也遭了大劫呵!幸亏他的谷子藏得好,没被日本人搜出来。听说我们要打日本鬼,所以……这是司令的宣传搞得好,传到了他那里……”
和合先生一边轻声地说,一边盯着屈八,看屈八的反应。
此时的屈八,仿佛愣了。半晌,才说了一句:
“那个‘寨主’,他不会自己来吧?他不知道我吧……”
和合先生说那就不清楚了。
屈八又愣了半晌,对和合先生说:
“如果他来了,由你处理。不要带他来见我,也不要告诉白曼。”
屈八说完,又嘀咕一句,不就是送几石谷子来嘛,那几石谷子,只怕也尽是瘪壳壳。
和合先生本是想趁着这机会,劝说屈八——许老巴——白曼——许伶俐和许家寨“寨主”“和合”,因为他这一辈子做的就是“和合”之事。可见屈八如此,他把那劝说之词又咽了回去。应道,好,好,我照司令的意思办。
和合先生认为,只要屈八收了他父亲的粮,这事,就大有回旋的余地,只是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慢慢“和合”。
屈八也许还是想见他父亲的,也许真的横了心绝不愿见。总之无人能揣测到他的内心。他听和合先生答应了照他的意思办后,便再没就他父亲送粮的事说什么,而是喊江碧波跟他到“司令部”去谈宣传工作。屈八说郑南山已在“司令部”等着,正好到一起好好总结总结这次的宣传经验。
“好呢!总结经验去呵!”江碧波甩动着学生头,跟在屈八后面,往“司令部”走去。她尽管想让自己显得老成、老成,但还是止不住脚步一跳一跳。
江碧波的这一跳一跳,若是在平时,我叔爷至少都会说一句,看那女子,跳大神呢!不过跳得有趣。可此时,他全顾不得什么有趣的女子,而是立即对和合先生说,你怎么不帮着我催屈八立即去盘湾岔,反而讲什么他爷老子要送粮?这个时候提到他爷老子,岂不会动摇他的军心?和合先生说他一是得先报告交办的事情,二是想做件好事。
“好事、好事,日本人要是一下来了,什么好事都会完蛋!”
我叔爷本想说你不把军事大事放在首位,你算个什么参谋长?!可虑及乡里乡亲的,和合先生又是德高望重之人,就把那直接不敬的话换了一下。
和合先生一听我叔爷这话,立即从“和合”中醒悟过来,说,那我们两个再去找司令,要他下命令,立即开拔。
和合先生刚一说完,又惊喜地叫起来,好了好了,老舂回来了。
我叔爷那一只眼却没看清,赶紧问,在哪里,在哪里?眼尖的和合先生说,到了禾坪对面,走走走,接他去。
侦察员老舂一回来,并不急着回答我叔爷“日本人到了哪里”的话,而是急着要见司令。
见了屈八司令,老舂说出的仍然不是日本人到了哪里,而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
老舂说他这回带来了一个顶顶重大的情报。
“什么顶顶重大的情报?”屈八催他快讲。
老舂却要先喝一口水,说口干死了,干死了。
屈八就要江碧波快给老舂倒碗水。
我叔爷说,口再干你也先把那顶顶重大的情报讲出来啦!
“先喝水,先喝水。”老舂说。
江碧波舀了一勺子生水,老舂接过杓子,一口气喝个精光。
江碧波舀一勺子生水并不是对老舂不尊。我们老家人,从小到老都是喝生水,就算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是爱喝生水,进得家门,从水缸里舀一勺水就喝,哪怕是寒冬腊月也大多如是。我们老家人说那扶夷江里的水好喝,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更好喝,清甜!若是讲喝生水不卫生,则答曰,喝了几十年哩,点事都没有!当然也有开水煮的茶、泡的茶,但多是用来招待客人。
老舂喝光一勺子生水,撩起衣袖抹抹嘴巴,这才开始说。
老舂说他走到哪里哪里,碰上了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人可不是个寻常之人……
那个非寻常人是怎么跟他搭上腔的呢?老舂讲得详细又详细。讲得屈八也不由地催促,要他只讲主要的、主要的!
老舂说:
“我不把这些详详细细地讲出来,你们不会相信呢!”
屈八说:
“我相信,我们相信,你只要把最主要的讲出来就行。”
老舂这才讲出了最主要的。这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原来老舂碰上了一个大队伍的“收编人”。那个“收编人”说可以拨出多少多少开办费,将屈八司令这支队伍予以收编,叫做收编扩军,收编扩军后并可以供给什么什么……
“他们到底是支什么队伍?”屈八赶紧问。
屈八第一想到的便是王震的“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如果是这支队伍,那就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屈八不可能知道的是,王震的南下队伍没有进入湘西南,已经返回去了。
“他答应给多少开办费?”有人赶紧问。
老舂说那人讲他们的司令有话,凡在百人者,拨开办费法币五万元。百人以上,按整百推算,如两百人则为十万。
“呵呀,我们不正是百来号人吗?”
“快算算,五万法币折合稻谷该有多少?”
和合先生立即算了出来,说约合稻谷一千石。
“一千石稻谷啊,啧啧!”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有人催老舂快讲。
“那人讲,只要一被收编,所有武器、装备、服装、饷粮均由他们司令拨发。”
老舂这话一出,引起一片呵呀。
“呵呀,他们那司令本钱就大啦!”
“呵呀,那只怕就真的是个大救国军啦!”
屈八听着这些“呵呀”,心里很不是个滋味,这不就等于在说本司令无本钱,本救国军微不足道吗?他真想狠狠地训斥一番,什么“本钱本钱”,抗日救国难道还要分本钱大本钱小吗?但他却是冷静地问老舂:
“他就没对我们提什么条件吗?”
“对我们提的条件?”老舂忙说,“提了,提了,四个字,‘就地抗日’。”
“就这么一个条件?就这么四个字?他没跟你讲抗日救国的道道么?”
老舂摇摇头。
“只讲给钱给装备,不讲抗日救国的道道……”屈八在心里断定,这不会是他希望的队伍。既然不是他希望的队伍,他就绝不会同意被收编。但他知道,这么大的“好事”,若自己一口拒绝,说不行,难以平息众人那“啧啧”“呵呀”之声。
“他那队伍的名称你总该打听清楚了吧?”屈八问。
“那名称、名称,好像是叫什么抗日挺进纵队。”
“到底是什么抗日挺进纵队?”屈八追问。
“这个,这个就忘记去问仔细了。”老舂说,“反正是个抗日挺进纵队。这个绝对没错。”
说完,老舂又赶紧补充,说自己当时一听有那么好的条件,就急着要赶回来,所以,所以,主要还是怕被人家先抢了那么好的条件去。这就好比做生意,谁先谈成就归谁做啦!老舂说他虽然没正式做过生意,但这点生意经他还是懂的。“做生意就得抢机会嘛,对不对?”
“什么做生意、做生意?!”
屈八正要呵斥,郑南山说话了。郑南山说:
“屈司令,你多次说我们是要干大事的,这欲成大事,正需有人相助。这机会倒也是个机会。”
暗恋着屈八的江碧波自然已能揣摩出他的一些心思。尽管她已看出屈八对此事由高兴而至迟疑,还是忍不住说:
“屈司令,管他是哪支队伍,只要他给钱给枪,我们就先得了他的钱和枪再说。”
和合先生也是希望接受这收编的,但他不忙于言语,他得等到问他时再说。
果然,屈八开口问他了。屈八说:
“之吾参谋长,你觉得此事如何?”
和合先生说:
“这被收编当然有被收编的好处,这好处老舂已经讲了,就是有钱有枪。只是,还得先弄清他的真实意图再说。”
和合先生的话正合屈八的意思。可有人迸出一句:
“既然他说要我们就地抗日,就总不会是坏事。”
“说得对,不会是坏事,借他人之力,先壮大我们自己,何乐不为?”有人又补上一句。
屈八转而问我叔爷。
我叔爷则是对此无所谓,随他哪支队伍,随他收编不收编,他反正没做什么大事不大事的打算,他只要快点狠狠地打鬼子一顿,为死在衡阳的弟兄们报一下仇,为自己那只被炸瞎的眼睛消消心头之恨。他着急的是屈八总是不提去盘湾岔的事……于是他立即回道:
“他收编也好不收编也好,不关我群满爷的事,我群满爷现在只想着一点,我们若不快去盘湾岔,日本人如果突然出现,你想要他收编也无甚可收了,你要接收他的武器票子,只怕也无人去接了。”
我叔爷这话帮了屈八在收编这个问题上的大忙,他当即说,林满群教官说得对,军情急迫,此事以后再议,现在我命令,立即往盘湾岔出发!先打好这个伏击仗!
我叔爷见屈八爽快地做了决定,松了一口大气,赶忙问老舂,是否打探到日本兵究竟到了哪里?
老舂说:
“我只顾忙着带这顶顶重大的消息回来,日本兵究竟到了哪里,可就没顾得上了。”
我叔爷连声说:“唉,唉,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怎么能糊涂了呢?”
不要责怪侦察员老舂,也不要笑我老家这第一支民众抗日队伍。二〇〇九年七月,当我回到老家,来到当年和日寇激战过的地方,住在一户易姓老人家中,和他讲到“走日本”时,他说日本兵进了村,他家的酸菜坛子、水缸里全被拉满屎;日本兵在宰鸡杀鸭时,根本没有什么防备,他们这些躲在村外山上的人,只要有胆大的端了鸟铳猎枪,就能打他们一个猝不及防……唉,那时的人,真蠢,胆子太小……
与这“真蠢”“胆子太小”相对应,我老家的这支民众抗日队伍,就算得上真正的英雄好汉了。
这易姓村民的家就在新宁崀山风景区隔壁,四面群山环绕,看到的除了山还是山。我去时尚只有一条小路可通,需翻过一道又一道山坳。当时的闭塞更可想而知。而日本兵就连这样的地方都来了,并且通过这样的地方突然出现在守军面前。这个地方,名叫黄沙江,属广西和湖南新宁交界之处。这支日军,就是从全州前来增援围攻新宁的一支队伍。
屈八命令杨六的第一支队,白曼的第二支队向盘湾岔进发后,他带着司令部、直属支队正要出发,急急地赶来了一个人。
那人边走边喊,我要见你们司令,见你们司令,我有话要和他讲。
我叔爷一听,以为是来了送情报的山民,他心里最挂记的仍然是日本人究竟到了哪里?他赶紧对屈八说,司令、司令,来了个要见你的人,只怕是有关鬼子的事。
屈八停下脚步一听,一看,立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那声音,虽然隔了十来年,但他不会忘记,也不会听错;那越来越近的身影,那走路的样式,他照样不会忘记,也不会看错……
屈八愣了一下,旋即说,走!不要管他!
来人却已经到了队伍面前。问,你们的司令是哪个、哪个?我要和他说句话。
有人为他指了指。
屈八想躲避也躲不及了,他父亲,到了他面前。
他父亲一到他面前,眼睛直了、呆了。
当父亲真的站在屈八面前时,屈八反而镇定了。
屈八正要以平静的口气说你来干什么时,他父亲已经叫了起来:
“天啊,你是我的许老巴啊!我的儿啊,我的崽啊,老天有眼,让你回来了啊!”
对着屈八带着哭腔喊叫的父亲,已经是个头发苍白、满脸皱纹、连背也弯了的老人。老人扎着裤腿,因常年劳作,裸露的小腿上暴着一根一根拇指粗的青筋,那拇指粗的青筋随着小腿的颤抖,不时如同泥鳅般蠕动。
我叔爷后来说,屈八父亲,那么样的一个哈宝地主,吃舍不得吃,穿舍不得穿,还当不得我这个卵打精光什么都没有的人,起码我还吃了几餐好的,还吃过美国罐头。
看着父亲的那个样子,屈八心头不能不泛起一股酸楚。这是他的父亲吗?这是那个吝啬得餐餐只准吃霉豆腐、餐餐嚼苞谷粒粒,把粮和钱看得比女儿的命还要重的父亲吗?那时的父亲,虽然吝啬,虽然把钱看得比命还重,但有一副结实的身板,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气,打赤脚走路都踩得三合泥地面发响,脾气一来,手把子一捋,他屈八都不敢上前……可眼前的父亲……
屈八虽然心里泛起一股酸楚,却只冷冷地说出一句:
“我是许老巴,但不是以前的许老巴,我现在是屈八。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不要耽误了我的军机大事。”
他父亲立时以足顿地,说:
“我做了孽,我遭了报应……可我这次是给你送谷子来了,那谷子就在后面,你去打日本鬼,你要好多谷子我给你好多,我只要你帮我狠狠地打那日本鬼,帮我报仇……”
他父亲后来娶的那个女人,也就是屈八没见过面的后妈,被日本鬼蹂躏后,又用刺刀捅死;她那才几岁的小孩,被扔进火里活活烧死……
“惨啊,惨啊!你没有见到那个场面啊!”他父亲老泪纵横。
“什么我没见到那个场面?”屈八说,“你以为只有你遭了劫?这全白沙,全新宁,全中国,有几家没遭劫?你不要再说了,再说就耽误我去打鬼子了。”
他父亲连忙说:
“好,好,我不说了,不耽误你去打鬼子了,我等你打完鬼子回来再说,崽啊,你打完鬼子回来可就不能再走啦,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崽了啊!我毕竟是你爷啊,做爷的以前再有罪过,你这个崽也要回来啊!……”
屈八要和合先生处理一下送来的粮食,处理完后立即赶来。
看着屈八带领队伍走了,这位父亲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絮絮叨叨,我的崽回来了,我的崽回来了,八字先生说过,我的崽,我的许老巴,三十岁后要走大运的,他这还不到三十岁啦,他就当司令带兵了……带兵好,带兵好,带兵就不怕鬼子了……
念着念着,他双脚忽地打跪,栽倒在地上。倒在地上他还在念,我的崽回来了,回来了,我又有崽了……
等他爬起来时,屈八,已经走远了。屈八队伍,也看不见了。
这位父亲没想到的是,他的儿子这一走,是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