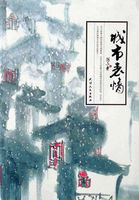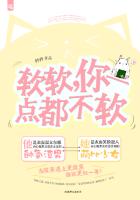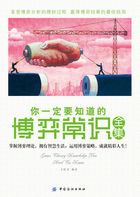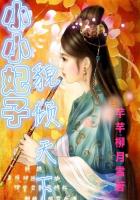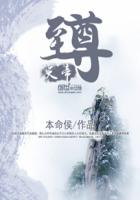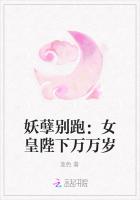关于雪峰山会战的紧急会议正在重庆最高统帅部进行。
紧急会议由蒋介石亲自召集,与会的有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第十集团军司令王敬久,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李玉堂等人。
与会将领在必须确保芷江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因为芷江是中美空军最重要的前进基地、训练基地,对日军占领区及其本土进行空袭的飞机多由此起降,由湘黔、湘桂及湘西前线调集的作战物资大多在此集散。若芷江失守,不但会导致盟军对日轰炸受极大影响,更要紧的是,将会动摇西南半壁河山,重庆将受到直接威胁。故必须确保芷江万无一失。
何应钦认为芷江保卫战必胜。他这个陆军总司令是在民国三十三年冬就任的,几乎和冈村宁次就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即所谓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时间差不多。是年秋,美军已逐渐把欧洲的兵力转用于太平洋战场,制定了“阿尔法计划”,即以中国为主的对日作战计划。国民政府为遏制日军西犯,配合“阿尔法计划”,在昆明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全部国军,特别是对西南战区诸部队加强统一指挥及整顿,并装备三十六个美械步兵师准备反攻。
作为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之所以认为芷江保卫战必胜,一方面是国际形势已日趋明朗,盟军的胜利指日可待;一方面是日军虽然看起来仍然不可一世,但在中国战场的战线拉长了两千余公里,实为强弩之末;而在中国军方面,得到的美式装备越来越多……更主要的是,芷江会战,尽占地利,湘西崇山环绕,易守难攻。特别是绵亘数百公里的雪峰山脉,是一道天然屏障。他判断日军根本不可能打到芷江,故应在雪峰山脉一带伺机寻求和日军决战,将进犯之敌歼灭。
出生于贵州兴义、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何应钦,十九岁加入同盟会,二十一岁参加辛亥革命,旋在黔军任过营长、团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还担任过云南讲武堂教务长、广州孙中山元帅府参谋、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兼教导一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参加过平定商团叛乱、刘杨叛乱和两次东征陈炯明,率第一军参加北伐……
何应钦是《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者,这两个协定都是与日本签订的,都是出卖国家主权的协定;他又是在“西安事变”中主张“武力讨伐”张、杨,以破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魁,我当年从中学历史教科书和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得到的对他的认识大抵就是这两点,等同于他在抗战期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至于他是芷江会战即湘西会战、雪峰山会战以完胜而告终的总指挥,并于三个月后亲手接过冈村宁次所呈递的投降书,则是从湖南芷江县志办公室和抗战文化研究所合编的《抗战胜利受降——芷江纪事》,及《湖南文史——湘西会战专辑》等资料书中得知的。由是也才明白屈八、杨六、老舂、我叔爷、和合先生他们在新宁第二次“走日本”时,参加打日本兵的战斗就是雪峰山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资料上记载得清清楚楚,会战的南部战场主要包括新宁、城步、绥宁、武冈西部地区。新宁是南部战场最先打响之地。
何应钦判断日军根本不可能打到芷江,满有把握地提出应在雪峰山脉一带伺机寻求和日军决战,将进犯之敌歼灭的作战之策,似乎应该和他生于、长于贵州偏僻山区的兴义,并在黔军任过低、中、高级军官有关,他应该是熟知山地作战的一位将军。而雪峰山会战的大捷,不能不说是他最辉煌的一笔。似乎颇有意思的是,作为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的冈村宁次,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紧急召开会议,策定夺取芷江机场作战目标;作为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则策定应对战略。这两个几乎同时上任的将军,以雪峰山会战见高低,最后是冈村宁次大败,何应钦全胜。紧接着是冈村宁次将投降书呈递到何应钦手里。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的军事紧急会议持续到午夜,最后,蒋介石下令,芷江保卫战由何应钦全面负责,集结二十多个师约二十万兵力迎击日军。
蒋介石以白开水代酒,提议“为确保芷江而共勉干杯!”
中国军队总的作战方略是:利用雪峰山这道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构筑纵深防御工事,采取攻势防御战略,施行“逐次抗击、诱敌深入、分割包围、聚而歼之”的战术,歼敌于雪峰山东麓。
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为: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总指挥,令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担负正面防御作战;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担负桂穗路防务;以第九十军为战役机动兵团,控制于靖县、绥宁一线,以策应第四方面军右翼作战;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接替湘北防务,原防守湘北之第十八军调沅陵、辰溪集结,作为第四方面军的机动兵团;新六军廖耀湘部为总预备队。空军则以芷江机场为基地,有第五、第二、第三等四个大队的各一部,另有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参战各型飞机四百余架。
中国会战的兵力不但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已经握有绝对的空中优势。
提到空中优势,不能不提到陈纳德将军。陈纳德与芷江又有不解之缘。
早在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八月,陈纳德就“接受”宋美龄之“命令”,赴芷江筹建航空学校。
陈纳德是于一九三六年收到蒋介石及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宋美龄的邀请信,请他来中国视察空军,而于一九三七年初春乘船自美国经东京来到中国的。他原计划只到中国视察三个月便返回美国,但抵达日本横滨后,看到日本如一架战争机器一样在急速运转,明白日本将对中国展开全面战争,中日之战,绝非如美国国内的舆论能以调停和解,而是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便急忙赶到上海,会见了宋美龄。宋美龄任命他为中国空军上校。他旋到杭州笕桥、汉口等空军单位视察,视察得出的结果是:中国空军必须大力加强。很快,卢沟桥事变发生,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空军根本无力拦截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他又亲眼目睹了毫无防卫的民房、学校、医院遭日机轰炸的惨景,决心为中国抗战尽力。故当宋美龄请他去芷江筹建航空学校,他立即赶赴芷江。
芷江之称,源于屈原《湘夫人》的“沅有芷兮澧有兰”。这座位于云贵高原东部湘西雪峰山区的小城,依明山,傍潕水,虽偏僻,但秀丽。《方舆胜览》载:“潕水两岸多生杜蘅白芷,故曰芷江。”早在公元前二〇二年、汉高祖五年时即置县,唐、宋、元、明,及清前期为州、府所在地,清乾隆元年设置芷江县。从战略地位来说,是“控荆湘、扼滇贵、拊蜀而复粤”的“势据西南第一州”,又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蒋介石电令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将洪江飞机场改建于芷江;华北事变后,为备战而扩建;抗战全面爆发后,再度扩建。在陈纳德到达芷江两个月后扩修完工并正式启用。启用的当月,苏联志愿空军大队一中队长伊凡洛夫斯基率领二十架飞机进驻,并于十一月八日下午率六架战机起飞拦截空袭芷江的日军十八架93式轰炸机,击落日机三架,击毙九名日军飞行员。次年春,苏联自身吃紧,驻芷江的志愿空军奉调回国。
芷江航校建立后,却仅有三架训练机,且在训练中摔坏两架,陈纳德不得不于当年十一月将航校迁往昆明。
由芷江航校仅有的三架训练机可看出当时中国空军的薄弱,中国在一九三六年才成立航空委员会,可供作战飞机仅九十一架。故而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只能任凭日军飞机肆虐,遭受狂轰滥炸。仅芷江就遭日机轰炸三十八次,来犯日机五百一十三架次。在这块小小的偏僻山区的土地上,就落下了日机投下的炸弹四千七百三十一枚。被炸死炸伤八百三十八人,炸毁房屋三千七百五十六栋。
一九四〇年五月底,陈纳德回到美国,要求美国政府大力援助中国空军。时美国尚未向日本宣战,其要求搁浅。陈纳德游说于朝野、军界,终得好友葛格伦律师相助,葛格伦系罗斯福总统的亲信,他不但成功地劝说总统批准了陈纳德拟制的“空军外籍兵团计划”,而且予以武器和飞机的协助。陈纳德通过各方筹集经费,招募空勤地勤人员六百名,美国政府提供一百架P-40型驱逐机供志愿队使用。这就是有名的“飞虎队”的诞生。
“飞虎队”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即美国独立日这天被并入美国现役空军编制,编制中的名称为美国第二十三航空大队。陈纳德被召回现役,任命为准将大队长。次年九月初,空军扩编,改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十四航空队,拥有飞机二百多架。同年十一月五日,在桂林组成中美空军混合大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衔司令。
陈纳德将第十四航空队主力、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进驻芷江机场。一九四四年三月,又将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主力派驻芷江机场;混合大队司令部亦随队进驻芷江。陈纳德穿梭于昆明、芷江指挥空战。他将驻芷江空军作战范围划定为“以华中特别是黄河以南,平汉铁路以西地区,南京、上海以东地区”,担负粤汉、湘桂等铁路、公路运输线,长江、湘江、洞庭湖等水路运输线轰炸、封锁任务。并立即调P-40型鲨鱼式驱逐机五十四架,B-25型战鹰式轰炸机二十七架,P-38型高空侦察机两架,以及C-46巨型运输机进入芷江机场。
四月,陈纳德电告蒋介石:“我很荣幸地通知主席先生,美国空军的超级空中堡垒B-29型轰炸机已经进入贵国。”并提出:“有两处前进机场,希望得到中国盟军的保护,一处在衡阳,一处在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