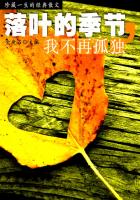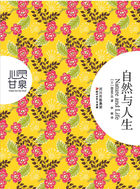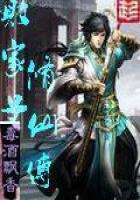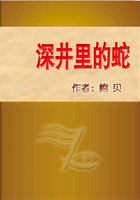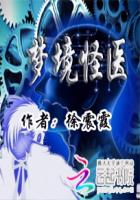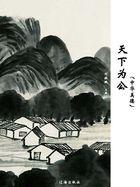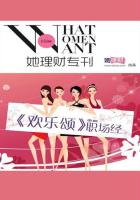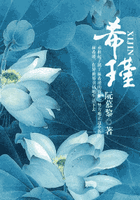在俄罗斯民谣《黑眼睛》的伴奏下,娜斯佳的自由操动作如芭蕾舞演员一样自由舒展。弧度非常漂亮,鱼跃、翻腾,转体,一连串美妙的瞬间诉说着与众不同的风情。“那一刻,我沉醉了。她的技术难度不是最高的,动作也不是最完美的,但给了我们其他选手不能给予的享受。娜斯佳的身姿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体操之美。”中国网友由衷地赞美。
终于,娜斯佳技压各路高手,获得了北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全能冠军。
劣势亦可做优势。修长的双腿并未成为娜斯佳夺冠的障碍,而是使她从一个运动员变成了艺术家。8月16日是属于娜斯佳的一天,也是属于你我的一天:正视自己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加上百折不挠的韧劲,谁说你不会变成生活的艺术家呢?
勇气是优雅地面对压力
——压力,是无可避免的,大到把你压垮,既然如此,何必把自己弄得小人一样、猥琐不堪?优雅一点儿,会等来命运转机和祝福。
飞机掉河里了!
这是2009年1月15日15时许,漫步在美国哈德逊河边的人们发出的惊呼。只见一架洁白的飞机,如一只张开翅膀的大鸟,划过天宇,紧接着,冲向冰冷的水面,激起巨大的水花。
机上一共搭载了155人!那是当天下午15时26分,从拉瓜迪亚机场起飞的1549号航班,起飞后不久就遭遇鸟群,两个引擎失去动力。机毁人亡的悲剧,眼看就要发生!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诞生了:飞机平稳停摆在水面上。第一艘靠近它的救援船发现,机上人员,包括一名9个月婴儿和一个幼儿在内,全部幸存。除一人骨折外,其他人几乎没受什么伤。
真是奇迹!此举,开创了民航史上水面成功迫降、无一人死亡的先河。激动得前任总统布什、新任总统奥巴马都写信祝贺。全球媒体忙着转载这条新闻,称:“买彩票都要买1549,太吉利了。”
1549次航班凭什么躲过灭顶之灾?
机长杰斯利·苏兰伯格,成了人们口中“最大的功臣”。这位有40年飞行经验的机长,曾是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他的一系列应对、决策恰到好处,堪称无懈可击:
遇险后,他立刻从副驾驶手中接管飞机,并报告塔台,得到了“沿哈德逊河向南开,降落在新泽西的泰特波罗机场”的指令。但那样会经过人口密集的居民区,万一坠落,可能酿发更惨重的损失。机长稍一思忖,立刻答复:“不,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会直接降落在哈德逊河。”
这一决定相当于把风险和责任背在肩上。水上迫降,技术难度非常高,要求飞行高度足够低,飞行速度足够慢,否则,会无法承受飞机与水面相撞刹那的巨大作用力。飞机瞬间解体、倾覆的惨剧,历史上不是没发生过。
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苏兰伯格机长,已成竹在胸。他一方面努力使失去动力的飞机在空中保持平稳飞行,一方面冷静地通知乘客:“准备进行空难着陆,”“把身体蜷好。”(Brace for impact )。
当飞机停好、人们乘救生艇离开后,苏兰伯格坚持最后一个离开飞机,在舱内巡视两遍,确认所有乘客都已离开。
他的态度,自始至终保持镇定从容。给妻子打电话,云淡风清:“刚才,发生了一起事故。”乘客比利·卡姆贝尔与其同坐一个救生筏,曾抓住他的手,想表示感谢,几乎落泪,他只是很平静地点点头:“没关系”。
一位营救人员描述了其眼中的苏兰伯格机长:“他坐在渡口的终端里,戴着帽子,品着咖啡,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他看起来无可挑剔,制服笔挺。”
无可挑剔的专业水准和令人心仪的淡定风度,令57岁的苏兰伯格一跃成为网络红人。Facebook 上关于他的留言多达数千条,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引用了海明威的话赞扬他:“勇气是优雅地面对压力,我认为,说切斯利苏兰伯格展示了这种能力是很客观的。”
可是,光靠一个苏兰伯格,1549次航班能成就这次神话么?不,一个英雄打不赢与死神的战斗。奇迹的诞生,要归功于诸多的因素,该次航班是一个完美的组合,一群优雅的人与苏兰伯格一路同行。
机组其他人员,以高度敬业的精神,忙而不乱地组织起逃生工作。首先采取措施将机身的通风孔和洞都堵住,以便使飞机更好地防水。降落后,一名空中小姐耐心地将坐在后面的乘客疏导到前门,顾不得腿上已被剐出一道深深的伤口。
乘客们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呼天抢地。有人在祷告,有人默默地接受现实,坐在紧急出口的乘客,准备打开救生门。整个机舱内安静得像图书馆一样。
安静,不等同于木讷、呆若木鸡。16号座位上的布瑞塔的举动,代表了生死五分钟内乘客们的表现:当机长发出“做好冲撞准备”的信号时,立刻按示范动作,低头弯腰,护住要害部位;飞机“坠入”水中后,也不害怕,心中一个信念:“我们一定能活下去,下一步该怎么做?”
飞机停泊之后,人们没蜂拥着逃生,或闹哄哄地给家人发短信、打电话,而是根据机组人员安排,有秩序地撤离。同时,没忘记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带孩子的妈妈,有人帮忙拿行李。职业是记者的乘客,放下了手中的相机,拨通了紧急救援电话,“没什么比生命更珍贵。”
伴随人们的撤离,河水在飞快地涌入,飞机开始下沉。广为传颂的泰坦尼克风度,此刻仿佛在1549航班上如灵魂附体,男人们齐齐喊道,“让女人和孩子们先下飞机!”……
码头上的无人摄像镜头,记录了从飞机滑落到救援船只到来的全过程。我永远忘记不了那有控制的降落,那白色的浪花,飞机那摊开的双翼以及双翼旁整齐排列的、从容不迫的人群。隆冬中的哈德逊河,寒意逼人,几分钟内就能冻伤肌体,再长时间,就有冻死的可能。但当救生圈和缆绳抛过来时,无人哄抢,无人推攘,无人践踏。有作家评论说,他们的姿态,就像一群绅士淑女在月台等地铁。
我倒觉得,像在中山音乐堂听古筝独奏,中场休息,那疏疏淡淡地走出来,说话或者不说话,饮茶或者不饮茶,含笑或者不含笑的人群。
很难想象,在这短暂的“自救”过程中,这155人中,有一个人失去常态、反应过激,会酿致怎样的恶果。集体性的优雅,源于美国社会多年来特别是“9·11”后,政府、媒体、社会公益机构不遗余力地传播危机应对策略,使之深入人心。乘客集体性的优雅,也源于内心深处的信仰,对他人的信任,对公序良俗的信任,对美德的信任。这种信任,最后会“正作用于”自身。很多天灾,很多人祸,不毁于“初始灾难”而毁于“次生灾难”,不毁于技术、设施而毁于幽微的人性。
2009年初,世界还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之中,1549航班的奇迹,是一丝希望,是上帝恩赐的一次提醒:迎面而来的压力,是无可避免的,大到把你压垮,但“既然如此,何必把自己弄得小人一样、猥琐不堪?优雅一点儿,会等来命运转机和祝福。”
从温丝莱特到剃头匠
——时间永恒,柔软的力量永远不会被折断。
今天,那些热烈讴歌温丝莱特的人也许忘了,在第81届奥斯卡之前,他们如何“淡漠”她。
从前的报刊、网络可以作证:1998年轰轰烈烈的头版,然后慢慢流向边缘。纵使报道也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河水暴涨,凯特母女被困于泰晤士河上的小岛”“新片无脱戏,凯特松了一口气”“影后突然宣布离婚,现男友为英国著名导演”……性感、美艳、花瓶,他们只把这类标签贴在她身上。《泰坦尼克》中的露丝仿佛为她定了性——风情万种的女神。
这样的女子,用浅浅的笔调带过就可以了。不必操心,她们会轻而易举地赢得想要的一切:名声、豪宅、有钱的老公。可剥开时间的茧细细地看,你会发现,这朵英格兰玫瑰走得格外“曲折”、格外“温吞”:
择偶的目光一般般。第一任丈夫是个平庸无奇的导演,但“没办法,我就是被他迷住了”。3年后,这段婚姻不出人意料地以离婚告终。
选片的眼光也“一般”。1999年出演的《圣烟》票房惨淡。描写萨德的《鹅毛笔》,虽然剧本构思奇特,演员表演可圈可点,但因部分情节过于惊世骇俗,许多国家未准公映。
作品数量也不多,以一年一部的慢节奏推出,绝大多数偏艺术路线,和商业大片的轰动不可同日而语。
速食时代,人人担心被遗忘,琢磨着“混个脸熟”。用11年的光阴来做一件事,用常人想象不到的代价爱一个人,将生命视作艺术品,而不是商品批量生产……这是影后凯特·温丝莱特沉寂11年、大美于天下的秘密。
这个颁奖台上终于加冕的女子,让我想起一个老人。从身份、年龄乃至国籍上,都与她不搭界的人。他叫靖奎,是个剃头匠,住在北京后海的老胡同里。这么多年来主要忙活的一件事就是:给别人剃头。北京街头不乏这样的剃头匠,一袭白大褂,布帘子一围就撑起一个摊点,时尚小青年是不会问津的。
靖奎的剃头事业更简单。通常小布帘也不围,老主顾一来电话,蹬上三轮车就出发。理发工具都是有年头的,最起码有三四十年的工龄,有的泛着黑,有的则磨得泛了白,市面上压根儿买不着。老主顾们更是“化石”级,年过八九十的都有。饱经沧桑的脸,在靖奎的手下,重新展现勃勃生机。
这让人有些微的心疼。因为理发师傅靖奎,今年已96岁了,一把剃刀,从民国到今天。96岁的老人为生活而奔波,本身是令人酸楚的,但靖奎过得很快乐。他乐呵呵地走过经年不变的后海、银锭桥,跟别的老人打招呼,夸人家:“呵,才70多啊,年轻着呢!”应邀拍摄电影《剃头匠》,有一个镜头要求角色坐在地上不动,老人就真一声不吭地偎依在墙角,直到被寒风吹得发起高烧……
这是疲于奔命的年轻的我们所久违的姿态,用四个中国字可以概括:静默、安详。
与温斯莱特相比,靖奎的安详别有一番力量。前者静默之后犹有“黄袍加身”,而靖大爷自始至终只是个小人物,主演过电影《剃头匠》,获得过200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特别奖,也没怎么增加他的收入、改变他的生活境况。仍然住平房,喝棒子面粥,吃馒头,接到理发的电话得赶过去。今年二月二,400多位老主顾都已经过世,连收的8个徒弟也早都离开了人世,古老的城墙下、冬日的暖阳里,一个质朴清贫的身影在踽踽独行。
什么成全了她与他?一个天后,一个长寿。是沉静的力量。“蕴伟力而静持,遇强阻而必摧”。喧嚣未必久远,静默往往长生。而西方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萨尔瓦多·达利则用一幅画讲述了相同的主题:时间永恒,柔软的力量永远不会被折断。
高明的骗子戴王冠
——峨冠博带者未必值得尊敬。
阅读本文之前,请先做两道选择题:农村二表哥给你打电话:“三强,最近听说卖鳝鱼能挣钱,你借我3万块钱成不?3年后连本带利还给你,年息10%。”你借不?
西装革履的大学同学找上门来,告诉你:“嗨,老张,最近房价又火了,联手炒房如何?你投20万元,我管保到10月份,让你赚30%。”你入伙不?
二表哥那邀请,我想你眉头也不皱地就拒绝了,凭他?唯一的资产是两间摇摇欲坠的砖混房,生意砸了,总不能拖一卡车鳝鱼来做抵押。大学同学,思忖片刻也回绝了。房地产这玩意儿,变幻莫测,他号称的5年投行经验,是用来忽悠散户的。
那么下面的投资项目,你信吗?会出手吗?
年息只有10%,不许探究“投资内幕”,你只负责掏银子,爱投就投,不投走人。
真有人信,并趋之若鹜。
这是一个阳光慵懒的中午。一位成功的商业人士带着激动的表情,走向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老人衣着华贵而低调,显得品位不俗。“你确定要加入我们的项目?”“是。”“你了解并愿意接受我们的规则吗?”“愿意。”掏钱的主儿诚恳地点头,“我会坚定地持有,并永不追问投资策略。”
这位牛气的老人,即伯纳德·麦道夫,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
麦道夫的个人经历和他麾下的基金公司,数10年来一直是投资界的传奇。他原是纽约皇后区的穷小子,拿着5000美元白手起家,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这5000美元,据说是靠当救生员及帮别人安装地下喷淋系统得来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麦老出现在美国顶级的社交场所时,已是今非昔比了。屋子装饰得富丽堂皇如领事馆;妻子每隔6周去著名的米歇尔美发沙龙把头发染成金色;信用卡刷得很潇洒,光2008年1月份,他们就刷了10万美元,其中有8400美元是在一家酒店花掉的——只住了一晚。
奢华的生活方式,令不少人肃然起敬。更奇妙的是麦道夫创立的基金公司,与其他大大咧咧叫嚷着100%回报的基金公司相比,冷静得像个贵族——只承诺一个月1%的增长点,一年才百分之十几。
但懂得复利计算的人心动了:这增长如能持续几十年。将是不可思议的天价。许多人不管彩旗飘飘,一心跟定老麦。事实证明,他们的忠诚“值”了:十几年来,麦道夫公司每年都会给他们当初承诺的回报。1亿美元,至少能有1000万美元。
一朝钱在手,没人细问麦道夫赢利的法门,只顾在年终岁尾时,心满意足地盘点银行里的对账单。当这个老头儿神神叨叨地鼓吹“我的投资原理叫分裂转换”时,他们就不懂装懂地点头。嗨,何必认真,当心把老头儿惹烦了,被踢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