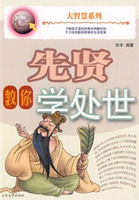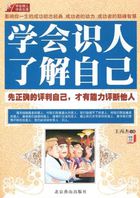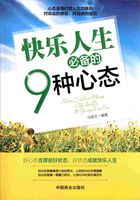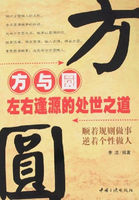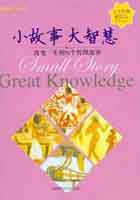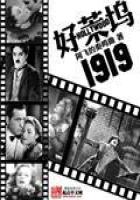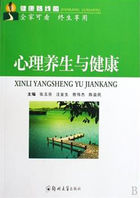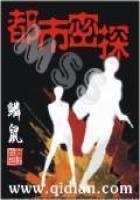战国时期,魏文侯任用武将乐羊攻打中山国,而乐羊的儿子乐舒却是中山国国君姬窟的亲信宠臣,因此大臣纷纷议论,要求撤换乐羊。但魏文侯主意已定,命乐羊领兵征讨。乐羊为争取城中百姓,对中山国包围数月,但围而不攻。于是,猜忌、攻击乐羊的奏疏像雪片似的飞到魏文侯案前,说乐羊是在顾及父子之情,建议临阵易将。而魏文侯却相信乐羊,不仅不撤换乐羊,还派人到前线慰问。终于,乐羊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中山国,百姓们都纷纷投奔归顺。乐羊班师凯旋之日,魏文侯为其举办了庆功会,并赏赐乐羊一个大箱子,嘱其回家再打开箱子。回到家中,乐羊打开箱子,发现里面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非议、诽谤自己的奏折密信。乐羊为魏文侯的信任所感动。期间,如果没有魏文侯的知人善用、用人不疑的举措,任凭乐羊的军事指挥才能怎样卓绝超群,也不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眼下有些企业领导者对手下人,既想利用人家的才能,又对人家放不下心,总认为人家与他离心离德,这是管理者用人之大忌。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前总经理松下幸之助说过:用人的关键在于信赖,如果对同僚处处设防、半信半疑,将会损害事业的发展。他认为,要得心应手地用人,就必须信任到底,委以全权。
用人不疑,是一条重要的用人原则,要真正做到,确实很难,但并非无章可循。
如何对人信而不疑,并且使对方不致“倒戈”呢?那就要靠力量和睿智。对别人信而不疑的人,如果又具备了力量和睿智,被信赖的人就很难兴起“离心”的念头。说得明白些,一个真正能够信赖别人的人,一定也会受到别人诚心诚意的信赖,在官场企业中,领导者就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心。
三国时的孙策,十几岁统帅千军万马,横扫江东,为建立吴国奠定了基础。谈到他的用人艺术,信任二字,不能不是个显著特点。重用昔日的交战敌手太史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太史慈身高七尺七寸,有一身好武功,“长臂善射,弦不虚发”,年方二十,就以智挫州吏而闻名,以后又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孔融,更是声名大振。他的同乡、扬州刺史刘繇,比孙策抢先一步占据江东。他本想借这种关系,追随刘繇干一番事业。可刘繇却不肯重用他,还对别人说,我要是重用太史慈,不是会惹得天下人笑话吗?正在这个时候,孙策率领大军杀到江东,直奔刘繇而来。刘繇派太史慈去孙策那边侦察情况。太史慈一见孙策,便把不得志的满腔郁愤发泄到孙策身上,跳上马挺起戟直奔孙策而来。孙策于交战中虚晃一枪,假装是刺马,顺手抓住了太史慈手中紧握的戟,太史慈也不甘示弱,一把抓下了孙策头戴的帽盔。两个年轻的英雄相搏,真可谓棋逢对手,杀了几个回合,难以决出胜负,各自只好罢兵。这以后,太史慈就跟着刘繇逃到了芜湖。时间不长,在两军交战中被孙策的部队俘虏。人们以为,这次孙策杀太史慈的机会来了。可却出人意料,孙策一见太史慈,好像是故友一般,马上给他松了绑,握着他的手说:“还记得咱俩打仗的那回事吧?假如那次我被你捉住,你又该怎么办呢?”太史慈又气又羞,冰冷冷地回答:“这件事我不好估计。”孙策听后,竟大声笑起来,他说:“今天的事就算没事了,咱们共同干怎么样?”当即下令将太史慈的兵马全部归还,并且拜他为中郎将。
这一战刘繇被孙策杀得惨败,幸存的一万多兵马逃到各地。孙策此时也正需要扩充自己的力量,他果断决定,派太史慈去招纳刘繇原来的部下。对此,身边的许多人都提醒孙策说,这个决定未免太冒风险了,如果太史慈去了不回来怎么办?孙策自信地说:“太史慈绝不是那种人,大家尽管放心。”他亲自为太史慈设宴送行,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太史慈回答:“两个月之内。”对于他的回答,大多数人都半信半疑,只有孙策确信不疑。结果过了五十多天,太史慈果然率着招回来的旧部回到了孙策军中。
孙策得到了太史慈这位战将,曹操也十分生气,他费尽心机想将其拉走,结果未能成功。孙策死后,太史慈又跟孙权征战南北,忠心耿耿,直到临死的时候,还深情满怀地表示:孙策、孙权兄弟俩,对我恩重如山,而我报答得却很不够。表达了他的一片感恩之情。
孙氏兄弟继承父业,年少有为,终于霸踞江东,这与善于用人是分不开的。而信任是孙策及其弟孙权用人成功的秘诀之一。
管理妙在“恩信并施”
李世民用人最见长的地方,是他善于以恩结士,恩信并施。
李世民在打天下的时候,隋末地方割据势力的首领刘武周手下的两位大将尉迟敬德、寻相率众八千来投降。按通常的作法,是把这些降卒分散,使降将不能再帅旧部。但是李世民却反其道而行之,仍命这两人将其旧部,加人大部队中。李世民的爱将屈突通很害怕这两个人叛变,就去劝说李世民削弱这两人的兵权。李世民却说:“过去萧王与人推心置腹,所以人人都能尽忠效命,现在我也这样来委任敬德,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正因为李世民对敬德、寻相的信任,这两个人都成了唐朝的开国元勋,敬德后来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夺取皇位立了汗马功劳。这都是恩信并施这条原则的效果。
平定天下之后,李世民知道官吏中收受贿赂的人不少,觉得应该加以制止。于是大臣萧踽就向他提建议,派人私下里拿上府库的绸绢去送给官吏,看谁收受。果然有一官吏收了两匹绸缎。李世民就非常愤怒,下令把这官吏杀了。民部尚书裴矩向李世民力谏:“做官而受贿,是该死罪。但这位官吏受贿却是陛下派人所为,就是有意陷人于法也,这恐怕不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个原则吧!”李世民听了裴矩的谏诤之后,马上悟到自己的做法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天下之士没有一个信任的,这将导致君臣之间的相互猜忌。于是深为悔悟,并召集文武官员五品以上者,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并说:“裴矩能当官力争,不面从于朕,倘若每事皆然,天下何忧不治。”
后来,李世民的旧臣长孙顺德受人所馈赠的绢,被李世民知道了,就很惋惜地说:“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就会共享府库中的财富,为何贪于收受贿赂呢?”因为这个人过去有功,李世民不想加罪于他,免了他的死罪,并在朝会的时候还赐给这位大臣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就非常不解地说:“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为什么还要再赠给他绢呢?”李世民就说:“如果这个人还有人性的话,那么他得朕赏赐所受到的羞辱就比杀他还令他难受。如果他得了赏赐还不知道要为自己的作为惭愧,那他就如禽兽无二,杀了这样的人又有何益呢?”李世民这样对待人的办法足以对所有人都构成教育和感召。
贞观六年,李世民的一位外任大臣张公谨死了,李世民第二天就准备去吊唁。管理皇帝生活的官吏就对李世民说:“今天是辰日,按历法今日不宜哭泣。”劝李世民不要于这日吊唁。李世民则说:“君之于大臣,就像父与子的关系那样,我哀哭臣的死是情发于哀,安避辰日。”于是前往吊唁,悲恸哀哭以表其情。
从这几件事上,已足见李世民用人恩信并施的绝妙之处。他正是以此手段揽住不少英雄豪杰之心,反过来,英雄豪杰也因此而乐于为其所用。李勣有出将入相的大才,李世民对他非常器重。一次李勣得了暴疾,医生说只有胡子烧成的灰可疗治此病。李世民听说后马上剪下自己的胡须,为李勋熬药。李勖当时感动得“顿首出血泣谢。”李世民对李劫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社稷,并非为了你,没有必要谢我。”还有一次李勖陪李世民吃饭,李世民对李劫说:“我在群臣之中寻找可把年幼的太子托付给他的人,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比过你。你过去不辜负李密,当然也就不会辜负我。”李勖再一次被感动,高兴得豪饮而醉。李世民竟将自己的龙袍御衣脱下来盖在李勖的身上。李勖后来果然力佐李治。
当然,“伴君如伴虎”,就是因为君心难测。李世民也有多疑的时候,特别是他的晚年疑心更重,所以也冤屈了不少他过去非常信任的人。但是,在大的方面,李世民用人一直是恩信并用,恩以结人,信以任人,君臣团结,配合默契,遂有大的作为。
李世民的君臣之信
李世民所用的重臣中,宋公萧踽,性情狷介,对人要求很严格,以至于很教条刻板,所以与同僚多合不来,有一次萧踽向李世民告发房玄龄说:“玄龄与其中书门下群臣,朋党不忠,把持权力,陛下却不知道他们在为非作歹。”李世民对房玄龄的信任是很难让谗言离间的,所以他对萧踽说:“卿所说的话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更何况人不可以求全责备,所以人君用人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然算不上聪明,但是也不至于糊涂到连房玄龄这样的人还看不清。”萧踽从此也就被李世民所疏远。
从这段话来看,可见李世民用人的信任是建立在取其所长,舍其所短的基础之上的信和任。
魏征曾对李世民专门上书奏事,讲用人的方法,这是中国古代用人艺术的经典之作之一:
“在朝群臣,当枢机之所寄者,任之虽重,信之未笃,是以人或自疑,心怀苟且。陛下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成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维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
以上这段文字其意思是说:在朝廷做官的人是国家枢机所寄托的人,陛下对他们委以重任,但对他们的信任却未达到笃诚的地步,这样,群臣各个心有疑惑,生怕见疑于君,所以心怀苟且,不敢真正任事。陛下为人处事,处大事比较宽怀,对于小的错误和罪过,则临时治罪,未免感情用事。委大臣以大事,责小臣以小事,这是用人治理天下的道理。现在陛下,在委任职责时,重大臣而轻小臣,但一旦出事,则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这样,信任你所看轻的人,而怀疑你所倚重的人,要想求天下大治,能达到目的吗!若陛下重用某人为大官,反倒去寻找、责备干大事之人的细错小过,这样,那刀笔之吏,就会顺从陛下的心思,舞文弄法,构陷大臣于罪过之中。这些大臣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自己向陛下陈述解释吧,又害怕陛下认为他们心里不服陛下;如果保持沉默,则害怕陛下认为那些刀笔吏所构陷的罪过都是实有其事,结果使这些大臣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不能自明于陛下。这样一来,君臣之间疑心大起,大臣们便苟且为官,以求免祸,就会在官吏中形成矫伪的习惯和风气。
李世民看了魏征的奏书以后,深以为然,并以此时时告诫自己。所以,贞观之治中,君臣关系比较融洽,相互信任,赤心相推,遂有天下大治的局面,垂范有唐一朝。
毛泽东委傅作义以重任
要做到求才若渴,必定要视野开阔,广泛察人、信人并用人。证明一个领导会用人的表现,就是他用人不拘一格,千变万化,因人而用。反之证明一个领导不会用人的表现,就是他用人过于拘泥,没有变化,死气沉沉。
近代诗人龚自珍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可是,如果领导用人拘于一格,老天“不拘一格降人才”又有什么用?
事实上,拘于一格,不敢大胆用人、灵活用人的领导比比皆是。他们的做法,往往使得人才无法冒尖、无法尽其所能,间接地使企业失去生机,失去竞争力。
所谓用人以胆,就是对人才大胆使用,不拘一格。
傅作义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曾任张家口绥靖公署主任兼察哈尔省主席和华北“剿总”总司令,驻北平。天津解放后,傅作义基于爱祖国、爱民族的热忱,以保护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物为重,于1949年1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194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傅作义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第一句就说:“我有罪!”毛泽东却对他说:“你有功,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又对他说,北平和平解放最好,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说,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去。将来咱们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到北平以后,就要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和华侨等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你可以被邀请参加会议,你有功,也有代表性。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积聚在傅作义心头的疑虑顿时冰消雪化。他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他回北平以后,一定向部下传达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指教和关心,一定要做好部队和平改编工作。并表示他个人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保证把工作做好。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弥补我过去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