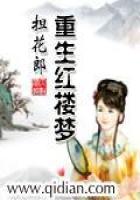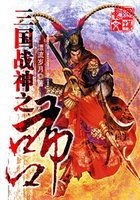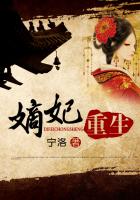话未说完,意大利公使起来解释:“我前天到贤良寺拜谒你,曾问徐侍郎这个人怎么样?你说,这个人不好。监斩许景澄侍郎、袁昶太常寺卿、徐用仪尚书等(主和派人物)都是他。他还逼死了自己的父亲徐桐相国。这种人,中国不惩办,各国只好代办。”李鸿章愕然:“我不过随便一句话,你们竟作为证据。”对尚书启秀的罪状,各国也找到了凭据。
如此一来,这场和谈便有些扑朔迷离。这时,天色已到黄昏。各国公使说,今天开议,未能议结,先散会,明天再制定照会文件。奕劻私下里对随员陈夔龙说:“看这个情形,英年、赵舒翘也许可以减罪。”
哪知,第二天照会送到,只见那罪名依然如故,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丝毫没有减罪的意思。并且,德国公使还怂恿军事统帅瓦德西,以动用武力相恫吓。在这样的强势话语之下,清朝的外交家们又能做什么呢?
后来,还是按照各国公使的意思对那些强硬的抵抗者作了处理。这中间,含冤而死的,只怕是不乏其人了。
当事者的隐痛
这段议和故事,后来的许多历史叙述中,都把李鸿章、奕劻、荣禄等人当作卖国贼来看。从民族主义立场看,这也许是有道理的。但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他们别无选择——除非亡清。
当时参加谈判的陈夔龙有一段剖白:“辛丑和约,肇于庚子之乱,条款之酷,赔偿之巨,为亘古所未有。当时主款议者,几为众矢之的。旁观不谅,责备之严,诚不足怪。庸讵知当局之负诟忍尤,艰难应付,有非楮墨所能罄者。”
是啊,你怎么责骂都不足为怪。你们哪里想得到我们这些人艰难应对,要对付各国的欺侮,还要看两宫的脸色,可是纸墨所能形容的?
这段肺腑之言,大概可以看出当“夹心人”的痛楚了吧!
晚清一次金融危机的化解
金融危机的来临,有时是因金融系统本身出现问题引爆的,有时则是在外力的压迫下产生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在北京闹得惊天动地,许多金融机构都受到了影响。如何来破解战乱中的金融困局,成为了摆在北京当局面前的现实问题。
其时,担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的是干练精明的贵州人陈夔龙。作为当事人,他在自己的《梦蕉亭笔记》中,对其中一场危机的起源与化解作了清楚记载。
金库被烧,市面瘫痪
五月十八日,闹得正凶的义和团一时兴起,放火烧了大栅栏(京城地名)中的一家洋货铺,火势迅猛,成燎原之势,结果把大栅栏东面的珠宝市整个市面烧为灰烬。而当时的二十多家炉房,就设在珠宝市。
所谓炉房,其实就是金库。因为当时使用的货币主要是银两,须熔铸后方好保存,炉房最初就是代客熔银的地方,后来逐渐演变为存银兑银的机构。
珠宝市的那二十多家炉房,是平常信誉最好、最有影响力的,足可和现在的几大国有银行比肩。试想,如果没有了金库,那银行是发不了钱的。同理,炉房毁了,那钱庄、钱铺自然也兑不出钱来。
因此,义和团的这一场火,烧毁的不只是几栋楼宇,而是烧毁了整个金融市面。
果然,因为炉房被烧,东四牌楼最著名的钱铺恒兴、恒利、恒和、恒源(世人通常称其为“四恒”),第二天就歇业了。
这可非同小可。
这四家钱铺,在京城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信用最好,流通也最广,如果真的就这么停业了,那可是关系到京城数十万人的财产生计问题。一时间,人心惶惶,大有末日来临之势。
几经周折,官银救市
作为地方官的陈夔龙,自然得负起救市的责任,不然朝廷问责也担待不起。何况,慈禧也当面过问了:“你是地方官,难卸其责,可这事究竟怎么办理?我想四恒并非是没有钱,不过为炉房所累,一时周转不过来,如果是他们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钱给他们,从速开市,免得老百姓受苦。你赶快找这些钱铺商量办法,最好三天内办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有慈禧的指令在,但陈夔龙还是愁得不行。谁都知道救市要靠政府注资,可要政府拿出那么多银子,一下子哪能啊!
他思来想去,找了许多人,都想不出好法子。
最后,一个名叫邢兆英的小官献了一条计策,他说,要筹款接济四恒,京城共有一百多家当铺,都很有钱,如果发一道命令,让每家借一万两银子给政府,那就是一百多万两,完全可以缓解这场金融危机。这确实可算一条权宜之计。但陈夔龙知道,对当铺可不能轻易下手,这里面有好多铺子是有权有势的人入了股的。再者,靠官势去硬借,到底不好。他又想到,慈禧可是当面答应可以用政府的钱去接济四恒的,虽然顺天府没有钱,但朝廷应该还有钱可借,那就不必去找当铺的麻烦了。
可是,借官银也并非易事,至少要有过硬的担保才行。四恒借了官款,如果万一不还,陈夔龙一介穷京官,如何担待得起?
经过商议,他们还是想到了好办法。那就是京城里大宗商务,如木厂、洋货庄、山西票庄、粮食铺、当典铺,都借有四恒的银两,四恒都收了借据的。把这些抵押给清廷,再把宫里面的银子借出来,应该是可行的。陈夔龙把这个办法报到慈禧那里,迅速就得到了批准。
事情至此应该有了个圆满结果,可这时又出现一个小小的波折。
陈夔龙奏请的一百万两银子,五十万两由皇宫库存发出,另五十万两由户部交付。皇宫那五十万两第二天就发了,但因为战乱,户部工作人员星散,办公地变成了驻兵地,那五十万两哪里领得出来?
正在这时,又有人指了一条明路。这人原来是陈夔龙在兵部时的同事,他说出户部有座内库在东华门内,当咸丰年间英法联军侵略京城时,咸丰曾命提银一百万两,存在内库,以备急用。这笔巨款已经四十年未曾动用过。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陈夔龙赶紧找人办了手续,把五十万两银子领了出来,交付四恒。
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危机就这样化解了。这一过程看似曲折反复,实质上还是很简单,那就是靠政府注入大笔资金来救市,——这和现在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当时战乱四起,做任何一件事都不容易,找这么一大笔钱更不容易。好在陈夔龙还算干练,和朝廷的关系也不错,不然就只有听天由命、望乱兴叹,让老百姓置身水火中了。
陈夔龙在自己的笔记中,对这件事很有一些宿命论的感慨。或许,在他看来,能完成如此一件艰巨的任务,实在是一件奇迹,大概就像梦一样吧!
清朝保密工作轶事
不管是在政府机关,还是在生意场上,甚或是个人的工作生活,人一辈子总有些秘密要保留。为此,保密与窃密的斗争,总是无处不在。一段时间来,荧屏上关于谍战、潜伏一类的电视剧此起彼落、接连不断,足见这类题材,是如何勾起人们观瞻的兴趣。
清朝的保密工作,也有许多有趣的地方。
清朝从关外入主中原,要确保政权的稳固,自然要想出种种控制手段。这些手段,有些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保密工作就要做得严实。
刚开始,由于一切处于草创阶段,这方面做得并不好。连军机处这样的核心机密产生地,也经常有泄密的事件发生。
“时有部院官以启事画稿为名,侦探消息传播街市,目为新闻”。这么容易就能获得秘密,实在是很好玩的事情。当然,这些刺探消息的官员并不是什么好鸟,他们把一些政府机密传播给大众,除了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外,根本没有其他好处。
但,这对于清廷政局的危害是严重的。
大概是意识后果的可怕,军机处自嘉庆皇帝开始,保密规章变得严厉起来。比如,军机大臣只准在军机处处理当日所奉谕旨(皇上的指示),其他部委机关的文件不准在军机处处理,一般的官员不准到军机处报告事情,甚至,军机处的章京(专职办事官员)办事处,一般官员都不得窥视。这是对保密场所的严格管理。
对文件的办理,也逐渐完善。当时每天的奏折,是在寅卯二时(约现在通常的早上上班前)发下,由军机章京分送各军机大臣传阅。凡是在奏折上批有“另有旨”、“即有旨”的奏折,由军机处章京用专门的保密匣子装好,请军机大臣到皇帝处请示,军机大臣再根据皇帝的意思,指导章京们起草圣旨,再报经皇帝亲笔改定后,交各机关办理。至于文件的传输,大多交由兵部承担,要层层签字画押,责任到人,确保万无一失。(《养吉斋丛录》)
保密工作的细致,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清廷的稳固和中央集权。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信息新技术的采用,保密工作不断遇到新的挑战。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电报开始广泛运用,但这项传自外国人的技术,我们并没有熟练掌握,导致失泄密的事情常有发生。
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给清朝驻日公使汪风藻发了一封函件,商量有关事情。第二天,汪风藻就给国内的总理衙门拍了一封长长的密码电报,其中就包括陆奥宗光函件的内容。
日本人是具有强烈的“密战”意识的。当时负责监听的日本电信课长佐藤爱磨截获了这份电报,因为加了密,一时还破译不出来。但这位佐藤通过分析清政府平日发给汪风藻的电文,很快发现了清廷密电码的编排规律,掌握了破译方法。
自此后,日方通过监听,完全掌握了清廷的政治、军事等重要情况。甲午战争期间,日方把清国陆军、海军的一举一动,都收入眼底、了如指掌。在这种情报不对称的情况下,这场著名的海战成为中国的耻辱之战,就不足为怪了。
保密工作要做得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子上,还是保密工作意识要强。
据载,晚清时有一朝廷重臣手中掌握着一个重要文件,这位老兄把文件藏在靴子中,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哪知,他家里有位家庭教师刚好是个“秘密”贩子,用钱买通了大臣的孙子,让他在爷爷睡觉的时候,把文件偷了出来,抄了个复本,卖了一大笔钱。
还有一位大臣更是可笑,他是张之洞的接任者,张之洞在任时,选派了两个“情报员”出国留学,结果,这两人,一个侦探得法国海军秘密,一个探听到了日本的秘密。这两个人探得秘密后,马上向当局作了报告,可那接任张之洞的大臣却十分愤慨:“我们每年费这么多钱,没想到培养了两个‘贼’出来!”
这些,大概是保密工作的大笑话。这些人的保密工作意识,是何等缺乏呵!
能延寿作药的鹿脯
鹿脯,顾名思义,与鹿肉有关,但切不可以为是鹿的胸脯肉。查词典,“鹿脯”词条下的解释是:鹿肉干。因此可以肯定,鹿脯是一种经过了粗加工的肉制食品,而不是新鲜的鹿肉。
关于鹿脯的吃法,所见记载不多,常见的有蒸、煮、炖、烤等几种。上次与一老饕式的朋友谈美食,他介绍了一款人参蒸鹿脯,说是既有丝丝缕缕的滋补,又有丝丝缕缕的香味,说话间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清代时,满洲贵族对鹿情有独钟,除了取鹿茸为药材外,鹿肉也经常成为餐桌上的珍馐,满汉全席中有一味烤鹿脯的菜肴,风味十分独特。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写在秋爽斋起海棠诗社大家起名号时,有以下这样的文字:“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吧。’众人都道:‘别致有趣。”黛玉笑道:“你们快牵了他去炖了脯子吃酒。’众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了。快做了鹿脯来。’”这里没有真正写如何烹调鹿脯的,但从黛玉的言语中,可以知道鹿脯是可以炖了下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