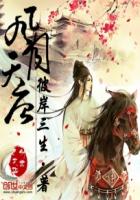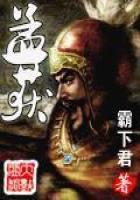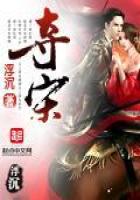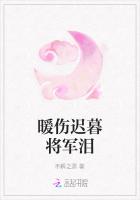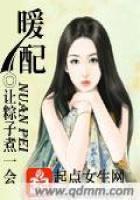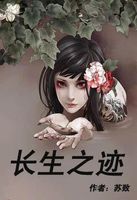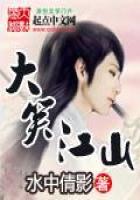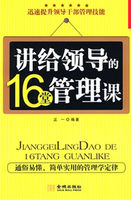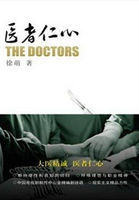陈夔龙时时思念,常坐书房流泪。一天街上闲逛,在一家服装店里看见一具木制的模特儿,身著翠绿绸旗袍。陈夔龙徘徊良久,终于以高价买回这模特儿。摆在房间里,肃然独对。据说,这模特极像许夫人。
陈夔龙情深如此,许夫人也算不枉了。
陈许的爱情故事说明:第一,爱情有很多种,并不是只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才感人;第二,纠缠着世俗功利意味的爱情,有时也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同样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尊重。
“义和团”不好玩
义和团,或者叫“义和拳”,对于已近中年的人来说,应该是个十分熟悉的称谓。
记得小时候的读物,特别是连环画里,经常有对义和团如何神勇、如何“刀枪不入”的描绘,夸耀他们在扶清灭洋、锄强扶弱的事业里轰轰烈烈、气壮山河。对这些传说,在当时我们还是很相信的,至少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义和团代表了一种神秘的正义力量,他们杀那些侵略的洋人就像砍冬瓜一样容易,实在是浪漫有趣得紧。
及至到了年长,看惯了红尘冷暖,走过了岁月沧桑,才知道那不过是一些文人的粉饰之词。义和团也是人组成的,是“人”,就不可能违背人的自然规律,怎么会“刀枪不入”呢?
后来,又看了一些当时的记载,发现除了反对侵略值得肯定以外,义和团的有些做法也值得怀疑。当年心目里崇高的义和团,现实中并不好玩。
蒙昧无知
“蒙昧”是体现在义和团身上的关键词。
义和团以反对洋教为己任,但其反对洋教的工具,却依然是中国一些传统的神秘主义的东西。他们相信的神并非完全来自佛、道等正规宗教。大概是佛、道这些正规宗教的教义太过深奥,普通义和团成员不容易接受。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些传说中熟悉的人物来作为自己的神,比如关云长、姜子牙、孙悟空、二郎神等。这些人物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打架非常厉害,很勇猛,具有神秘的“功夫”,经常打胜仗,另外就是经常在小说、戏曲里出现,即使是不识字的农民也十分熟悉。
义和团如何借助这些神的力量?
他们采用的也是极简单的在农村流传的降神附体的方式,每一个义和团成员都可以请得这些神附在自己身上,使自己变成神的代言人,从而“刀枪不入”,天下无敌。至于义和团的首领,则比普通成员要更加厉害,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无所不能。
可以说,义和团其实还是很愚昧的。从他们信奉的神来看,根本看不到他们的先进性。这种愚昧,也注定了他们是必然被利用、必然要失败的。他们号称神力无边,但现实却如同我们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一样,面对洋人的现代枪炮,这些被“神”附了体的人,常常不知不觉就成了炮灰。
只可惜,他们死的时候,还不知怎么回事,或者是在惊讶:怎么还有比“神”更厉害的东西?无知者无畏,但这无畏的代价也太大了些。
残忍嗜杀
“残忍”,是义和团的一大特色。
这么说,可能会有人不同意,因为义和团杀的是洋人,是侵略者,不能用“残忍”来形容他们。
其实不然。正如他们所信奉的神是那样莫名其妙一样,他们对正义的看法也莫名其妙。比如,他们“扶清灭洋”、反对洋教,是因为有些团民受过洋人、教堂的欺负,这还可以理解。可是后来,连所有沾“洋”字的东西都反对,对所有与“洋”字有关联的人都残酷虐杀,这就过于残忍了。
1900年6月中旬,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义和团大规模进入北京、天津地区,灾难也随即降临到这两座名城。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凡是用洋物的,一个都不放过,如有谁用眼镜、洋伞、洋袜等,在义和团那里肯定是死路一条。“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有一家人甚至因为有一盒洋火(火柴),八口人全部被杀。
这种景象,实则比“残忍”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可怜可悲
当然,义和团还是“可怜”的。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似乎代表了朝廷的正义力量。但清廷对义和团,却只是抱着利用的态度。
天津西郊的杨村之战,义和团奉命上前线冲锋,不堪敌人机枪扫射,掉头逃跑,却又为清军所阻。两面机枪夹击之下,死伤殆尽。
东交民巷之战,慈禧的亲信荣禄对此深怕敌方不支,而致使馆夷为平地,不惜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使馆防御。(见笑蜀《庚子读史笔记》)
如果这些史实还叫人半信半疑的话,那在八国联军正血洗北京、残杀义和团的时候,清廷已开始与侵略者议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1900年9月7日起,为了讨好侵略者,清廷竟开始连续下令剿杀义和团,命令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
义和团打着“扶清”的旗号,最终却被清廷所扑灭,这真是一个极大的反讽。义和团的可怜之处也正在这里。
一则笔记来看义和团
为了说明“义和团不好玩”,这里再引一则当时的笔记。
笔记说,庚子年间,有义和团的成员为躲避八国联军的屠杀,藏在京城西边的翠微山里,因为战争期间,后勤工作跟不上,团民们没有吃的,实在饿得忍不住了,就抓了邻村一个姓韩的富户,勒索一万两银子。这姓韩的没那么多钱,请团民们再少一点,义和团不答应,竟把这姓韩的杀掉了。这韩富户的老婆可不答应了,想跑到官府去告,一转念官府奈何不了义和团,于是直接跑到洋人那里,那洋人的部队办事倒很迅速,一会儿就派兵到了翠微山,义和团的伙计们此时还正在呼呼大睡呢。只听一排枪响,团民们纷纷惊起,仓皇抵抗,哪里是洋人的对手,一会儿全部被杀光了。(《汪穰卿笔记》)
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第一,义和团很残忍很可怜,居然绑票撕票,到头来自己也没落得个好下场。第二,清政府很无能,连自己的子民也保护不了。第三,侵略者很讨厌,义和团的事,再怎么说也是当时中国的内政,要你们来瞎操心干嘛?杀来杀去,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真乃千古至理也。
议和之中的“夹心人”
鸦片战争开始后,清廷当局几乎完全没有主见,任由下面主战派和主和派两派大臣打闹,谁占了上风就听谁的。看着打了几次胜仗,便立即主张战斗下去;眼见节节败退,又赶紧和入侵者谈判。
如此反反复复,迁延数年,条约立了不少,银圆赔了不少,土地割让不少。换来的,当然只是片时的安宁。逐渐的,倒形成了一定规律。往往先是主战派占了上风,与侵略者一阵猛打,但由于无论是士兵训练上还是武器装备上,都逊了一筹,打不过,情势变得危险起来。这时,主和派就派上了用场,朝廷无奈,急急忙忙地让他们去和入侵的列强谈判,直到暂时平息。
这中间,朝廷的最高掌权者是没有多少绝对性意见的。常常一下子信任这个,一下子又听信那个,两边摇摆。从主战派来讲,打了就打了,打不赢就算了,最终的处罚无非是革职、杀头一类,结果简单直接,一点都不复杂。倒是主和派,等到收拾战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在清廷的决策人和外国侵略之间周旋,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作为中国的谈判代表,无疑要顾及朝廷的面子,但外国的坚船利炮虎视眈眈地守在那里,又哪里敢表示半点强硬的态度。
因此,直接参加和谈的人是名副其实的“夹心人”,两边都不讨好,的确不好当。
忍气吞声到处拜访
话说庚子年(1900)七月廿一日,面对气势汹汹的八国联军,预知战事无望的慈禧、光绪仓皇西逃。接下来的两个月,被委任为全权谈判代表的李鸿章、庆亲王奕劻陆续赶到京城,开始和联军议和。
这个过程当然是艰难的。
首先是各国之间的意见就不一致,这个国家认为要这样,那个国家认为该那样。令人头痛的还有,就是各国的外交公使和本国的统兵军官的意见也不一致。李、奕二人带领一帮随员遍拜各公使,费了不少口舌,纷纷扰扰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才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协议。议定的条款对清廷当局来说酷虐异常,但自己身处弱势,只能是无可奈何。如果撕破脸皮,只怕战事又起,到时又还得修补条约,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只好忍气吞声。
外国人的意见得随时向上面报告
当时李鸿章已到垂暮之年,有病在身,参加正式谈判常常不能亲往。两位全权代表中,开初时只有奕劻能亲自履行职责。
开议那天,奕劻带了陈夔龙、那桐等一干随员,来到日本使馆。日本公使代表各国将条约内容宣读了一通,即交给奕劻,举止间甚是无礼。
奕劻虽是全权代表,但也终究只是代表而已。当然不敢擅自做主即行答复。出得使馆,奕劻很是伤感地对跟随的陈夔龙说:“端王等人因为迷信义和团,导致了这场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今天的会议令我难受。可为国受辱,又还有什么话说。你要速将各国公使递来的条约交李中堂(鸿章)阅看。即日发电给行在(慈禧、光绪),希望他们能批准。这事必须在今日办完,电稿也不必送我审定,发后抄一份给我就行了。”
奕劻这番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派自己来议和,真的是受气,但又没有办法;二是条约的事情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禀报给上面。
从这一点来看,奕劻还是比较清醒的。兹事体大,事关中国数万万人的福祉,自己如果胡乱做主,背的是千古骂名。
陈夔龙不敢耽误,马上去请示李鸿章。李鸿章这时病重,见不了客。好在他早有交代,指示像这样的向最上头报告的事,要用“重”笔来写。陈夔龙素以干练闻名,这时便抬出宗庙社稷,用“重”笔起草了一份电稿,让李鸿章的儿子送进去审定,并即刻发电。
上面犹豫不决,具体操办之人难受
电文一到西安,慈禧、光绪也知事情重大,马上进行研究。这两位计议半天,发现很多事情不合自己的意思。
比如,赔偿的款项太过巨大;要求惩办的一些大臣罪名太重;德国公使还要求在京城建纪念碑,这可有碍国体,等等,反正这些事情都不能同意。
这时,荣禄正跟在慈禧、光绪这两位巨头身边。作为臣子,他深知李鸿章、奕劻他们议和的不易。因此,在慈禧和光绪面前,他婉言力劝,一再说事情紧急,不答应的话就有可能再起战火。
慈禧听了,竟发了火,说:“请皇上斟酌,我不能管。”这很有些无赖的意味。
第二天,北京两位全权代表又发电来催,称各国公使正在等答复,以决定是否继续进兵。荣禄赶快据实上报。
这时的慈禧更无赖了,居然说:“两位全权代表只知道责难我们,不肯向各国公使据理力争。我既不管,皇上也不管,由你们管去吧!”话一说完,竟将电文扔在地上。荣禄不敢言语。
光绪这时出来解围:“你们也不用着急,明日再说。”
荣禄回到府邸,想着这种情形,就是明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自己和奕劻、李鸿章这些谈判代表,两头不是人,心里的苦楚只有自己承受。事情还是要做的。他揣测:“默想慈禧的意思,也知道这事情非答应不可。不过难以当面说出‘答应’二字罢了。”
两天后,见了慈禧和光绪,荣禄先说了一通其他事,最后轻描淡写地说:“前日两位全权代表发来的电稿,已经过去几天了。中间又有电文来催。能否让我们先起草一份回电,再报请您审定后电发?”
慈禧心里到底不爽,沉默了一会儿,见情势难以挽回,只得说:“如此也好。”
荣禄得旨,赶紧拟制了回电,并迅速呈报慈禧。慈禧含糊应允:“知道了。”
得了圣旨,荣禄即安排发电,奕劻、李鸿章等收电后马上知照各国公使,议和便基本成了定局。
这是庚子年底(1900)的事了。一年后,荣禄向陈夔龙说起这件事时,感慨万千:“你们在北京应付各国公使,处境艰难。我在西安两宫(慈禧、光绪)前面委曲求全,最后总算完成了这件事,处境更难。”
呵呵,“夹心人”真不好做也!
接续谈判也艰难
和议基本达成,两宫安然回到北京。
接下来,就是讨论惩办“抵抗者”的事情。这次谈判放在英国使馆。因为李鸿章已经病愈,便和奕劻及一干随员同赴英国使馆。
英国公使首先发言,无非强调这次各国到中国来,却遭到了义和团的抵御,其中罪魁祸首是端王载漪,只要把端王从严处理了,其他人可以不论。听了此言,奕劻马上作了否决,因为端王是皇室亲属,万难重办。
那英国公使早料到会如此,立即又抛出一份要求惩处的名单,中间有庄王载勋、右翼总兵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都要求从重从严论处,其他则依次递减。
对这些人的罪名,李鸿章、奕劻心里清楚,像庄王、毓贤固然有罪,但总兵英年并没有实权,不过是在联名抵抗的告示上署了一个名,这也犯不上杀头之罪,最重判个死缓就够了。至于尚书赵舒翘,仅仅是陪同刚毅在京郊视察过一次,根本没有什么仇洋的实际行动。即使不应该附和刚毅,革职就行了,哪里能判重罪?
当时,中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各国公使似乎也同意中方的观点。可还有一件事让李鸿章很不明白,他问各国公使:“前几天你们所说的罪魁,并没有尚书启秀、侍郎徐承煜,今天忽然将二人划进来,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