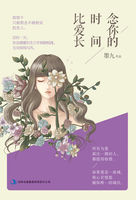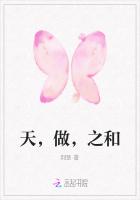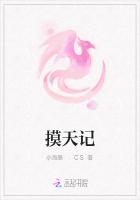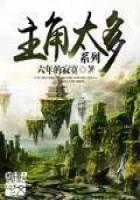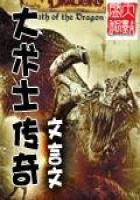游损在含山县登科桥安了家,生了一男一女,过了几年甜蜜的生活。近些年,由于朝廷依然大进“花石纲”,搞得天下鸡犬不宁,人心慌乱,交通不顺畅,长江上各类生意受到很大的冲击,不少的商贾被迫关门,人们怨声载道。在这种的状况之下,木材厂的木材没有办法正常营销和外运,所以游损的生意淡了下去,只能吃老本。
游损带着父母等家人乘车来到含山轩辕岭山麓,游损的妻子和儿女见了爷爷、奶奶无比欢喜,连忙迎接进屋。
房屋盖在含山登科桥边上,是一座大合院,背山面水,周围群山环拱、竹木掩映,朝夕鸟语脆然。庭院前有一块菜地,屋后有竹林。游酢抬首,南面的轩辕岭高耸入云,忽然想起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见此环境,心中无比欢喜,便住下了。
晚饭时,游酢问道:“这房子花了多少钱?”游损回答说:“不多,三十贯。”游酢听了说:“确实不贵。在洛阳,一枝魏紫的牡丹花也要一贯钱。”家人听说一枝牡丹花如此昂贵,都咂舌,游损讲:“这么说,我们这座房屋才值三十枝牡丹花,真是山里比不得城市。”游酢叹道:“山里好啊,时局太乱,我年老了,隐退江湖能够有个栖身之处也安心,过一段就回老家建阳去。”游损说:“爸,这里不是同样能够养老,再不行可以到历阳城的家去住,为啥一定要回建阳?”游酢说:“古话说‘叶落归根’,我虽然一生大多时间在外,但是在我的心里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吕氏也说:“老爷说得是,我也非常想老家。我和老爷回去,你们下一代最好也回去,如果实在不想回去,也不勉强。”游损和媳妇等听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沉默。
吃过饭,游酢便到屋里休息。
过了三四天,游酢想去历阳走走,吕氏也心想去看看那个曾经住过的地方。游损租了一辆马车陪同父母前往。
含山与和县交界,从轩辕岭出发到历阳城有半天就够。
到了游拂的店铺门口,游损跳下车喊道:“哥,爸、妈来啦。”
游拂和媳妇闻声奔出店来,将父母迎接进去。一家人相聚的喜悦,自不须细说。
吃过午饭,游酢对吕氏说:“我回‘立雪堂’住。你呢?”吕氏应道:“我也去。”游拂和媳妇听了说:“爸、妈,这里可以住。”游酢说:“不要,我那里清静,好读书。”游损说:“哥哥、嫂嫂,爸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懂,让他去吧。有空的时候多去关照关照就可以。”
下午,一家人忙着打扫、整理立雪堂,左右邻居知道了也赶来帮忙。到傍晚,房屋的卫生基本已经搞好,床铺铺好,锅灶能够生火烧水、做饭了。
当晚,游拂请岳父杜善老板过来,一起为父亲洗尘。这时,游拂的生意景况也每况愈下,大不如前。但是,他不敢在父母的面前露出任何的表情。游损知道情形,也不好抖出实情,只好委婉地请父母回到含山生活。游酢回答说:“先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再说吧。”游损只好自己一人先回去。
第二日,附近的许多老百姓听说游酢回来了,都很高兴,前来看望、祝贺。
吕氏欣慰地说:“你年纪那么大了在外,我天天担心,现在回来了在一起了,我悬着的心总算安定下来了。”
几天后的一个晴朗傍晚,游酢到街上散步。历阳是和州府衙所在,街上居住着上千户人家,颇有几分热闹。这一条五百米的长街,还有那些大小巷和胡同,过去傍晚时他经常带着孩子来漫步。离开了一二十年,往事依依,这里的街道多少有了些变化,除了一些熟悉的老相识,来来往往的大多是陌生的面孔了。
忽然,听到有人说:“哎呀,游大人。草民有礼啦!”游酢一看不是别人,而是张半仙,于是站定问道:“张半仙,生意可好?”张半仙回答说:“回大人,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哪种生意都不好经营,我自然也好不了,勉强换一口饭吃而已。大人到我那摊子坐坐,叙一叙旧。”游酢回答说:“我已经辞官告老还乡了,今后就叫我的名字。我到这将会住一些日子,以后有的是机会,你先忙活去吧。”张半仙说:“那好,改日好好再谈。”他说完回到自己的家去。
游酢继续往前走。他又到“半边街”的“陋室”去。那里的主人虽然永远不可能再说话,但是他的魂灵才能理解自己此时此刻的心境。他来到“陋室”前,但见屋顶已经长了狗尾草,瓦檐看去满是绿绿的青苔,地面上一片狼藉,目不忍睹。看见如此凄凉的景象,他原来一路上积蓄的语言霎时化为烟灰,于是默默地离开那儿。
游酢老多了,况且大病初愈身体也觉得大不如前。平常在家里读书、练书法,有时帮忙带孙子,教孙子读书;有的时候到附近走走,与自己年纪相仿的人们座谈,偶尔下象棋,或者听听社会上传播的各种各样的消息。他已经完全与朝廷脱离关系了,只是每月还可以领到一份俸禄。人到了晚年,没有多少人有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样的胸怀。游酢虽然是读书出身者,一个历经宦海风波的人,他明白自己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东山再起了,只求能够平安地度过晚年。
游酢身体较好后,正想回老家建阳,这时吕氏却病倒了。游酢只好立即让三媳妇去请郎中,自己继续留下来照顾夫人。家庭的事务,全部落在儿媳们的身上。游拂的媳妇杜氏,她是个极孝顺的人,每日必有几次进夫人房间询问吕氏:“妈,你觉得身体怎么样?”或者“好些吗?”、“要吃什么,我去买。”吕氏见媳妇这样,心理很欣慰,总是温和地应答。其实,吕氏也想回建阳老家,可是不曾想到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病势日重,想到家庭困难,丈夫又年老多病,因此交代道:“老爷,咱家的景况不怎么好,你的身体又差,回去老家没有人照顾,还是先留在这里,等以后我们身体都好了些再回老家。”游酢觉得吕氏的话有道理,就安下心来,可是担心夫人的病重,把这事情写信告诉了玉儿和秋香。
秋香住在太平州,闻讯赶来看望吕氏。
游玉与丈夫在江苏,她收到书信无比伤心,扔下自己的家务,赶来和州历阳城。
游酢虽然解甲归田了,可是地方上的州县官员不时地有人前来看望,朝廷的官员偶尔路经江淮一带的州县,也会顺便来探望、慰问。毕竟,游酢曾经是朝廷的老臣之一。俗话说:“无官一身轻”,游酢本来是豁达的人,现在退隐在江湖,说话没有太多的顾忌,洒脱得很,谈笑风生。一次,有位朝廷来的官员问游酢道:“当今,谁可以为济世者?”游酢答曰:“陈了翁也。”
没有想到这番话很快在朝廷传开。有的大臣说:“知人者,游酢也。”蔡京等听了大为不高兴,可是游酢已经是退隐之人,没得他奈何。
吕氏的病情有了些好转,她知道玉儿和秋香毕竟都是已经有家庭的人,对她们说道:“我已经没有事情,再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有你们的哥嫂们会照顾,你们回去吧。”她们观察了几天,见夫人病情有了好转,便回去了。
游酢自从退居历阳以来,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晨起临池练书法,上午出去街上下棋,下午和晚间读书。
一天,游损夫妇又来看望父母。游损再次劝说:“爸、妈,我那儿山水好,到我那儿去比这历阳清静。”
游酢对历阳有一种深厚的情感,还是坚持留下来。游损夫妇没有办法,回含山去了。
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经历,联想到许多的往事,觉得几十个春秋就像一阵长梦,醒来万事如烟。这时,他想到还是庄子的《南华经》一书好,这本被禅学所崇奉的经典,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虽然自己年轻以来曾经几次读过,十分的喜爱它。可是,他后来入了程门改学儒家的学术,再后来又在官场混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时间再学习。现在,重新想起它,拿起它,每一天都看它,思想受到很深的触动,心灵得到了很大的净化。
庄子说:“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所以,“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是啊,人生是如此的短暂,万事回头一场空,可是人世间却还到处充斥着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甚至谋财害命或者血淋淋的厮杀,太残酷无情了;人类不少人除了自私,还缺乏应有的自爱、互爱、博爱,因此社会变成了赌场、战场、屠宰场……自己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对庄子的思想比过去理解得更深刻了些,过着“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的生活应当满足了吧,更有何求呢。
过去,对于庄子的有些话都不敢相信;现在读起来却理解了。回想起少年时江侧先生所教和青年之后入程门的所学,游酢觉得各有其所用,不过从立身处世来说,儒、道两方面需要完美的结合。可是,从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体验到,以儒家为正道的朝廷上那些表面上满嘴‘仁、义、礼、智、信’的君子,为了争权夺利,背地里却不惜陷害他人,甚至不顾天下苍生,不用说古代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残酷,即便是蔡京所制造的“元祐党碑案”就致使数百名官员、两千多人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对人们的迫害和摧残多么严重啊!那些玩弄权术者比猛虎凶恶,比蛇蝎更毒,他们确实远不如道家或者禅家清白可近。凡是看清了这一点的人们,怎么再能够去相信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呢?
游酢的思想日益地在向哲学的深处发展。他回忆起洛阳人接花的习俗,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虑,写了一首《接花》的诗:
“色红可使紫,叶单可使千。花小可使大,子小可使繁。天赋有定质,我力能使迁。自矜接花手,可夺造化权。众闻悉惊诧,为我屡叹吁。用智固巧矣,天时可易欤?我欲春采菊,我欲冬赏桃。你不能栽接,你巧亦徒劳。雨露草必生,霜雪松不死。有本性必生,亦时雨与之。所遭有变易,是亦时所为。时乎不可违,何物可违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