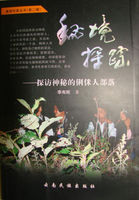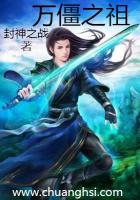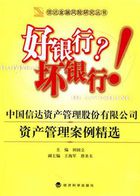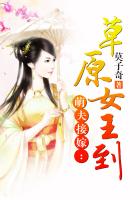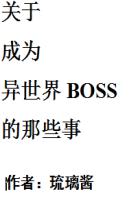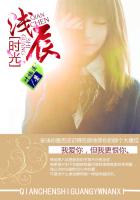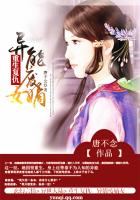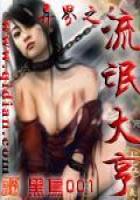一 鬼话“渡”得康王归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项羽悲歌骓如泥塑,泥马却怎么就偏偏“渡”他康王赵构呢?
“泥马渡康王”无疑是个传说。
传说的花,生在史实的根茎上,难解难分,令人眼花缭乱,也叫人拍案称绝。
传说中的泥马渡康王(赵构被徽宗封为康王,驾崩后庙号高宗)至少有着两大派系:一是“江派”,称泥马渡康王为“泥马渡江”;一是“河派”,称泥马渡康王为“泥马渡河”。
“江派”有宁波“甬江说”、扬州“长江说”;“河派”不像“江派”那样言之凿凿地落在某座城市的某个节点,但也还有“黄河说”与“漳河说”。
将“泥马渡康王”自南至北一路追问下去,最后走到了河北磁县县城内的崔府君庙。
这儿的刘先生说:康王渡的不是什么长江、甬江、黄河、漳河,而是位于磁县城北十公里的牤牛河。
牤牛河?连河的名字都不载史籍,没听说过,这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
2005年10月6日,在细雨蒙蒙中,和刘先生一起寻访牤牛河。
看到的,是条宽不足十米的小河沟,现在连水都没有了。
面对这样的小河,康王怎就没办法过?金兵怎就没办法追?
刘先生说:泥马渡康王和崔府君庙紧密相连,县城的崔府君庙虽然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并不正宗。正宗的崔府君庙在该县台城乡,要不,咱到那儿看看百姓怎么说。
继续北行约十公里,至台城乡。过泥泞小街,穿狭窄胡同,见了破旧的崔府君庙。
是个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位93岁老人的讲述,让我们顿有穿越时空、洞见历史的快感——它比专家学者书上网上的“泥马渡康王”,都要精彩真切。
这位老人说,康王渡的不是牤牛河,而是个小河沟。
小河沟名字更难听,叫蛤蟆沟!
泥马渡康王是经高宗本人点头认可的,难道泥马涉渡的,竟是小小的蛤蟆沟?宗泽无奈“装神弄鬼”
西湖南岸植柳成荫,清风徐来,摇得柳丝翻碧浪,浪涛间不时传来黄莺几声鸣啭,“柳浪闻莺”就此暴得大名。
“柳浪闻莺”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它在涌金门至清波门的滨湖地带。
南宋时,这儿是宋孝宗为奉养退居二线的太上皇赵构而建的御花园——聚景园。聚景园的北部,是显应观,“高宗以祀崔府君也”,“累朝崇奉异常”。
“显应”是宋朝皇帝对崔府君的封号。999年,真宗在磁州(今河北磁县)为崔府君修了庙;1035年,仁宗封崔府君为“护国显应公”;1116年,徽宗加封崔府君为“护国显应昭惠王”。
崔府君是何许人?
共同的记载是府君姓崔,名子玉,也有崔珏、崔瑗、崔浩诸说,其实不一,甚至被搞得张冠李戴。
早在仁宗封他为王时,对他的身世就已难以廓清。“崔府君封护国显应公诏”云:“惠存滏邑,恩结蒲人;生著令猷,殁司幽府;按求世系,虽史逸其传。”显然,他在阴曹地府那儿管点事。
据说,崔府君在大唐贞观年间曾任磁州滏阳令,因有“异政”,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显赫政绩,当地群众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曾设祠供奉他;死后,百姓就顺势把他奉作一方神仙给以供养了。
直到今天,磁县台城乡崔府君庙前的半拉对联还是“福佑磁州第一神”。而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写卷《唐太宗入冥记》,则云太宗因“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被摄入冥界,接受审判。审判唐太宗的,正是这位名曰崔子玉的冥府判官。
崔子玉作为一方百姓奉若神明的好领导、好神仙,皇帝下诏封号加爵,修庙祭祀,既可安抚一方,也能树个榜样,无外乎“因民所向而封崇之”,是那个时代很稀松平常的事儿。
更何况,这位神明在宋初曾被“引入”京师汴梁,在城北有了个崔府君庙,更因“公主祈祷有应”,太宗还遣内侍修缮并赐以庙名。
如此一来,太宗以下赵宋数位皇帝不断对其加官封爵,也算是渊源有自了。
不承想,赵家皇帝推波助澜神化崔府君,却被磁州百姓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拿过来当成了制约康王赵构奉诏北使金营、媾和金国的“神棍”。
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兵渡过黄河,逼近京师汴梁。钦宗为向金人示和,派遣九弟赵构渡过黄河,出使金军大营,并以割三镇、尊金主为伯等为条件,谋求宋、金议和。
赵构一行离京北上,由滑(今滑县)、浚(今浚县)至磁州。
此时此地,一段插曲,改变了赵构乃至大宋王朝的命运:磁州守将宗泽,劝说赵构拜谒位居通往金营驿道之侧的崔府君庙。
看到赵构,聚集于崔府君庙周围的人号呼劝谏,“民如山拥”。他们似乎对康王取道于此,继续北行与金媾和,表现出一种强烈不满。
入庙后,康王卜得“吉”签,州人借此抬府君轿舆、拥庙中神马,力请康王乘归磁州馆舍,不要北行与金媾和。
朱熹在南宋追述此事,说:赵构“出使时,至磁州,磁人不欲其往,谏不从”。
如此这般,宗泽“假神以拒之”,对赵构说:这儿的崔府君很灵,可到庙里卜上一卦;庙里有匹马,很有灵性,是匹神马。
于是,在宗泽劝说下,赵构进庙烧香卜卦。
恰在这时,马儿口衔车辇(车马备驾完毕),站立在赵构北去金营的路上。宗泽借此上奏赵构,说:“此可以见神之意矣。”
就这样,赵构打消了继续北使金营的想法。
今天我们已然无法复原当时的场景,但一个基本史实是:力主康王使金的刑部尚书王云,因群殴而死。从这个侧面,不难窥见当时局面之纷扰。
也许这一突发事端让赵构惊惶不安,甚至被迫取消使金“议和”。
但也正是这一转折,为大宋保全下了中兴的种子——当金人陷落东京,拿着皇家花名册,按图索人悉掳北国时,赵构成了“漏网之鱼”。正是徽宗的这位九皇子,日后应天(今商丘)即位,才有了史家所称的南宋,才有了眼下我们追寻的大宋南迁。
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认为:这些最初的叙述,或隐或显地露出了神人、神马背后起作用的,是一代名将宗泽与磁州“州人(百姓)”,让我们看到这些神人、神马的信奉者,也是神人、神马的操纵者,以自己的行为,给予神人、神马以特殊的灵异意义。
然而,到南宋楼钥奉诏撰写的《中兴显应观记》中,神人、神马已然成为事件的主动者:该记将“神马拥舆”视为“即位之兆”,并把此说当成“神之意”。
因系奉诏撰写,《中兴显应观记》无疑代表了当时朝廷的意志:“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营不百里。既出,谒祠下,神马拥舆……州人知神之意,劝帝还辕。”
在南宋官私记载中,“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被极力渲染,传说流变纷呈——为攀附皇帝,大江南北乃至黄河漳河的许多地方,都把它演化为发生在自家城边乃至村头的事儿。
既然臣民信以为真,为崔府君建观立庙,就是皇帝很乐意的事了。到了1186年,孝宗将崔府君由徽宗所封“护国显应昭惠王”升格为“护国显应兴圣普佑真君”。
这下,皇帝又顺势“强奸”了民意。
百姓总是玩不过皇帝。
猾吏投机攀附康王
“肃王已到金国为质,一去不返。眼下金兵兵压京师,殿下还非要去金营媾和,难道真会弄出个什么结果吗?”宗泽劝谏赵构道,“与其质身金人,不如留在磁州为妙呀。”
但是,“崔府君事件”发生后,赵构没在磁州滞留。
“从者以磁不可留,知相州汪伯彦亦以蜡书请帝(赵构)还相州。”于是乎,赵构在第二天就离开磁州,到了相州(今安阳)。
不幸的是,赵构登上历史舞台的原点,竟然左右了他政治生命运行的轨迹。
日后,相州知州汪伯彦成为“南渡派”的领袖,宗泽成为留守东京、坚持抗金的代表人物。
而安阳人岳飞,追随宗泽,在其培养下,成长为抗金骁将,其刚其烈,不逊色于临终三呼“过河”抗金的宗泽。
其实,在赵构应天即位、于坚守中原还是退避江南间犹豫时,就因“崔府君事件”,显露过对宗泽的“信任危机”。
主战派领袖李纲推荐宗泽担当东京留守,赵构以为宗泽有装神弄鬼的毛病,曾很不以为然地说:“泽在磁,每下令,一听于崔府君。”
在李纲解释“古人亦有用权术假于神而行其令者”,并强调京师特殊地位,非宗泽难有人当此大任后,赵构才勉强同意了这一任命。在李纲相位被革后,宗泽独撑抗金局面,尽管他一再上表,请求赵构还都东京汴梁,但赵构还是听信汪伯彦等的建言,决意南渡。
赵构近汪伯彦而远宗泽,似在情理之中。
赵构在应天府(商丘)期间,崔府君尚未被他视为自己的保护神。
传说中预示着赵构即位的“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吉兆,传播却晚于赵构在应天府即位。
就赵构本人,对所谓崔府君灵异的态度,也有个从建炎之际的否定,绍兴年间的下诏建庙奉祀,禅位之后亲临拜谒的接受过程。
而陪同赵构出使、在磁州亲历“崔府君事件”的中书舍人耿延禧,在赵构即位后,上呈《建炎中兴记》,述说种种“传国之祥”、“符瑞之应”,不但只字不提崔府君,还对宗泽与磁州百姓搬出“应王”(护国显应昭惠王),强阻赵构北行,持守完全批评的态度。
而《宋史·高宗本纪》在叙述宗泽“请(帝)留磁”后,接下来就是“磁人以云(王云)将挟帝入金,遂杀云”;“从者以磁不可留(侍从以为磁州不可留居),知相州汪伯彦亦以蜡书请帝还相州”。
康王赵构是奉钦宗之命出使金营的,按常理推断,他担负的是非常之秋的非常之命。而宗泽要想留下赵构,“废止”钦命,绝不是一两句深得赵构认同的话就能解决的。
宗泽必须拉出“神命”与“帝命”对决。而这个神,又是赵构的先祖捧出来的——信不信由不得赵构本人。
至于卜卦,只不过是个方式。赵构无论卜吉卜凶,宗泽都能给他个无可辩驳的解读。卜凶,那就更不能到金营了。
就是这样,宗泽还是放心不下。而“州人”打死力主赵构出使的赵构侍从、刑部尚书王云,也许还有宗泽的背后纵容。
《靖康纪闻》在叙述这一事件时,就说:“守土者(当然暗指宗泽)诡奏云:‘王云入境,忽为庙中神马突死(猝然踢死)。’异哉!”
不认神可以,你赵构在混乱的场面下,不向现实低头,就不行了:“王(康王)见事势汹汹,乃南还相州(《宋史·王云传》)。”
恐吓赵构,打死王云,这责任当然都得推卸到神的身上。不然,宗泽这样的小官与磁州百姓,怎么能担当担待得起呢?
于是,神话般的传说诞生了。
这传说,最初是什么样子,我们已无法得知。2005年10月7日,磁县台城乡93岁的贾先生说的“泥马渡康王”却是这样的——
大雁南飞,嘶鸣不绝。质身金营的康王赵构与金兀术决定追猎大雁,追着追着就追到了磁州台城乡村北的蛤蟆沟。天刚下过雨,蛤蟆沟的水激荡着向东流入黑龙潭,康王的马在此却步不前。
忽然,一位老人对康王说,你骑我的马过去吧。
康王换了老人的马,果然过了蛤蟆沟并到了府君庙。结果,他发现自己骑的马,原来是府君庙的“泥马”。此时,泥马大汗淋漓,还冒着热气呢。
金人没有泥马,过不了沟,被赵构甩在沟的对岸。
惊吓之中,康王躲到府君庙的神案下藏匿起来。迷糊之中,他给磁州的官儿托了个梦,说自己落难于磁州城北四十里的台城崔家。
磁州的官儿连夜带着人马,赶到台城。问谁家姓崔?百姓说,村里没有姓崔的,就崔府君姓崔。
来到崔府君庙,那个官儿看到神案上有野鸡翎(康王的穿戴是人家金人的),知道康王躲在下面,就救出了他。
磁州的官儿是谁呢?传说省略了。
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先生说:“那个时候,磁州的官儿不是别人,正是宗泽。磁县的‘泥马渡康王’传说与历史对接得近乎天衣无缝,盖因渊源有‘史’呀!”
天下不可一日无主。金军攻破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后,赵构侥幸留存下来,作为赵宋王朝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一些攀附之徒,开始为其登基寻找依据。
二 靖康:康王PK钦宗的谶语
“泥马渡康王”的传说架构,的确很棒。
但文献中第一次提及“渡”字,却是“崔府君事件”发生八十多年之后的事儿。
南宋初期,萧照画《中兴瑞应图》,曹勋赞曰:“云(王云)不知己,力邀北驱;应王(崔府君)杀之,天心所如。神民共济,乘以公(崔府君)舆;天命已兆,是为宝符。”
在这儿,宗泽一手导演的“崔府君事件”虽被解读为“中兴瑞应”,但无“渡”无马,只是坐轿而已。且一句“神民共济”,说得明白:大宋“中兴”,不能没有赵构,不能没有百姓;《中兴瑞应图》写的,自是赵构之意志。
嘉定四年(1211年),程卓使金,曾撰《使金录》,记下道里行程。程卓《使金录》十二月十四日“至磁州”云:高宗为王尚书云(王云)迫以使虏,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欲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
这是目前所见资料中对于“泥马渡康王”之“渡”最早的记载。
程卓试图将传说附会与历史事实、地理方位进行对接。他虽然很难确指神马助佑康王“南渡”的“河”究竟是哪条河,但“泥马渡康王”的传说,至此已有雏形。
在这儿,“民”被删除,成为“神人”,而马,还不是“泥马”,只是有了“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
在空间上,程卓倾向于“赵构自磁州南返相州”时,有“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以此推测,似乎赵构南渡的该是磁州(今河北磁县)与相州(今河南安阳)之间的漳河。
明末清初散文家、史学家,绍兴人张岱有诗曰:“项羽曾悲骓不逝,活马犹然如泥塑。焉有泥马去如飞,等闲直至黄河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