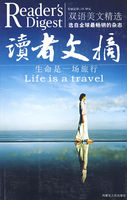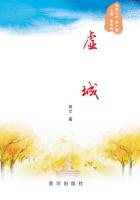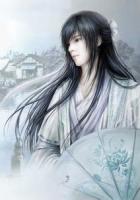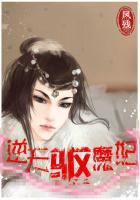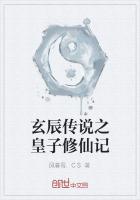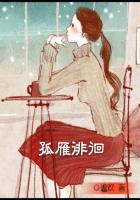2005年10月22日,以“莫须有”托词害死岳飞的秦桧,在上海“站起来了”。
艺术工作者金锋为秦桧夫妇塑了站像作品,名叫《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喘口气了》。目前,它正在上海一家艺术馆内展出。
秦桧站像高1.9米,王氏站像高1.7米。金锋表示:为秦桧夫妇塑站像是呼吁现代社会重视人权和女权,秦桧夫妇跪像是过去人权和女权被侵犯、被压迫的最好表现,逼人下跪或死后塑跪像都是侵犯人权的。
他声称,为秦桧塑站像不是为其平反。但这次跪着的秦桧能够“站起来”,也是有一点儿背景的。
2004年2月2日,在秦桧的家乡南京发现了一座宋代古墓,某媒体就以《南京发掘一古墓:疑是秦桧墓》为标题进行炒作,消息称“根据庞大的墓葬结构,说明墓主身份显赫……有可能是秦桧的墓”。同时援引南京大学教授贺云翱的话说:“这座古墓的墓主很可能就是秦桧。”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2月4日证实,该墓是一前一后两个规模普通的墓,南京某报又推断出此墓系秦桧“夫妻合葬墓”一说。2月7日,发掘现场令许多媒体感到尴尬:开棺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簪子、梳子、丝绸等物,死者显然是女性。然而,一些媒体仍然咬定秦桧不放松,称“女墓主可能是秦桧爱妾”。2月9日,一切真相大白后,一些媒体又称此墓是“秦桧假墓”……
“秦桧热”的背后,涌动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秦桧“站起来了”,倒下的到底是什么?
《大宋南迁》虽然只是《厚重河南》的一组主题报道,但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报道力所能及地回望、反思或唤醒些什么,因为那个时代的经验教训,同样适用于今天我们这个融合了五胡、契丹、女真(金人)、满族等的中华民族。
每个民族都敬重英雄,小瞧懦夫——每有大宋使者至金,金人就问李纲“尚能饭否”?宗泽、岳飞更不用说了,金人就直接叫他们“宗爷爷”、“岳爷爷”。
请问:金人这样称过、问过、呼过他们的走狗张邦昌、秦桧吗?
软骨头是每个民族都瞧不起的,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
历史的天空翱翔着宗泽的三呼“过河”,岳飞的《满江红》。
正气歌,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遗产与瑰宝。
谁擒住了方腊?
这个问题,我们太熟悉了。不是武松,还能是谁呀?
杭州西子湖畔,2004年复建了武松墓。在落实浙江省人大代表这一建议时,武松这位生擒方腊后于杭州六和寺出家的和尚,也顺势来了个抱得美人归——同时复建的钱塘名妓苏小小墓,就在武松一个箭步就能跨到的地方,与武松墓并肩而立。
尽管生擒方腊的功绩一再向武松身上扣,但活捉方腊的却是一代名将韩世忠。
《宋史·韩世忠传》记载:“宣和二年,方腊反,江、浙震动,调兵四方,世忠以偏将从王渊讨之……时有诏,能得腊首者,授两镇节钺。世忠穷追至睦州清溪峒,贼深据岩屋为三窟,诸将继至,莫知所入。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险数里,捣其穴,格杀数十人,擒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峒口,掠其俘为己功,故赏不及世忠……”《续资治通鉴》的说法,也大致与之雷同。
擒方腊者,韩世忠也。
其功生前为辛兴宗所冒领,数百年后,演义又归之于武松,此乃韩世忠之不幸也!
但不幸才刚刚开始。
再说“兀术兵号十万,世忠仅八千余人”,两军战于镇江至南京之长江一线。在长江南岸的黄天荡,韩夫人梁氏有过一番擂鼓助战。这一战,让曾是京口(今镇江)名妓、有姓无名的梁小姐,有了个英姿飒爽的名字:梁红玉。
梁小姐不让须眉,抢了老公韩世忠抗击金军的盖世战功,本也应该。但有了“梁红玉”,三传两传一演义,大家却又把韩世忠重创金兀术(完颜宗弼)的历史,当做小说,来轻飘飘地观赏了。
首挫金兀术者,韩世忠也。
其功生前被赵构“褒奖甚宠,拜检校少保、武成感德军节度使、神武左军都统制”;数百年后,却归之于小说演义,此乃韩世忠之不幸也!
2005年9月25日,我们拜访苏州太湖之滨的韩世忠墓,其身藏荒凉杂草丛中无人来寻、无路可寻之残态败相,更是这位大宋“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大不幸也!
71岁的张先生独守韩世忠墓园祠堂,他说:每年来此拜谒的,也就是几个自称韩世忠后裔的人,顶多再加上几个专门研究韩世忠的学者。几年前,一个大鼻子、黄头发的美国人到此来研究韩世忠的事儿,至今还让这位老人祥林嫂般倾诉:“你看,人家还知道韩世忠呢!”
老人对我们说:韩世忠墓在祠堂西北面的小山上。
沿路寻找,只见山上一座座新起的墓地。
在满是荆棘野草的山间寻觅二十多分钟,手、腿一再被带刺的荆丛穿刺,就是不见韩世忠墓!
遇到一提篮卖香的大娘,买了五元钱的香烛,问:“韩世忠墓在哪儿?”
她要带着我去寻找。
忽然,随车采访、分头寻找韩世忠墓的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喊:“小于,在这儿呢!”
还是教授的本事大,人家就是领路人。
但循声找到程教授,才发现他也没有找到,只是身边聚集着六七个老婆婆。
在婆婆们的带领下,穿过一丛又一丛荒草杂树、荆棘藤蔓,我们终于见到韩世忠墓。墓碑上写着:“宋韩蕲王墓”。
树木杂草“四面楚歌”地拥围着韩世忠墓,藤蔓搭在墓碑上,幽静凄凉。
几位婆婆一边慌忙弯腰割除墓前的野草,一边用我们半懂半不懂的吴越话,唠叨着大概是你们要买些香烛给韩世忠烧烧的话。
点上香烛,深深地向韩世忠鞠躬。还有梁红玉,尽管墓碑上没有她的名字,但她是和她的老公合葬于此的。
告别韩世忠墓,走到一个稍微开阔的地方,婆婆们拥着程民生教授要“导游费”,说:“靠山吃山嘛,没有我们的引导,你们怎么找得到呢?”
此话在理,程教授掏出二十元,权作向导费。钱拿到手,有个婆婆又问:“看韩世忠的大碑吗?”
当然得看,只是找不到呀!
在婆婆们的带领下,瞻仰韩世忠碑。
神道碑的高大出乎意料。
共有两碑,如今以水泥砖头垒在一起,恰似牌坊:左碑是“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系宋孝宗御书,字大如斗;右碑由宰相赵雄撰文,1.3万余字,漫漶不清。
此碑为江苏碑刻之冠,碑文尚有遗存。
“莫须有”刻在碑上:岳飞蒙冤,举朝文武多不敢言,唯有韩世忠却当面质问秦桧;秦桧以“莫须有”三字相答,韩世忠仰天长啸:“‘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有人劝韩世忠不要与秦桧作对,他说:“畏祸苟同,他日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被解除兵权后,韩世忠闭门谢客,阅书读经,不再言兵。他常骑毛驴,携小童一二,带着一酒壶,闷游于西湖之上。
婆婆说:七八十年前,一场台风,把神道碑吹倒了,断成几块;前些年,有人拼接上了。因为有些石块儿找不到了,这碑就成了现在这个水泥与石碑混杂在一起的“牌坊样”。
婆婆们还引领我们看“牌坊样”碑后面的碑座。
程教授和碑座比高,看上去不相上下。他叹息道:“光看这个碑座,就知道韩世忠墓园当年的恢弘,也能判断他为南宋立国立下过的不世功勋。”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英雄的功勋也不免随着时代变迁而褪色。
英雄铸造的民族精神,却是我们不该忘记的。
不幸的是,我们恰恰正在忘记。
在杭州岳飞庙,当这儿的导游讲到岳飞为什么葬在杭州时,说:“岳飞的老家在河南汤阴,那儿黄河发大水,他就坐在莲花宝盆里,漂到了杭州!”
家仇国恨,都没了。只剩下自然灾害。
北宋灭亡,缺的正是本该在天地之间回荡的英雄气。
宗泽、李纲都是文人,他们没打过仗,没指挥过什么战争。但是,当金兵来犯时,他们指挥的战争,竟然都打赢了。
为什么武将望风披靡,文人却能打胜仗?
他们是大宋帝国最早的觉醒者,他们心中激荡着一股英雄气。
人活一口气,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更是如此。
当满朝文武都认为自己打不过金人时,退却、逃跑、失败,就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了。
皇帝成了难民,这个国家还能有谁活得舒坦呢?
下面这组《大宋南迁·秋来一龙东南飞》,不只是笑看赵构夹着尾巴逃跑的黑色幽默故事,更是大宋王朝在国家倾覆之际呼唤国家英雄的命运交响曲。
一个没有正气与英雄的国家,财富越多越堕落。
怕死,是靖康前后大宋王朝上上下下的通病——徽宗、钦宗、高宗及他们的行政、军事班子内绝大部分成员,莫不如此。
怕死,只能当亡国的奴隶。
谁能比怕死的徽宗、钦宗死得更难看呢?
岳飞的死?不!
尽管他死得“莫须有”,但气壮黄河嵩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