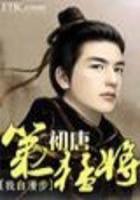兆丰大帝一天比一天感到死神的逼近。当最后一个太监也被他赶出卧房的时候,他独自仰天躺在那里,眼睛清晰地看到一个青面獠牙的小鬼在徐徐向他走来。小鬼走得那么从容,挟风带光,却是一步步向他逼近。这个小鬼像神奇的变脸人,瞬息万变,一会象一个与他有肌肤之亲的玛雅,一会儿又象一个曾被他五马分尸的大臣。
他还看到了小鬼后边有长长的队伍,队伍的最前面是他印象并不深刻的祖父祖母,他们不是来向他索命,眼神里流露出来的目光,更象对他的召唤。祖父祖母的身后是他记忆也逐渐模糊的父母大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死去也有三四十年了。
他们象是始终奔波在死亡之路上,面色憔悴得已经快没了人形,目光呆滞犹如一潭死水。他们似乎在渴望着他去拯救,但拯救的唯一办法就是他必须随他们一齐去行走在永无尽头的死亡之路。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救赎他们的生命。
他们那么执拗地看着他,召唤着他,吓得他一次次大嚷大叫。但是门外伺立的太监却听不到他失声的尖叫,因为那是他压抑在心底的悲鸣。
在墨一般的黑夜里,他感到是那样的无助和孤独。所有这一切煎熬,只能一个人忍受。他指望不上谁了。过去,还有一个皮尔卡,象同性恋人一样,为他化解所有的不能示意于人的痛苦,但是现在皮尔卡也没有了。
是,他还有皇后,还有贵妃,还有三千宫女,但他比谁都清楚,这些女人没有一个与他有过真正的爱情。他自己也没有生发过对她们的眷恋。他仅仅把她们当作发泄****的一个工具吧了。
除了元国元霸,他还有十几个皇子,六七个女儿,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些儿女除了向他索要金钱之外,他们很少象平民父子之间那样,认真地进行过心与心之间的交流,秦元国让他失望,秦元霸也让他失望,那个大公主秦元春,他就更连看一看都没兴趣了。
在最早,他还对太子秦元国十分喜爱,元国仁慈憨厚,喜爱读书。但他很快发现,由于他多年没能眷顾的这个太子,不可自拔地陷入到匪夷所思的天文学之中了。
而且秦元国率朴,只要他征询意见,秦元国就直言无忌,指责他的荒淫无度,以至后来,到是他这个做父亲的皇帝怕见这位太子。这个象他的母亲玛雅一样眉清目秀的太子,也有着他母亲一样的沉默及拒人千里的性格。
所以即便秦元国例行公事的每周来探望一次父皇,他也懒得与太子多说什么。太子的眼神似乎永远都在探究深不可测的天穹,始终处在飘离浮散的状态。在他偶尔回到现实状态的时候,却象儿童一样出言无忌,敢指责父皇,敢攻讦兆丰大帝最亲近的太监和女人。他还能指望什么亲情慰籍呢。
那个自从玛雅回到京城就给他惹事生非的秦元霸,从来就没有与他讲过那怕一句有关人情味的话。唯一能让这个秦元霸显示做为一个儿子应有的父子之情的时候,就是来向他索要王位和权利的时候。
他早已看出秦元霸骨子里的那种对任何亲情都毫不怜惜的病态的冷漠,在这个世界上,大概除了自己,谁都不会让他稍微怜悯一下。兆丰大帝从没有听他提起过他的生母玛莉,好象他是从石头里蹦出来似的。
就连兆丰大帝还曾多次打探和询问过玛莉的消息,而他却一次也没有说过。这也是自从兆丰大帝病重以后,一直没有告诉过秦元霸的原因。他不能指望秦元霸的怜惜和安慰了。
到是秦元春隔三差五进宫来向他请安。但是,早已对她心生怨怼的兆丰大帝直至现在,也没原谅她曾经让他十分恼火的丑闻。况且,这个本该安守闺房的女儿还对国政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嘲讽他施政中的种种失误。让他是可忍孰不可忍。
直到病入膏肓的现在,兆丰大帝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成了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尤其是当他每天深夜从恶梦中惊醒的时候,特别地感觉到苍凉和孤独。
他很想倾诉,很想有一个人能静静地听他诉说心底的悲哀和忧伤,他想把自己曲折坎坷、诡异莫测的一生讲给一个人听,想讲讲他作为一个正常人也必然存有的疑惑、违茫和无奈。
但是,做为一个大国的君主,一个有着三千宫女的皇帝,一个有着众多儿女的父亲,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当在恶梦中惊醒的时候,他曾把门外值班的小太监召唤进来,给他讲自己浑身的疼痛,讲任何一个老人都会有的对生活的报怨。
但是,他发现这些小太监都象傻子一样木然不语,连眼睛也不肯和他对视一下。他很快就失去了讲诉的兴致。他还曾从那些后宫佳丽中选出几个和他晚上做伴,可是这些偶尔有幸来陪驾的宫女除了莫名其妙的兴奋和久候不见皇上与她们****便生出惊慌和不解外,丝毫也没兴趣听这个老男人的絮叨。
要不忍不住瞌睡哈欠连连,要不干脆背过身去呼呼大睡。这个时候的他,既已无兴趣摸揣这些美妙的侗体,又没有精力做男女之间的那种勾当。他只有轰她们一走了之。
虽然他贵为皇帝,但是由于失去性功能,他也感觉做为一个男人的失败和耻辱。说句心里话,他都不敢冲她们发火了,由于自己的无能,他都失去了恼火的权利。而且他还担心这些宫女回去以后,传播他的无能而使他名誉彻底扫地。
后来,他还曾尝试过许多药品,包括从邻邦进口的据说非常奏效和灵验的"伟哥"之类的药品,但都不能拯救他的衰败。这就让他逐渐害怕了女人。现在,他虽然已不能指望享受男欢女爱,但他渴望与人交流。
可是,他想了好多个晚上,仍然没能想出一个合适的能帮他排遣恐惧、孤独和忧伤的倾诉对象。有一次霍达例行公事的来朝拜他,他很想让霍达坐在他的身边,诉说一下自己心中对日益严重病情的恐慌,再畅谈一次从玛雅出征以来的种种曲折。但他发现霍达一脸的漠然,顿时便象一盆水泼了过来,打消了诉说的欲望。
霍达竭力做出的恭敬之态的背后,隐含着的却是拒之千里的冷漠。回想起来,他们君臣之间,从来没有过水乳交融般的长谈,也从来没有过肝胆相照的亲近。而且,由于他多年以来就形成的戒备和疑虑,满朝的几百大臣中,他连一个可以促膝谈心的人也没有。
他们除了对他敬畏、逢迎、拍马之外,大概就是想千方百计为自己捞取一点什么好处了。他们大概也从来没敢指望与做为皇帝的他成为什么莫逆之交,掏心窝说话的朋友。
所以,每每看到索命小鬼向他徐徐走来,他只能孤独地为自己哭泣。他看见了他的许许多多早已不在世的亲属,他们都在用召唤的眼神在看着他,急切地等待着的回应。
好象只有他应了他们的呼唤,他们就可以摆脱掉阴间地狱的折磨,就可以获得自由的解脱。但他的理智还是很清楚的,他不能回应他们的召唤,一旦回应了,他就会随他们而去。他现在还不想去,活在人世还是美好的。
尽管他此时急切地想回应母亲的呼唤,想奔上前去,执起母亲那双绵软温暖的小手,但是,他现在还不想。他宁愿暂时舍弃这种睽违已久的亲情。
但是,他该为自己准备"后事"了。尽管这个念头,产生过很多次,但都被他坚决地回避了。人固有一死。这其实是他心里早已清楚的事情,但他从未认真地思考过这个必定的结局。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心存侥幸地寻找过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尽管饱学读书的他早已知道这种能让人长生不死的药物,其实就根本不会有,但他还是期望能发生奇迹。
现在看来,奇迹是不可能了,那就为自己修建一座永久的家园吧。虽然一直不愿意直面这个悲哀的话题,但不见好转的病情却一天天提醒他,该进行陵墓的修建了。否则,一旦某天早晨命归黄泉,自己都不知道要葬身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