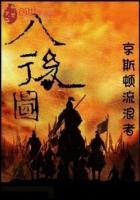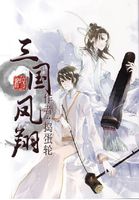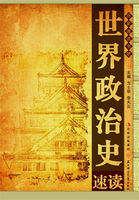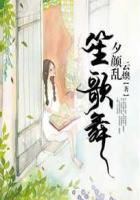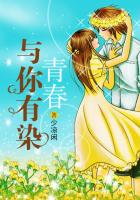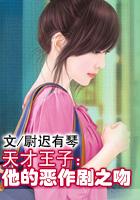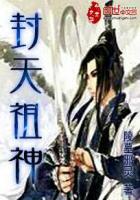义渠戎国疆域考证
周穆王西游的“焉居、禺知之平”在哪里?
焉居、禺知之平,即指焉支(即焉居)、禺氏(即禺知)族群居住的地区。“焉居”即“焉耆”“焉支”,秦时写作“义渠(岑仲勉说)”,称“义渠戎”。“禺知”即禺氏,春秋战国称“乌氏戎”。
义渠国是商、周时期的西戎古国,为义渠戎所建。义渠国君于周初曾入朝周王。《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十年,季历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逸周书·王会解》载:正北方义渠(贡)以兹白,兹白者若白马,锯牙,食虎豹。《括地志》原州条引《史记·秦本纪·正义》载:“原、宁、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义渠戎国辖境包括原、宁、庆三州,以今地言之,即今甘肃镇原、宁县、庆阳一带。《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这块土地,本属先周“焉居”之地,
后属义渠戎国。
春秋时期,《史记·匈奴列传》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座落于该境域内的山脉,古称陇山,即今六盘山。六盘山以西分布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分布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即位于岐山之北的义渠戎国,位于梁山之北的大荔戎国(铁镰山南、渭河以北、洛水古道以东、黄河西岸),位于泾水之北的乌氏戎国,位于漆水之北的朐衍戎国。《后汉书?西羌传》载:“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獠、圭、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由上可知,东周时期义渠戎国境域由商周时期的今甘肃宁县、镇原、庆阳扩展到泾水之北的今宁夏固原一带(泾北有义渠之戎)。
战国时期,《后汉书·西羌传》载:秦惠王“伐义渠,取郁郅”,可见郁郅原系义渠戎地。《前汉书·地理志》载: “北地郡······郁郅:泥水出北蛮夷中,有牧师苑官。”可见郁郅属北地郡之一县。“郁”“禺”同音,“居”“耆”“知”“支”“郅”古音近似,郁郅即“禺知”。岑仲勉认为,“禺知”即月氏(乌氏、虞氏),由此可知,西周的“禺氏”地区也即春秋战国的“乌氏”地区。所以,西周的“禺知”“乌氏”,以地名而言,即《山海经》中的“郁郅”,汉代有郁郅县可证。汉置郁郅县,在今甘肃庆阳、宁夏固原地区。所以,今宁夏固原、甘肃镇原、庆阳一带,古属郁郅(禺知、乌氏)境域。关于汉代乌氏地区的辖境,《汉书·地理志》载:“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县二十一:高平、复累、安俾、抚夷、朝那、泾阳、临泾、卤 、乌氏、阴密、安定、参巒 、三水、阴槃、安武、祖历,爰得、眴卷、彭阳、鹑阴、月氏道。”安定郡条下的“月氏道”,居延漢簡“驛置道里簿”说:“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清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说:“月氏道,疑即在盐茶厅,以处月氏降者”,则月氏道在今宁夏中卫市海原县。清《隆德县志》说“汉月支(氏)道”在今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境。从以上县名书写排列顺序中,除郡治高平按“修志凡例”排在第一位外,其它县名的排列顺序大体上遵循了一条按照地理方位毗邻排列县名顺序的原则。以今宁夏境内已考定地理方位的县名言之,对汉代乌氏县来说,朝那、泾阳在其南,参巒、三水在其北。从汉代乌氏县的这个地理方位和周穆王进入“焉居、禺知”地区后便在黄河岸边活动的情况看:西周“焉居、禺知之平”,主要指今宁夏西南部的河套平原,战国后期这里曾为义渠戎国之地,大致包括了今宁夏固原、同心、海原、中卫、中宁及甘肃镇原、庆阳、靖远黄河内岸的陇西地区。这块山川,是周族先民走出青藏高原首达黄河岸边的图腾神山——崇吾之山(今宁夏中卫香山)的所在地。
义渠戎国的兴亡
义渠国存在于商、周时期。
殷墟甲骨卜辞载:其乎戍禦羌方于義沮,羌方不喪衆(《合集》27972)。義沮即义渠。
《竹书纪年》载,商帝武乙(前1144年—前1110年)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 。由此可见,义渠戎国在商帝武乙(约公元前12世纪)年间,就与姬周王国共存。
《逸周书》载:“昔者义渠氏有两子,异母皆重,君疾,大臣分党而争,义渠以亡”。 商帝武乙乘义渠内讧及国王生病,俘获了义渠国王。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疏证辑校 》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
《后汉书·西羌传》载:“周遂凌迟,戎逼诸夏",“泾北有义渠之戎。
《逸周书·史记解》说:“嬖子两重者亡。昔者义渠氏有两子,异母,皆重。君疾,大臣分党而争,义渠以亡”。义渠国王被俘获,其族仍存。
春秋战国时期,义渠已成为秦境西北的大国,与秦抗争不断。
秦穆公时期(前659一前621年) ,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史记·匈奴列传》)。
春秋战国时期,义渠已成秦国西北部的一个大国。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后汉书·西羌传》)。
秦厉共公六年(公元前471年) 义渠来赂,繇诸乞援(《史记·六国年表》)。
周贞王八年(前461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至是中国无戎寇,唯遗义渠种焉(《后汉书.西羌传》)。
秦厉共公 三十三年(前444年),伐义渠,虏其王(《史记·秦本纪》)。《后汉书.西羌传》载:至贞王二十五年(前444年),秦伐义渠,虏其王。后十四年,义渠复侵至渭阴。后百年许,义渠败秦师于洛。后四年,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后八年,秦伐义渠,取郁郅。后二年,义渠败秦师于李伯。
《史记·张仪传》载:义渠君朝于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之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以烧掇焚杅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秀千纯,妇女百人以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耶!”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
秦惠王三年(前335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后汉书·西羌传》)。
(秦惠王)七年(前331年),义渠内乱,秦遣庶长操将兵定之(《史记·六国年表》)。
秦躁公十三年(前430年),义渠来伐,至渭南(《史记·秦本纪》)。
秦惠文君十一年(前327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史记·秦本纪》)。
后五年(公元前320年),惠王北游戎地至北河(史记·秦本纪)。
后六年,伐义渠,取郁邽。(《后汉书·西羌传》)。
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年),义渠君之魏,公孙衍谓义渠君曰:“道远,臣 不得复过 矣,请谒事情”……其后五国伐秦(《战国策》)。
后九年(前316年),义渠君闻秦有六国之师,来袭。与战于李伯之下,秦师败绩(《秦集史》)。
后十年(公元前315年),伐义渠,得徒泾,取二十五城(《史记·秦本纪》《后汉书·西羌传》)。魏有西河、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之,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史记·匈奴列传》)。
武王元年(前310年),伐义渠(《史记·秦本纪》)。
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年),及昭(襄)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后汉书·西羌传》)。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后汉书·西羌传》)。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距胡(《史记·匈奴列传》)。
秦灭义渠戎后,置其地为县。《汉书·地理志》载:“北地郡,秦置……义渠道,莽曰义沟。弋居,有盐官。大要,廉。卑移山在西北。莽曰西河亭。”秦北地郡置有“义渠道”,王莽改名“义沟”。《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县“有蛮夷曰道”,《括地志》载 “县有蛮夷日道,故曰严道”,《后汉书·百官志》载 “凡县主蛮夷曰道”,李贤注《后汉书·马援列传》载 “县管蛮夷曰道”。 秦“义渠道”显为管理“义渠戎”的机构。
义渠戎国与城市文明
义渠戎国灭亡了,但义渠戎国对河套地区开发建设的巨大贡献不应该被湮埋。因为这关系到对先秦时期河套戎狄文明发展程度的认识。
从义渠戎国的疆域来看,秦灭义渠国,夺取了 “陇西、北地、上郡”。上述三郡,约当今宁夏、甘肃、陕北的河套地区及陇山东西之地,皆属义渠国疆域,今宁夏全境属之。
从义渠戎国的存在时间看,义渠戎国从商代武乙年间(约前12世纪)有国至秦昭王时代灭亡,在河套地区存在800多年,与周朝相始终,自有其存在地理环境与经济基础。
城市建设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从义渠戎国的城市建设看,春秋末期,义渠戎社会发展很快,由游牧转向了农耕,已经筑城定居,《后汉书·西羌传》说:“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战国时期,义渠戎已是秦境西北定居城市的农牧强国,与秦战和不断。《史记·匈奴列传》载“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义渠戎国有多少城市史籍缺载,但仅从秦惠王夺取的“义渠二十五城”来看,说明义渠戎国城市林立,其国民已建城而居,这就不是一般的发展水平,他们至低是过着农牧并举的生活。
在宁夏地区,应有义渠戎国遗留下的城郭遗址,过去不大注意罢了。故义渠戎国(今宁夏及甘肃庆阳地区)境内有许多城郭,为义渠戎所筑。在秦惠王攻取的义渠戎国的二十五城中,其中许多城郭当沿袭为秦汉及后世之城郭。今宁夏境内的一些城郭遗迹、遗址,应属春秋时期的义渠戎始筑。城郭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义渠戎国不单纯是游牧民族、游牧经济,义渠戎国的社会经济、社会形态已相当发达。宁夏平原的开发建设亦并非始于秦汉,至迟应始于春秋时期的义渠戎国。
义渠戎与秦渠开挖
水利建设是人类从事灌溉农业的必备条件。中国开渠挖沟,引黄灌溉始于史前时代。
大禹治水时,农耕族群就已懂得在黄河上分渠引水,发展灌溉农业。《史记·河渠书》载:於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集解”说:厮,分也。“索隐”说:厮,即分其流泄其怒是也。二渠,其一即漯川,其二王莽时遂空也。
大禹时代即已种植水稻。《史记·五帝本纪》载:(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诗经·闭宫》说:后稷 “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后稷是周的始祖,名弃,尧举其为“农师”,舜命其为管理农业的“稷”官。在尧、舜、禹时代,就已发展了水稻种植。水稻种植离不开田间沟渠,引水灌溉,这和《史记·河渠书》说大禹时代已从黄河上分渠引水是完全一致的。
西周时代,种稻普遍,开挖沟渠,灌溉和排水的沟渠配套已成为农官的基本职能。《周礼·稻人》载:稻人,掌稼下地。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泻水。
春秋战国时期,秦、魏等国早就发展了灌溉农业。各国开渠引江水、河水、溪水发展灌溉农业习以为常。
西门豹引漳水溉邺。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史记·河渠书》)。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史记·滑稽列传》)。
郑国渠。秦引引泾水灌溉关中沃野。《史记·河渠书》载: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闲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 :“始臣为闲,然渠成亦秦之利也 。”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泾水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战国末年秦国穿山凿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 300 余里,灌溉关中沃野,号称4万顷,秦以富强。
义渠戎与秦、魏毗邻,时战时和。秦、魏早就开渠引水,受益巨大。对于在河套地区定居800余年、“筑城郭以自守”的义渠戎来说,不会不知道开挖渠道,引黄河水灌溉农田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河套处于我国的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量少,蒸发量大,如果没有灌溉条件,农作物难以生长,既然宁夏河套的农业垦殖起于秦代,而秦代水利工程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当然会利用黄河水开渠灌田。义渠戎开挖沟渠,引黄灌溉当无疑问。
河西走廊引水种稻始于秦汉之前。《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閒,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都廣之野为后稷葬所,在今河西走廊额济纳旗。都廣之野生产“膏稻(水稻)”,也就是说,今额济纳旗在《山海经》时代即已种植水稻,是中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山海经》成书于秦汉之前,秦汉之前河西走廊即已种植水稻,则河西走廊稻作区开挖沟渠,引水灌排自在秦汉之前。
西汉时期,司马迁到处漫游。司马迁对所到之地的河渠建设很关注,对其引水渠道都有细致的观察记载,例如,在四川,他观察过都江堰,记载到:“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欍,百姓飨其利。”在他所到之地,他还写到:“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史记·河渠书》)。”司马迁到过宁夏平原,他说:余尝西至空桐(史记·五帝本纪),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史记·河渠书),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长城亭障,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利矣(《史记·蒙恬传》)。以上司马迁所至之地,有空桐(包括固原地区)、朔方(包括宁夏)、行观蒙恬所为秦长城亭障(宁夏、内蒙秦皇长城位于宁蒙河套平原黄河内岸),也就是说,司马迁“行观蒙恬所为秦长城亭障”肯定到过宁夏平原。司马迁所说的“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其数“以万亿计”的灌溉田畴渠道,必然包括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渠道。应该说,司马迁所过所见“万亿计”“ 莫足数”的引水渠道,从黄河水利资源利用来说,宁夏引黄渠道肯定多于周边地区,为数不少。这些“万亿计”“ 莫足数”的引水渠道,肯定也不全是汉武帝、司马迁时代新开挖的,多数当是春秋战国乃至其前遗存下来的古渠。因为这一地区早就是半农半牧地区或农耕地区,当地民众的智力、生产生活必需及引水技能不会落后到守着黄河不用或不会用!更不会落后到等到汉武帝时代才学会开挖渠道引黄灌溉种植粮食等农作物。
宁夏在义渠戎时代即已引黄灌溉,“秦渠”为秦义渠戎开挖,成渠于战国秦时代。“义渠”一名为羌语音译。据藏学大家任乃强先生研究,羌语中,适于耕种的河谷叫戎(Rong译字一作绒)。羌族居住在陇西的,既乐于从事农业,就必然入居河谷,并发展成为定居族落,所以牧民称之"戎"(这样的地名,西藏和西康还保存得很多。如金川叫"甲戎",瞻对叫"捏绒",得荣叫"德戎",盐井叫"察瓦戎",九龙县叫"吉乌绒"之类,都是农耕河谷之义)。殷代人因其音而造戎字,以与羌族相区别。戎字从戈,戈为车战用的钢铁武器。古羌族用石器为矛,无戈。居住在关陇间的,因为承受汉文化,才用戈。所以,就造字取义来说,"戎"的称呼当是在殷以后才有的,以前只称“朔方”、“ 熏育”或“玁狁”。因为那时还是牧民部落,属羌类的原故。简言之:羌与戎的区别,就是牧与农的区别,华族化与非华族化的区别。“渠”字在羌语中是河水的意思。汉语中“渠”、“沟”是指人工开凿或自然形成的水道。“义渠戎”即开挖渠沟,是引河水灌溉的戎族。王莽将义渠改为义沟,显然是示意义渠有引黄渠道。义渠戎之所以能够在河套地区延续居住800年,并且“筑城郭以自守”,正是因为他们有开挖渠沟,引河水灌溉的定居农业。否则,“义渠戎”不可能在河套地区延续居住800年,更不可能在其国内普遍“筑城郭以自守”。秦灭义渠戎后在此地置秦县,此地之渠后世称之为“秦渠”。
汉代官员早就知道宁夏秦渠等引黄灌溉开挖于汉武帝之前。《后汉书·西羌传》载:顺帝永建四年 ,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曰 :“臣闻子孙以奉祖为孝,君上以安民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汤﹑武也。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髃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书奏,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 。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 虞诩说雍州之域“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即指宁夏河套平原有龟兹盐池(今宁夏盐池在内)。虞诩说得很清楚,自商周以来,因为包括宁夏在内的“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的禹贡雍州之域沃野千里,“北阻山河”“ 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所以“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包括宁夏),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所谓“皆为此也”,说白了,汉武帝之所以争夺宁夏等河套平原,就是此地早就具有“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的引黄灌溉(激河浚渠)渠系,粮食来源充足。
研究宁夏的先秦史,自商周至战国,义渠戎史是其主线。撂开义渠戎史而说宁夏商周之后的先秦史,就是空缺了800年的宁夏先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