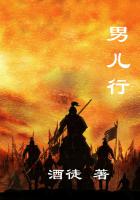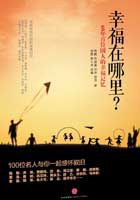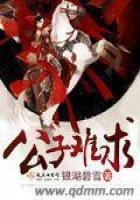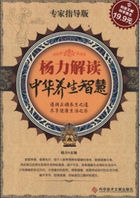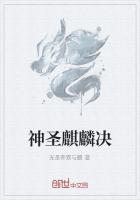序:《延笃传》见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四,列传五十四,全文计一千零一十一字。蔚宗为文,“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见《宋书·范晔传》卷六十九引《狱中与诸甥侄书》)读《延笃传》,乃知其言非虚语也。
《后汉书》旧有唐章怀太子李贤注,虽时有可取,然未为精当。清末长沙王益吾太史撰《后汉书集解》,博采众家之说,为时所称,然以今视之,疏漏尚多,犹未尽善。
余慕延笃其人,喜读其传,久之有所得,今为笺证,以补前人之不足,并就教于识者方家。
延[1]笃字叔坚[2],南阳犨[3]人也。少从颖川唐溪典[4]受《左氏传》,旬日能讽之,[5]典深敬焉。又从马融[6]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
笺证:
[1]延,周王族,见《左传·昭二十二年》。一说,吴公子季札,封于延陵,后世以延为姓,见《史记·吴世家》。
[2]《太平御览》卷四五二引谢承《后汉书》:“延笃,字叔固。”谢承,三国时吴人,避孙坚讳,以固为坚。
[3]犨,始见《左传·昭元年》:“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犫。”《汉书·地理志》南阳郡有犨县。《续汉书·郡国志》作犫。故城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五十五里。
[4]章怀注:“《先贤行状》曰:‘典字季度,为西鄂长。’《风俗通》曰:‘吴夫槩王奔楚,封堂溪,因以为氏。’典为五官中郎将。‘唐’与‘堂’同也。”《后汉书·蔡邕传》卷六十:“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是为汉末硕儒。
[5]章怀注:“先贤行状曰:‘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唐溪典以废笺记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讽之,粮尽辞归。典曰:‘卿欲写传,何故辞归?’笃曰:‘已讽之矣。’典闻之叹曰:‘嗟乎延生!虽复端木闻一知二,未足为喻。若使尼父更起于洙、泗,君当编名七十,与游、夏争匹也。’”
[6]马融,东汉巨儒,郑玄、卢植俱师事之。延笃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百家之言”,然马融矜全情薄,安存虑深,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颇为正直所羞。故师未必贤于弟子也。
举孝廉,为平阳侯相。[1]到官,表龚遂[2]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间。以师丧[3]弃官奔赴,五府并辟不就。
笺证:
[1]中兴功臣冯勤中子顺,尚明帝女平阳长公主刘奴,章帝建初八年,以顺中子奋袭主爵为平阳侯,薨,无子。和帝永元七年,封奋兄劲为平阳侯,奉公主之祀。劲薨,子卯嗣,安帝延光中为侍中,薨,子留嗣。事见《后汉书·冯勤传》卷二六。如冯留嗣爵在延光后二十年,正值顺帝末。延笃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必在桓帝之前,即顺帝时,故知延笃所相之平阳侯当为冯留。又,《后汉书·皇后纪》(卷十):“(明帝)皇女奴,三年封平阳公主,适大鸿胪冯顺。”章怀注:“平阳,县,属河东郡。”误。《解集》引钱大昕说:“此山阳之南平阳,非河东之平阳。”此说是也。河东郡之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境,亦非袭遂之故乡。山阳郡之南平阳,在今山东邹县地。
[2]袭遂,山阳南平阳人。事昌邑,则涕泣谏诤,守渤海,则卖刀买牛,贤臣也。事见《汉书·袭遂传》卷八九。
[3]延笃之师堂溪典,卒于笃之后,马融卒于桓帝延熹九年,仅在笃卒之前一年,故此师非二人,明矣。然笃别有师,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京兆尹延笃受《左氏》于贾逵之孙伯升,因而注之。”贾逵生于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卒于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其孙伯升如少于其祖五十岁,则当生于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延笃卒于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如其终年六十岁,则当生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少于伯升二十七岁,伯升为其师可信。又延笃为平阳侯相当在顺帝中期至末期,顺帝末为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其时伯升已六十四岁,卒于此时,亦为常理。故此处所言之师,当为传《左氏传》之贾逵之孙伯升。
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1]稍迁侍中。帝数问政事,笃诡辞密对,[2]动依典义。[3]迁左冯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宽仁,忧恤民黎,擢用长者,与参政事,郡中欢爱,三辅咨嗟焉。[4]先是陈留边凤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为之语曰:“前有赵张三王,后有边延二君”[5]。
笺证:
[1]“著作东观”,即于东观参与撰述国史之意。按东汉修史可考者约有七次,此为第四次,见《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
[2]章怀注:“《谷梁传》曰:‘故士造辟而言,诡辞而出。’范宁注云:‘辟,君也,诡辞而出,不以实告人也。’”按语出《谷梁传》文公六年。此说可取。出而诡辞,守机密也。
[3]《北堂书钞》卷五十八“国有疑常问得失”条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为侍中,自在机密,常见进纳,上数问政事得失,恒以经义古典,开谏帷幄,言不宣外。”《太平御览》卷四五二引文略同。
[4]《北堂书钞》卷七六“正身率下”条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迁京兆尹,正身率下”;“劝农桑遂增户口”条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传》:“迁京兆尹,劝民农桑,遂增户口”;“忧官如家恤民如子”条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迁京兆尹,忧官如家,恤民如子”;“三辅咨其政教”条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为京兆尹,三辅咨其政教”;“邻郡归之”条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迁京兆尹,劝农桑,增户口,谷食丰饶,邻郡老少归之。”《文选》卷五三陆机《辨亡论》(下)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迁京兆尹,恤民如子。”
[5]《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赞》卷七六:“自孝武置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而吏民为之语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赵张,赵广汉、张敞也;三王,王遵、王章、王骏也。皆京兆尹之能者。边指边凤,《后汉书》无传。《循吏列传序》卷七六:“边凤、延笃先后为京兆尹,时人以辈前世赵、张”。
时皇子有疾,[1]下郡县出珍药,而大将军梁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2]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笃以病免归,教授家巷。[3]
笺证:
[1]《太平御览》卷九八八引《文士传》:“延笃为京兆尹,桓帝时,梁冀专政,时皇太子疾,诏书发京兆,出牛黄。冀遣诸生赍书,持牛黄,诣笃卖。笃以为诈,论杀之。”文略有不同。延笃于桓帝元嘉元年著作东观,稍迁侍中,再迁左冯翊,又徙京兆尹,其间当有数年之久。如徙京兆尹在著作东观之后四、五年,则始任京兆尹当在永兴二年。梁冀于顺帝永和六年初任大将军,至桓帝延熹二年败死。故皇子有疾,下郡县求珍药一事,应为永兴二年至延熹二年间事。其时之皇子当为桓帝子无疑。按《后汉书·皇后纪》卷十,桓帝梁皇后,梁冀妹,“后既无子,潜怀怨忌,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桓帝邓皇后亦为梁氏所进,并无子。此处所述之皇子,或为梁邓二后所生,诞而不育,史载有缺,其余宫人所生子,恐梁冀不为求珍药矣。
[2]章怀注:“吴普《本草》曰:‘牛黄味苦,无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胆中,如鸡子黄。’《神农本草》曰:‘疗惊痫,除邪逐鬼。’”按《太平御览》卷九八八引《吴氏本草经》曰:“牛黄,牛出入鸣吼者有之。夜视有光走牛角中,死,其胆中如鸡子黄。”文稍异。吴普,华陀弟子。《三国志·魏书·华陀传》卷二九:“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陀学。普依准陀治,多所全济。”《后汉书·方术传》卷六四引注《陀别传》:“吴普从陀学,微得其方。”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七:“梁有华陀弟子吴普《本草》六卷,亡。”《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吴氏本草因》六卷,吴普撰。今书已亡,清人有孙星衍、周澄之、顾观光、黄奭、姜国伊、王仁俊、叶志诜辑本多种。
[3]《集解》引惠栋曰:“按《汉中常侍吉成侯州辅碑》有延笃题名。又笃撰孙程等《传》,皆叙其所承本世,曲为文饰,是笃乃阉尹支党,故得不罹梁氏之祸。不然,冀之横暴,睚眦触死,岂有显刑梁使而得自全者乎?史家所记,盖非其实。”
《汉中常侍吉成侯州辅碑》见宋洪适《隶释》卷十七,称州辅“遭孝质无嗣,乃定册帷幕,援立圣主,有安社稷之勋”。州辅,《后汉书》无传,仅一见于《宦者列传·曹腾传》卷七八:“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以定策功,皆封亭侯。”此与《州辅碑》所记颇相一致。故知州辅之功即在拥立桓帝也。顺桓之世,梁冀专权,“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敢有所亲豫。”(《后汉书·梁冀传》卷三四)其时,与梁氏集团对立者为朝中正直大臣一派,尤以李固、杜乔为中坚。故终桓帝之世,其政治势力大别有三:一为梁氏外戚集团;一为李杜等大臣;一为曹腾等宦官。初时议立桓帝,曹腾辈曾与梁氏同谋。但梁冀执政,残害李杜,皇权下移,宦官失势。以故宦官转而支持大臣,以图合力拥帝,收回政柄。《曹腾传》载:“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颖川堂溪典等。”李固、杜乔与虞放等辈,实即党人之先声。延笃自属此派,曹腾所进之堂溪典即为其师,此尤可证。州辅为曹腾之佐,卒于桓帝永寿二年,正此时也。遂有延笃等人列名碑阴之事,诚不足怪也。曹腾、州辅虽身为宦官,并无劣迹,其后推倒梁冀,桓帝即借宦官之力,非宦官尽为梁党,明矣。
又,惠栋指斥“笃撰孙程等《传》,皆叙其所承本世,曲为文饰”,乃袭用《后汉书·宦者孙程传》卷七八章怀注语。章怀注原指《东观汉记》述孙程为“卫康叔之胄孙林父之后。”按孙林父即孙文子,春秋卫献公、殇公时人,先与宁惠子攻出献公于齐,立殇公。复与宁喜争宠相恶,孙林父奔晋,再拥立献公。《春秋》(襄二十六年)斥之为“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孙林父实一反复无常之小人。《汉书·古今人表》卷二十以孙林父入于下之上,即九品人等之第七,除大奸巨憝外已无可下。自来史家未曾予孙林父任何佳评。使宦者孙程为孙林父之后,令其认此祖宗,实不知何荣光之有?惠氏之不审史实,无乃太过乎?另,延笃入东观著作,在桓帝元嘉元年,为东汉修史之第四次,据《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载:“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此次修史规模较大,主其事者为太中大夫边韶,参与者有崔寔、朱穆、曹寿、延笃。延笃其时资历尚浅,故列名最后。所著前后计百十有四篇,焉知《孙程传》必出自延笃之手?即使出自延笃之手,又焉能以己意为之?今《东观汉记》早佚,检《孙程传》佚文,亦并无谀词,即使《孙程传》为延笃所撰,又何罪之有?惠氏以列名《州辅碑阴》及或许撰《孙程传》之两事,即坐以“阉尹支党”,实厚诬古人之甚者。《延笃传》下文明载,延熹九年党锢之祸起,“后遭党事禁锢”,可见延笃乃党人之中坚,宦官之目刺。惠氏弃此显证于不顾,徒炫其稍知列名碑阴及著作东观,穿凿附会,妄加罪名,论史者不当慎哉!
又,惠氏以“笃乃阉尹支党,故得不罹梁氏之祸。不然,冀之横暴,睚眦触死,岂有显刑梁使而得自全者乎?”惠氏此说,实大谬之奇者。虽梁冀横暴恣绝,乃并世非无不惧权奸者。延笃以磅礴正气,斩梁冀千里求利之使,可谓大快人心,读史至此,郁气为之一舒。惠氏竟以“显刑梁使而得自全”罪之,真不知其欲古人何去何从?且必以天下正人均遭梁冀屠尽,始为快乎?且:“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笃以病免归,教授家巷。”史明载梁冀诛求,有司谄谀,延笃以此失官,危乎哉避退乡里,又焉得谓自全乎?
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笃乃论之曰:“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1]”夫人二致[2]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复,枝叶之有本根也。[3]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4]“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5]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6]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从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7]
笺证:
[1]汉世末季,于仁孝之辩,似曾论争甚烈。沿至三国时,争尚未息,故魏陈思王有《仁孝论》之著。佚文见《太平御览》卷四一九引:“且禽兽悉知爱其母,知其孝也。惟白虎、麒麟称仁兽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乱也。孝者施近,仁者及远。”曹植之说与延笃之论,颇相类近。其时残乱迭起,国事蜩螗,人或欲事亲以归德,或欲施物以济功,所见不同,所论有异,或有已也。惜史料湮没,难考其详耳。
[2]章怀注:“二致,仁、孝也。《易·系辞》曰:‘殊涂而同归,百虑而一致’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八篇上)释人字:“按人耦犹言尔我,亲密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人有耦,方有仁,故仁即儒家理想中人与人关系之准则也。此准则,概而言之,即仁者爱人,反之,则为不仁。人与人,最亲者莫如父母兄弟,故孝悌为仁之本。仁与孝,近视之则一,远观之则二,“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故无须较铢两,定前后。此延笃所论之大旨也。
[3]《太平御览》卷四一九引延笃《仁孝论》:“夫仁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仁”下无“人”字,“根”下无“也”字。
[4]语见《孝经·三才章第七》。
[5]语见《论语·学而》。
[6]《太平御览》卷四一九引延笃《仁孝论》:“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犹心体充实为先。”文稍异。
[7]仁孝同质而生,有纯体之者,即仁孝均为至善,如虞舜、颜回是也。有偏体之者,大孝如曾、闵,仁功如管仲,各从其称。故建功业者,施物济时,彪炳史册,论德为先。然事亲者德归于己,近取诸身,实枝叶之有本根也。故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所施不同,事少两兼,必舍此而就彼也。延笃之论,精义在此。
前越巂太守李文德[1]素善于笃,时在京师,谓公卿曰:“延叔坚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进之。笃闻,乃为书止文德曰:“夫道之将废,所谓命也。[2]流闻乃欲相为求还东观,[3]来命虽笃,所未敢当。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4]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5]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谥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6]虽渐离击筑,旁若无人,[7]高凤读书,不知暴雨,[8]方之于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脩[9]以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谄,下交不黩,[10]从此而殁,下见先君远祖,可不惭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11]。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12]
笺证:
[1]李文德,《后汉书》只此一见。《州辅碑阴》有处士李文德,或即此人。
[2]《论语·宪问》:“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3]求还东观者,重参朝政也。
[4]《全后汉文》卷六一,严可均据《太平御览》卷四三一于此下补:“吾食赤乌之麸麦,饮化益之玄醴,折张骞大苑之蒜,歃晋国郇瑕氏之盐。”文不类。
[5]投闲,不废时之隙也。《太平御览》卷三九一引《东观汉记·桓荣传》:“投闲辄诵诗”。
[6]《诗》、《书》之乐有如此,非通人不识也。
[7]《史记·刺客列传》卷八六:“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8]《后汉书·逸民高凤传》卷八三:“高凤字文通,南阳叶人也。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
[9]章怀注:“束脩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此说是也。然亦谓谨饰自约。《后汉书·卓茂传》卷二五:“时光武初即位,先访求茂,茂诣河阳谒见。乃下诏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
[10]黩同渎。《易·系辞下》:“君子上交不诌,下交不渎。”延笃,真君子也。
[11]章怀注:“《史记》,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养由基怒,释弓搤剑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诎右也。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气衰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者百发尽息。’此言羿者,盖以俱善射而称之焉。”此注未得其实。善止者,谓自束修以来,所行无所惭赧,今当思止步,以求完节。如不善止,犹思干禄求进,则必为当路所忌,而贻士林之羞。有如善射者,当量力而止也。
[12]此复李文德书,延笃明志之作。《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知学优则仕,未知仕优则学,愚儒也。延叔坚知事不可为,而遨游艺苑,驰鹜书林,渴饮河海,志镂金石,此其中纷纷欣欣之乐,适足以使人忘世之有人,己之有躯,终至舆盖天地,幻化鸿蒙矣。延笃,真古今第一高士也。
后遭党事禁锢,[1]永康元年,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2]
笺证:
[1]《后汉书·孝桓帝纪》卷七:延熹九年,“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书名王府。”天运汹蒙,阴阳难测,政势如潮,人其奈何!虽如延笃之谦退,亦不能免,悲夫!
[2]周寿昌《后汉书注补正》卷六:“《延笃传》,乡里图其形于屈原庙。按笃为南阳人,楚汉之际,南阳属楚,故有屈原庙也。”此说可信。
笃论解经传,多所驳正,后儒服虔等以为折中。[1]所著诗、论、铭、书、应讯[2]、表、教令,凡二十篇云。[3]
笺证:
[1]服虔,见《后汉书·儒林列传》卷七九,作《春秋左氏传解》。
[2]章怀注:“‘讯’,问也,盖《答客难》之类。”
[3]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然古今为注解者绝省,音义亦希。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隋书·经籍志》有《战国策论》一卷,汉京兆尹延笃撰。《两唐书》同。《颜氏家训·书证篇》有延笃《战国策音义》,当是一书。又,《隋书·经籍志》有《延笃集》一卷,《两唐书》均作二卷。《全后汉文》卷六一录延笃之文,除《后汉书》本传所载《仁孝论》、《与李文德书》外,尚有《答张奂书》、《与张奂书》、《与高彪书》、《与段纪明书》、《贻刘祐书》等残篇。惜哉,其文之不传也。
(原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