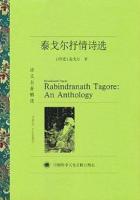“葫芦娃,葫芦娃,一颗藤上七个瓜……”手机响起时,我还在床上睡大觉。用被子把头盖住,并把有缝隙的地儿,都压得严严实实。但不知道是谁那么有毅力,让手机响了一遍又一遍,将我的瞌睡虫一点点的从身体里驱除。
无奈之下,只好伸出一只手,寻着声音的源头,抓起手机对着里面一阵怒吼:“大清早的不睡觉,听手机彩铃不要钱还是怎么着啊!”
正常人在我强大的起床气爆发之后,第一反应便是道歉,只有林青,能淡定的过滤掉我抓狂的情绪,直奔重点,“杨义出事了。”
“那小子能有什么事儿呀,挂了啊,睡醒再说。”我打了个哈欠,准备唤回那些还未走远的瞌睡虫,再顺道找周公谈谈心。
“周雪儿劈腿了。”林青淡然的说道。“劈腿”两字,像颗重磅炸弹,落在我犯困的心房之上,直接炸得我睡意全无,“什么时候的事?”
“刚刚。”听着林青淡定的回答,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起,开起免提,边换衣服,边冲电话嚷道:“小白杨知道吗?控制住情绪,别私自行动,操上家伙,在老地方等,听我指令。”
“干嘛?”
“捉奸!”我响亮的答出这个振奋人心的词语,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仿佛都充满了活力,让我心潮澎湃,“捉奸”这种事,还能被我遇到,尤其是替别人“捉奸”,真是欢乐啊。这跟痘痘长在别人脸上最让人开心,一个道理。
但被劈腿的悲剧男是杨义,是我的好朋友,又让我因“捉奸”而产生的所有兴奋,瞬间变成了愧疚,却又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杨义绝对有理由认为我是幸灾乐祸,不厚道。
好吧,我承认,我幸灾乐祸,但我很厚道。
相机、录音笔、口罩……“捉奸”装备一个都不能少,一股脑的扔进背包,向着“奸情”出发了。
出门打了辆出租车,直奔“时光”咖啡店。
A市这几年发展得不错,高楼林立,可交通却出了名的堵。市政建设每年也都在做做样子,表面上是多修路,缓解交通压力,可在我看来,也就是换着花样堵呗。
出租车在马路上缓慢的行驶着,我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却又无可奈何。“捉奸”这种技术活,讲究时效性,就像做菜讲究火候一样。你要去早了,主角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剧情,你要去晚了,就只能看彩蛋了,精彩演出只能等到看重播,可这种重播,是可遇不可求的。
眼看着过了路口就到了,却被堵在了路口。
“师傅,我能不能在这下车,我有急事儿。”我着急的向司机师傅发出求助请求。
“妹子,这不能下客,我们在中间这根道上,两边都是车,瞧前面路口还站着交警呢,可不敢让你下车。”我的下车请求被司机师傅驳回。
“师傅,我真有急事儿,晚了就来不及了,你看交警也没看咱们这边,我火速下车,一定不给您添麻烦。”我试着劝说司机师傅可以发发善心,并在心底默默许下心愿,交警看不到这边,交警看不到这边。
“妹子,真的不行,而且在这马路中间下车,也很危险。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你的父母想一想,这安全最重要,宁等1分钟,不急1秒钟,好事不在忙上,咱在等等,要是因为急了那1秒钟,而发生不好的事情,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
坐在车里,远远的看着“时光“咖啡的大招牌,仿佛那招牌上坐着一只煮熟的鸭子,在司机师傅长达3分钟并且还在继续的劝慰之下,飞走了。
我本想跟司机师傅说我其实是短跑运动员,下车之后,能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马路边的安全地带。想想还是算了,司机师傅苦口婆心,语重心肠的劝说着,纵然是失足青年,迷途羔羊,也应该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师傅,我不下车了。“我想如果我不及时的表明不下车的决心,司机师傅应该还会劝说下去。
“这才对嘛,妹子。“司机师傅转头看着我,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
我又看了看手表,已经堵了10分钟了,估计“奸情“应该谢幕了吧。我无力的倚靠在出租车后座的白布座椅上,拿出手机给林青发了条短信,简单的说了下堵车的情况。
林青回复我说,不着急,等着你。
我立马原地满状态复活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奸情“还没散场,好戏还在。在我激动之时,车流终于动了,司机师傅一脚油门儿,2分钟不到,直接将我拉到了”时光“咖啡大门口。“捉奸”这种事儿,就得天时、地利、人和,正好全凑齐了,我觉得是天在助我,不,准确的说,应该是天在助杨义那小子。
下了车,我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时光”。见林青与杨义二人正悠闲的喝着咖啡。这不该是“捉奸”的节奏啊。
“时光”是林青开的一家咖啡店,是我、林青、杨义三人的根据地。
说到林青,那可真真儿是出生豪门,俗称名媛,出得盛宴,入得party,在A市的名流圈儿里,那是排得上号,叫得上名儿的,一头深蓝色短发,猛的一看像是黑色,放阳光下仔细一看,每一根发丝都泛着蓝色的亮光,妩媚又张扬,冷艳又性感,那叫一个漂亮。
我能与林青成为闺蜜,完全是人生中的意外,俗称缘分。
四年前的一天,我走在大马路上,听到有人喊,“小白,小白”。条件反射似的边应声边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转身望去。
见林青穿着一身白色运动装,手里牵着根皮绳,我顺着绳子看向跟前,一只全身雪白的大狗,正用鼻子嗅着我的裤腿。我不敢乱动,从小就怕狗,何况还是一只大狗。在我眼里,狗分两种,一种是我们老家养来看大门的土狗,一种就是有钱人养来解闷的“狮子狗”。这只“小白”通体覆盖着白色长毛,看起来油光水滑的,尤其是脖子上系着的小领节让我准确的判断出,这狗属于“狮子狗”一类的。
林青轻轻的用力扯了扯手里的狗绳,“狮子狗”在狗绳的阻力下,不得不放弃嗅我的裤腿。林青上前一步,企图用那只没牵狗绳的手,按住“狮子狗”的脖子,可这“狮子狗”顿时“疯如脱兔”,往前一冲,嘴直接亲上了我的小腿肚子,并咬了一口。
一想起听别人说过的,被狗咬了可不是小事,严重的会得狂犬病,我吓得哭出了声来。
林青急忙上前,抓住“狮子狗”,将我的腿成功的从狗嘴里拔了出来。
其实“狮子狗”也没真咬着我的腿,只是咬住了我的裤子而已,不过当时确实慌了。
林青只微微看了一眼泪眼婆娑的我,并没有表示太多的关心,弯下腰将“狮子狗”轻轻地抱在怀着,用手帮它顺着背上的毛。
“看来‘小白’喜欢你。”
我用手背胡乱的将眼泪抹去,整个动作略显狼狈,“喜欢我还咬我?”
“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被咬得比你还惨。”
我和林青就这样认识了,和一切俗套的友情剧情发展一样,我们不“咬”不相识。
后来,我无数次要求林青给“狮子狗”换个名字,林青说换成小七怎么样,我说还是算了吧,叫小白也挺好。再后来,我再也没见过“狮子狗”小白,林青说它跟别的狗私奔了。
有一个豪门闺蜜,我感觉自己也是半只腿踏入豪门的人了,在林青长久以来的名缓气场的熏陶下,我感觉呼出的二氧化碳都变得高端大器上档次了。
而林青有了我这个女**丝闺蜜以后,学会了翻白眼。
我上前把背包往林青旁边的空座上一扔,在杨义旁边坐了下来。
看着杨义云淡风轻的淡定劲儿,我反而不淡定了,难道是受刺激太大,反应失常了,我将手重重的往杨义肩膀上一拍,安慰道:“小白杨,要挺住呀!”我特意将“挺住”二字咬得特别重,希望可以向杨义传递些正能量。
杨义转头看了我一眼,嘴角轻轻的扬了扬,“我没事。”又端起咖啡品了一口。
在我看来,杨义那轻杨的嘴角不是坚强的表现,而是一个男人被深深的伤害之后,面对朋友的安慰,为了不让对方担心,同时还要保持着男人范儿的强颜欢笑。
我又看向对面的林青,小心翼翼地问道,“他不会是被刺激傻了吧?”
林青仿佛没有看到我脸上的担心与震惊,冷清的说道,“一早看到周雪儿,挽着个男人,从对面的豪庭酒店出来。”
果真是有“奸情”,对“奸情”的兴奋代替了对杨义的担心,我又接着追问:“然后呢?”
林青白了我一眼,无视掉我的兴奋劲儿与求知欲,“通知了杨义。”
“接着呢?”
“就是你看到的这样。”林青看了杨义一眼,无奈的说道。
我见杨义还是一副无动于衷,事不关己,云淡风轻的模样,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由然而生。但再怎么气恼,眼下安慰杨义才是最要紧的,这是我头一次安慰被劈腿的男人,而且还是我的闺蜜,我心想,一定要组织下语言,既不能伤到杨义的男人自尊,又得传递正能量,还得晓之以礼,动之以情。于是我在心底打了一番腹稿之,拍着杨义的肩膀,语重心肠的安慰道:“小白杨,别难过,绿帽就如同男人成长路上的荆棘,所以咱勇敢的戴上它,再撕烂它,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说完以后,我仔细的观察着杨义脸上的表情,见他原本云淡风轻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龟裂的迹象,我知道我的安慰发挥作用了。
杨义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对着我和林青,郑重的说,“不用安慰我,我早知道了。”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