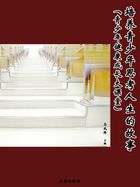鹿茸卖了个好价钱,日子一天天过去,赵白茅在深山中也走得越来越远。他进了林子就像是鱼进了水,什么招都敢想,哪里都敢闯,几丈高的大树搭个手就能上,到了陡峭的山崖地带甚至会手脚并用地爬行。这两年光是村人知道的,他就至少碰上过十多次豹熊之类的大牲口,有一回甚至是靠着装死,才逃过黑瞎子的血盆大口。
那年秋天赵白茅猎到几只紫貂,卖了貂皮回村后,一路上只要有人伸手,他都会给个大钱。猎户讲究的是讨彩头,有几个癞子却嫌钱少,嘴里不干不净,他就站着看人家一会,笑嘻嘻地反过来给人家赔不是,“我还得留着钱给我爷爷治腿,等他好了,叔叔们要啥我给啥,指定没二话。不就是几张破皮子吗,人活着还怕弄不到了?哎,老疤叔,你那皮袋里装的啥?别藏了,我都闻着味了,是不是打的好酒啊?我尝两口?你别走啊!就两口!”几个癞子被他嬉皮笑脸这么一弄,明知是给自己画了个大大的饼,却无论如何也发作不起来。
随着狩猎经验慢慢丰富,赵白茅开始体会到武器的重要性。角弓又换过两张了,但还是觉得杀伤力不够。他不止一次想过,如果箭头不仅仅是包铁,而整个都是铁打的,一发十支,那该有多厉害。猎叉虽然威力大,但却太过笨重,要是能随意伸长缩短就好了。
这一年,盔枕村来了帮专为猎杀异兽进山的武师,他们身上背的家伙着实让赵白茅大开了眼界。
异兽不同于寻常猛兽,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九头鸟、貔貅、青牛之类,极其罕见,即便大队猎户在赶山时撞上了,也决计不敢招惹。成年异兽体内大多生有兽丹,是炼制上品丹药的极佳原料。传说这等凶猛多智的物种一旦活过百年,便能成精变人,盔枕村的猎户别说是打,连看都没有看见过。
这帮武师来到盔枕村落脚,做进山前的准备,村中猎户虽说平日里好勇斗狠,见了他们却多少显得有点发怵。武师们没带弓弩,背的全都是雷州墨家特制的火器,据说一铳轰出去,连五百斤老山猪的厚皮都能洞穿。赵白茅远远瞅着那些包得严严实实的长条皮囊,眼馋不已,但在听过村人大谈墨家机关术如何了得,造出的东西又昂贵到何种程度后,未免瞠目结舌。马鹿紫貂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碰上的,一张上好的猞猁皮最多能卖五十个大钱,想要攒一千个大钱也就是一两银子,寻常猎户起码得花费几个月时间。一两银子能买得到一把钢火不错的短刀,却未必能值墨家火器的一颗弹丸钱。猎户们说那玩意在关内向来有价无市,玩得起的都是些阔佬,一般人能看上一眼,那就是天大的福气了。
老赵头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用他的原话来说,阔佬算个鸟,一把破铳算个屁!谁他娘的不是一个脑袋两条膀子,他们能玩得起,咱们就一辈子注定玩不到?啥事连想都不敢想,皇帝老儿的位置岂不是得空在那里,等老天降下个真正长角带尾巴的龙种才能坐?!在盔枕村人人都管老赵头叫“疯子”,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此——哪怕他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也绝不会改了满口狂言的毛病,连教孩子都教得跟常人不同。
老赵头不止一次跟赵白茅提起,年轻时亲眼看见过仙侠飞天,并一口咬定修武才是穷人翻身的唯一出路。
“龙门峰那地方有多高多冷,你总该知道吧,不是仙侠,谁能在那里呆得住?老子眼看着那人影呼的从山顶上飞起来,吓得屁滚尿流,头也没回地跑了。唉,早知道他娘的就多看几眼……臭小子,别鼓个眼睛跟蛤蟆似的,老子还能骗你不成?修武修到一定地步,那就是活生生的仙人,再好的火器都没啥用啦!当年九州三分,唯独咱们关外东州还没主。浮屠王跟大燕抢最后这块地盘的时候,就是凭着金丹武圣的实力,单枪匹马杀尽八千铁甲军,一战惊天下,从此成了东州之主。嘿嘿,浮屠王也是穷人家出身,杀过猪屠过狗,还不是照样震得大燕到今天都不敢越雷池一步!”
老赵头靠在炕上口沫横飞,手里的二胡接连拉了几个破音。
赵白茅并不相信仙侠杀神之说,直到过了几天,那帮武师从山上回来,他见到其中一人在借村民的百斤大秤称猎物时,是随手用两根指头夹着秤尾,接过秤去的。而在那时,秤砣还吊在另一端的秤钩上。
这得有多大的力气?赵白茅简直傻了,继而下了狠心——总有一天,老子也要学武!
从邻里的闲言碎语中,赵白茅知道老赵头年轻时曾喜欢过大户人家的女儿,没钱没本事却去抢亲,被打得只剩半条命,从此来了盔枕村郁郁过活。对于男女之情,赵白茅似懂非懂,猜想应该就是要拿来做老婆的那种,女的做饭生娃,男的挣钱养家。盔枕村有好几个寡妇,整天往家招些男人,王木匠之流便是常客,这般骚货赵白茅压根看不上。他觉得以后要是学武学成了,挣了大钱,就去城镇上买个宅子,再帮老爷子讨十几二十个正经婆娘,奶大屁股翘的那种,大人都说这样的好生娃。
赵白茅开始更玩命地进山,他知道自己现在能靠的就只有这双手。
王木匠没能断了占便宜的念头,有天竟趁着赵白茅不在家,偷到了门上。老赵头从睡梦中惊醒,滚下火炕,抱住他的腿死不撒手,嘴里大喊大叫。王木匠踹了老人两脚,连滚带爬地跑了。
几个月后的冬天,醉酒的王木匠掉进泡子里送了命,裤带没拴,下身惨白一片,那话儿冻得比花生米大不了多少。谁都不知道这家伙撒泡尿怎么撒到了离村那么远的地方,只不过也没谁去在意。
“爷爷,姓王的是我弄死的。”赵白茅那晚上陪着老赵头喝了半宿的酒,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如狼。
老赵头仰脖干了一碗,操起二胡,回了他两个字:“舒坦!”
老赵头最终治好了腿,这对于盔枕村的所有村邻来说,都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他们习惯于见到赵白茅进山玩命,习惯在背后指指戳戳,更习惯嘲笑这个对于穷人而言不可能实现的念想。
现在他们尽皆目瞪口呆。
没有人知道,赵白茅带着所有积蓄去请大夫的那天,钱还是差上一点。药童报完点过的钱数后,那大夫斜眼看了看堆成一堆的铜板碎银,脸上的讥嘲呼之欲出,“我这里可是祖传的招牌,一分手段一分诊金,半个子儿都不能少。”
赵白茅静静地看了他片刻,抽出还沾着血的猎叉,一言不发地放在桌子另一边。
于是大夫带着药童一起赶来。
老赵头又过了一段舒坦日子,寿限终至,某次酒后长睡不起。
赵白茅没有掉泪。
他又开始攒钱,为了走出大山、出人头地的承诺。老赵头打听过,黑沙江对岸马王屯的一家武馆不错,赵白茅本想够钱之后就去求个弟子名分,却没想到在山中碰上了那个来自斩龙城的姑娘。
生平第一次,他发现所有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总和,离自己如此之近。
伸手还是缩头,并不难选。
至少老子摸到过,不是吗?赵白茅当时只有这么一个疯狂的念头,像体内熊熊燃烧的野火。
天池湖边,赵白茅趴在浅滩上,呕了许久。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游上来的,更不明白又如何逃过了大劫。
上万兵卒拖拽的那个巨大石球已经不见,视野中看不到一个人,满地火把器械也全部被收走。赵白茅举目四顾,最终望向自己的胸前——可怖刀伤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道肉色嫩红的疤痕,背部摸上去也是如此。
“摸一下就动刀,还好我命大福大!”赵白茅笑得上气接不接下气。
百里之外,大队巡城马的簇拥下,一个窈窕身影似是心有感应,回首看了眼月色下的白头山。
“大小姐,他看到天石,本就留不得,别再多想了。”莫七骑在马上低声说。在他身后的运送队伍中,二十四架愚公车所载的巨型石球被油布蒙得严严实实,上万兵卒军容齐整,鸦雀无声。
“你早就打算一到地方,就要他的命吗?”莫红眉瞥了他一眼。
“我倒是没想到,他见识过七杀星芒,居然还敢跟我们走。”莫七显得有点感慨,“初生牛犊不怕虎,大概说的就是这类人了。”
“这样的蠢牛,比那些软骨头强得多……”莫红眉出神半晌,忽向策马行在不远处的中年将军招了招手,“魏将军,这次我爹不让我来,我偏偏还是来了。不知道回去以后,你怎么跟他交待?”
“末将自当向主上请罪。”中年将军抱拳答道。
“那你杀了我想要杀的人,又怎么跟我交待?”莫红眉笑了笑,瞳仁深处有着什么东西如火苗般蹿起。
中年将军听她语声有异,抬头看时,骤然口喷鲜血,大叫一声栽下马去。
运送队伍稍起涟漪,随即抢上几名偏将,抬了那将军快步走开,唯恐一个不小心,这小魔女又要出手伤人。莫红眉却是对他们视而不见,恍惚中,只觉得那双充满野性的眼睛仍在面前,正眨也不眨地看着自己。
这种感觉,对金枝玉叶的她而言,正如一壶烈酒不小心洒上了胭脂。
绝不协调,但也同样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