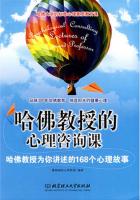明珠怔怔出神,似已默认。白狐继续道:“后来,我才知道,那小贼如今正是那偏居一隅的伪汉皇帝,陈友谅!云楚他正是借了这个机会招揽了那厮,这几年,我们泰山派的人没少受陈友谅的挑衅,他云楚倒乐得在一旁看好戏。当时,尔东发现你那个侍女行迹古怪,到底是不是她把陈友谅引过去的,我自然不好说,后来那夜,尔东怀疑她往酒里下了东西,便跟踪她一探究竟,岂料竟被她察觉,还交上了手,这样一个狠角色,不由我们不忧心。”她缓缓摇头,似乎在叹息。
邢佳佳道:“说到这,你也该明白,到底是谁下的药了吧?他本想让采酒玷污了你,再正好被晗弟发现,这样便能挑拨的我泰山派分崩离析,自相残杀。是云楚给你下了春药!”这一句话就如一面刀子,直直的插入她心口,痛的她直不起腰来,猛地抓紧了身下的床单,几乎要将它扯出几个洞来。耳边似乎又想起丹姬的话来:他越是待你好,你越是要小心,他最擅长整的人生不如死!
白狐见她额上大汗滚滚,面上略显不忍,劝道:“明珠,你始终是他的大仇,还妄想他能待你真心么?还是早早抽身吧,好么?”明珠缓缓摇摇头,似乎一面被锈蚀的铁门,几乎是僵硬的晃着。白狐又道:“我知你对晗弟心意,晗弟对你也一直痴心不改,佳佳生性单纯,你们两个在一起,总是互相体谅互相帮衬着些,又有什么不好?”
明珠摇着头,两行热泪簌簌而下,紧紧抱着胳臂,似乎周遭是百丈雪原一般。白狐与邢佳佳对视一眼,也只能无奈的叹了一声,道:“既如此,你做何打算呢?”话音刚落,便听门上传来敲门声,是宋采酒:“师娘!”
白狐扬声道:“进来吧!”宋采酒问声迈了进来,他肩上还缠裹着白沙,但也没什么大碍了,行了礼,道:“师娘,采琴师弟传来消息,云楚即日要赴太原,似乎是与察罕铁穆耳见面。”
他说着抬目扫了明珠一眼,见她一袭素纱,衬得侧脸及耳垂都莹白似冰。明珠眸中一波,暗暗打定主意。白狐轻叹一声,道:“你果然还是放不下。”邢佳佳问:“怎么了?”
明珠真诚的回视了她一眼,她深信下药的不是邢佳佳,所以不再怪她:“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看看的,白姐姐,佳佳,谢谢你们,我明日便告辞了。”
宋采酒大惊,道:“姑娘身子还这般虚弱,怎能独自远去?还是让在下送姑娘一程吧。”明珠笑了笑:“不必,宋少侠的好意我心领了。”宋采酒只好低了头,许久方道:“周姑娘,你为何这般固执,非要一条道走到黑呢?看得出师父师母都很喜爱姑娘,你何必非要跟云楚那魔头搅在一起,况他只是一味在利用那你。”
明珠不语,心中暗暗道:即便你们是好人,我也不敢相信你们,即便他是恶人,我却依旧愿意相信他,明知这样傻,却半分由不得自己。
邢佳佳拉了她手,道:“周姐姐,既然你非要走,那叫晗哥去送送你吧。”明珠抬了眼,朝她眼里望去,似乎想看穿什么,又始终什么都看不破,唇角勾了下,语气淡淡的:“不必了。”
众人一时无言,邢佳佳见药已凉透,便拿回去热了,宋采酒也告退出去了。白狐见她倦意甚浓,搀她回房休息,替她掖了掖被脚,道:“明珠,你太傻,你难道真的看不出,他不爱你?”
明珠愣愣的盯着帐顶,幽幽道:“我知道……他心里只有白姐姐你一人。”白狐摇摇头,苦笑道:“你错了,我之前说我的脸是被仇人所破,其实不尽然,这事,还是拜他所赐。”
明珠转眸看她,只见她那半边冰冷生硬的银狐面具,一时哑然,道:“是顾君倾么?”白狐手紧紧抓在衣角上,良久才整理好面容笑道:“罢了,瞧我,还提这些做什么。”又埋头为她理了理被脚,关切道:“那九阴真经,你断不可再练了,我前日为你运功驱毒,显然招了魔道。想来云楚教你的心法是错的,你每每运气时,胁下是不是针扎般痛?”
瞧明珠默然,便点头道:“果然,他真是卑鄙。”又道:“那日若不是晗弟出现的及时,你与佳佳只怕都难逃走火入魔的下场。晗弟他如今武功大进,假以时日,云楚也不是他对手,难得,他一直深爱你,哪点及不上云楚呢?况如今尔东也松口了,你虽说是妾,但佳佳绝不会欺凌于你,能与相爱之人厮守,名分这身外之物又算得了什么?”
她说完,再去看明珠,已然睡熟了,窗外依旧飘雨,昏沉的光线洒在她面上,那面孔竟不沾一丝血色。她叹了一声:“云楚,你何其残忍!”便迈步出去。
吱呀!一声,古旧的檀木门咧开一道口子,细沙样的日光透过门缝射在木板地上,空气中似有千万丝缕光芒跃动,乌靴鞋底踩在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清俊的手,拾起桌上一卷发黄的书卷,那是一本唐诗,才翻了两三页,书旁是一笔簪花小楷的注脚,熟悉的字迹,却不由浮起这样一幕:
同是这样一个柔和的晌午,她笑嘻嘻的拿着几张纸过来书桌前,她那样背光站着,明眸散发着晶亮的光,周身也仿佛镀上一层光圈似的。
嗓音宛如清泉泠泠有声“我有几个字不认得,你瞧瞧怎么念?”他搁下笔,略略好奇的看着她,道:“何字?”她摊开手,摆上一张三寸见方的宣纸,食指在纸上一指:“这念什么?”
他挑眉,还是读道:“我!”她点点头,揭过第一张,指道:“这个!”他心怦然一动,道:“爱……”她很满意,又揭过一张,微微低了脸去,小巧精致的耳垂似乎被日光刺穿,莹润有光。她在等他说下去,他唇角动了动,许久才道:“猪!”
她抬起头,一脸不满,嘟着小嘴道:“啊?!”他一笑,将她圈在怀里去……
他突然笑笑,那笑容中竟有一丝苦涩,索性撂了书,抬步走出屋子,衣角带起一阵风,哗啦啦,将那书卷又翻过几页去。屋外原种了一株桃树,此刻新红未谢,淡香悠然。
又想起那个下午,他坐在桃树下读书,她靠在一边,百无聊赖的拿了他手去玩,右手擎了支紫毫小笔,他看得入神,只觉被她拉着的手指尖痒痒的。
再一转头,只对上她灿烂如桃的脸庞,举着他掌心给他看,炫耀道:“你瞧!”他顺着她视线向掌心望去,唇角僵了下,那五个指头上各画了个小孩儿的脸来,俱是眉眼弯弯,咧着嘴笑的模样,不禁就问道:“这是什么啊?”
她振振有词,柔软的小手一下一下指着:“这是你想我的时候,这是你很想我的时候,这是你非常想我的时候,这是你想我想到发疯的时候,这个……是你最想我的时候!”
他面上和若春季里最温柔的风,颊边隐现一个梨涡来,又问:“那为什么是笑脸?”她笑的越发厉害,双目弯得像月牙儿般:“想我的时候也要笑哦!”
一片桃花飞落指尖,他抬手捻住,那一瓣粉粉的润润的花瓣就捏在拇指与食指之间,艳丽恬淡,总是像极了她的脸,她的人……“想你的时候也要笑么?”他心里这样念了一句,唇边现出一抹苦涩的笑来,像是刚喝了最苦的药汁,嚼了苦丁的根茎,又似乎,那也只算得上是冰山一角罢了。
又是无数落英缤纷而下,一个浅粉人影半跪于地,明眸照水,禀道:“回主上,找到明珠小姐了,在城外栖霞镇郊的一所闲庄内……”见他只是淡淡嗯了一声,又请示道:“主上,可要接小姐回来?”
他眯起眼,逆着光看去,那锐利的视线,似乎要刺破云层,直插到九重天上去:“不必了,给她一次选择的机会也好……”指尖不觉使力,那一瓣落花已成黏黏一团,粉色的汁水染红了骨骼清秀的指头,顿时玉陨香消。
听见门响动,明珠翻了个身,雨声沙沙,吵得难以入眠,她索性张开眼,朝外看去,那一丛丛枯黄的竹子都模糊了,竹窗前落下的雨滴溅起重重轻雾,几滴雨沿着墙壁一直往下,流到了地上去。到底是谁在酒里下了药,这似乎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各执一词,又好像都很有理,说来说去,不管在哪一方,她都只是一枚棋子罢了……
浓浓的药香扑鼻,竹门再次传来开阖声,带来淡淡凉意,她便又闭了眼,不自觉的裹紧了被子,可好像不管怎么包裹都不能暖和一点点似的。脚步轻捷,她似乎早猜到是谁,亦只是睫毛颤了颤。裴晗温润的声音传来:“听佳佳说你一直不肯吃药……”
她颤了一下,没有睁开眼来:“我不是拿样,只是我从小到大都不吃药,你多少也听说过吧。”裴晗似乎点了点头,轻轻嗯了一声,一只略带温度的手探上额头,她一颤,猛地坐了起来,警觉道:“你要做什么?”话一出唇,又略略后悔,因他此刻眸中,竟带着一丝郁郁,失望,又或许别的什么。
她裹紧了被子,低头道:“裴晗,我还能相信你么?”他伸过手来,一把将她束在怀里,认真道:“明珠,你可以相信我,尽管你不再相信全天下的人。”她突然觉得心上暖融融的,颤颤道:“可是,你也可能被利用而不自知。”
裴晗将她拉开一些,凝视她削瘦的脸庞,一字一字道:“我不会让别人利用你。”明珠喉间哽咽,撇过脸去,道:“太迟了,裴晗,我的心已经不在我这儿了。”裴晗眸中闪过一丝伤痛,那么深,她不止一次深尝,所以没人比她更了解那般滋味。
他叹了一声,抱起了她,顺手扯下屏风上的风衣盖在她身上,大步迈入雨帘,他的臂膀这么温暖,将所有雨丝都隔在外面,明珠贴在他胸膛的手微微颤抖,他认蹬上马,力夹马腹,马儿愤蹄狂奔,就像以往,又不似以往,他们的心境已经全然不同了。
白狐身着一件广袖真丝衫,衣袂轻扬,站在不沾片尘的竹墙前,翩若惊鸿,令人不能逼视。她双手交叠于腹前,望着那马蹄留下的浅窝,坑洼处已积了雨水,颇像一块无暇水晶,这样的天气,连吐出唇的话语都带着三分寒气:“看见了么?”
她斜后方站着的欧阳东俊唇角勾起一丝笑容,一节竹簪绾着半束发丝,广袖羽衫,加之面上闲适的神情,直与那四周遍植的修竹无二。只瞧他点一点头,原本无波的眸中泛起一丝精光:“虽然以裴晗如今的武功修为,白姐已不及他,但是他总是受过您的救命之恩,您要开口拦他,他断无拒绝之礼。”
白狐轻轻摇摇头,眸中似堆砌一团柔和的雪光:“我当初救他,本就是怀着私心的,他这些年虽从不提及,想来也该知道一两分了,况且明珠又何尝不是救过他性命?他对明珠,到底是用情至深,上回逼着他诈死,已经是极伤他心,若今日我再出言相迫,他只怕就要拿命来还我了。我难道还真让他死不成?”
欧阳东俊沉吟不语,又听她叹道:“这孩子温厚大度,不记仇恨,一项都以赤诚之心待我与尔东,若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是好人,那么一定是晗弟了。他与明珠原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直如瑶台双壁,若不是我们拆散,此刻定成一对神仙眷侣……”
欧阳东俊听出她话语中几分萧索之意,开解道:“白姐不要太自疚,裴公子有他的责任在,再者说,有云楚在,他们就不可能在一起。”
白狐恻恻一笑,那一笑中夹杂的是说不出的万种滋味,神情也渐渐从失落中回缓过来,重归于一片清冷。欧阳东俊见此,微低了头献策:“白姐,不如派南风暗中看顾着些,我料想着,裴公子多半只把她送到栖霞镇,这一路上并不太平,不妨派人暗中盯着些,若是跟住了她,不愁收拾不了云楚。”
白狐点了点头,冷笑道:“你说的不错,即便是晗弟放她走,她也必然会去趟这趟浑水。就让南风跟着她,你也跟去,时机成熟就下手……”说着又补充道:“路上照应着些吧,好歹她也叫过我几日白姐姐……”
欧阳东俊愕然,急忙道:“这怎么行,南风不在,谁来保白姐安全?”白狐转眸看了他一眼,道:“左右你还是信不过晗弟?放心吧,我明日就启程回泰山去,别磨叽了。”她眸中寒光一闪,语声仿若发自幽冥:“我预感,察罕帖木儿一定会跟云楚闹出点什么,咱们刚好坐收渔人之利。”
欧阳东俊略略一想,白狐腹中怀着的,可是刑尔东的骨肉,裴晗怎么说也不能置结拜大哥的孩子于不顾,便应着去了。
白狐发出一声薄叹,一转头,见邢佳佳站在门口,顿时一惊,脱口问道:“你都听到什么了?”邢佳佳倒是一脸惊奇,反问:“什么听到什么?嫂子,您怀着身孕,怎能站在檐下吹风?叫哥哥知道,又不定怎么数落我……”她小声抱怨着,搀了白狐进屋,又捧上一碗安胎药。
白狐心中犹自计较,面上却温和如春,接过来吹着热气:“你真是有心了。”邢佳佳似是有些失望,托着香腮道:“是晗哥吩咐熬得,他说您昨儿个睡得不好,这几日又奔波劳烦的。”
白狐笑笑,药还太烫,不知是为掩饰尴尬,还是另有目的,问道:“上次同你说的事?可有苗头了?”邢佳佳面上一红,支吾道:“我倒没什么,是他……总也……”整个人都忸怩不安起来,惹得白狐哈哈大笑,拉了她在身边,道:“不怕,嫂子教你……”
雨丝又细又乱,却依旧没有打乱他的方向,他一直往东北,路边景物匆匆,他却无心去看,柳条刮在脸上,竟也不觉得疼,她只叹道:太迟了,你这番话说得太迟了,曾经那颗心就摆在你面前,可是你错过了,它被别人捡走了,想要却再要不回来了。
为何她总是在错误的时候遇上不对的人,若是没有云楚……又怎能没有云楚,没有云楚,她或许早被江湖人士残杀致死,根本不可能健康快乐的长大,是云楚给了她一个美好的童年,只是,他又统统收回去而已。
到了界碑前,他猛地收缰,马儿人立而起,连嘶数声。他仔细的为她系好风衣的带子,雨丝变的朦胧轻缓,柔柔的抚在二人身上,又将二人隔绝于人世之外。他修长的指为她展平衣角,终于等到那披风上一丛丛翠竹都平平铺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