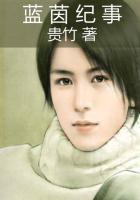马姐眼镜的镜框于大客厅老式座灯的黄晕中在我面前带过一缕银色的闪光,而傅婉云对于马姐身份的揭示让我多少放下了一些好奇心。
一幢两层的旧式小洋房,现在大概就住着这么两个女人,马姐一人操持上下诸般事物,名为“管家”其实就是个保姆嘛。
看来我之前以为这小姑娘家业庞大,该是多虑了。
先前傅婉云一口啖定要亲自为我准备夜宵,我便不好再推辞,依着她的话坐定了一方黑木茶几边的青藤座椅。左右环顾了一下,这间客厅的布置格调相当雅致,除了器皿家具都很有些年头了之外,装饰品也都是古色古香,。特别是我面前茶几上的一个青瓷花瓶,里面虽然只是几支寻常野花,但花瓶圆中带方,四面分别烧制有四只沉眉怒目,惟妙惟肖的牛头,让人忍不住便想多看几眼。
再联系到傅婉云这小妞雅致而充满了淑女气质的名字,这剡溪口傅家虽然门面不大,莫非也是什么书香世家不成?
没等我想完,马姐就已经端着茶托和茶盏翩翩而来。或许是因为大厅中的灯光过于古旧和迷离,我在马姐的身上看不到那种“服务者”的气质和态度,她的脚步是如此不紧不慢,自信翩然,就连银色眼镜后面的笑容也温婉可掬,比起傅婉云来,她可更像是这一家子中的大女儿。
“马姐,有劳了。”
从她托过的茶托中接过那一盏蓝瓷杯,我笑着说。
其实我并不懂品茶,但好歹是龙井虎跑边长大的人,在鼻端略略一过,我就知道这毫不起眼的瓷杯中乘得是江浙一带上好的新茶。这时候只听马姐笑着说:
“师傅,小云把事情都跟我说了,今晚多亏了有你在,才不至于弄出大事情。小云的父亲在外经商,她妈妈现在跑到姐妹家里去搓麻将了,大概总要等到个十一二点才会回家。师傅你看,你是不是在这里稍作休息,等主母回来了以后再好好酬谢你……”
话说的倒也得体,可是我真是替这位姐姐捏了一把汗。
岂不闻史上有种淫贼,专做偷心之事?救人,那不过是个幌子而已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小僧我既然号称大湿,当然便是躲在后面的那只黄雀了。想要把我这只黄雀留到午夜?到时候人妻,女仆御姐,青春美少女齐聚一堂,本大湿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呵呵,那可就很难说了!
况且屋子里还放着一个尚未尽兴的俏尼姑,我这一趟,实在是不宜久留。所以我连忙推脱道:
“呃,小僧进了姑娘家,在这里受人款待,已经相当失态了。佛门弟子,救人行善那可是分内之事,马姐你也不要放在心上。再说了,明天傅小姐不是还要带着小僧去雪窦山一游的嘛,有什么事,那时候再说也不迟呀。”
“好,既然这样,那就请师傅在这里稍等,小姐马上就把夜宵做好了。”马姐提议不成,倒也笑靥如常,将茶托放在木桌上款款退回了厨房。
也不过是一盏茶的时间,傅婉云就端着两个小碟子上来了。我定睛一看,果然是因为我提了个光头,对我照顾有加,两个碟子里一个是糕饼,另一个好像是笋尖一类的食物。
“喏,这龙须笋干,还有我们这里的千层饼,你要是吃不光,带一点回去给打人的那个大叔吃好了。”把碟子放到我面前,傅婉云边说边坐到了我对面的那张椅子上。
“诶,你别看那人长得老,其实他跟我差不多年纪,你可别叫他大叔。”我心想贾托尼幸亏没听见傅婉云的话,不然还不被她气死!
“哟哟,哪个花和尚说刚才自己已经到了更年期来着……”这一会儿她回了家,气质更是活络了起来,灵动的眸光配上那黑瀑般的长发,在这令人感到恍惚间时空交错的老屋里显得别具一格,“是不是你啊?”
“滋。”
我咬了一口千层饼,觉得满口松脆,心想对于这个无聊问题也没必要和这小丫头争执,毕竟趁着这有限的独处时间,多了解她们家一些才是。于是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傅姑娘,你们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吧?”
“喔?”
人说头发长,见识短,这句老话虽然没什么考据的根底,但这位傅小姐似乎略有“见识短”的嫌疑呀。
虽然我救了她,可她怎么能这么就和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推心置腹,讲起自己家的旧事了呢?不过,这正是我想听的,我连忙刨根问底道:“这么说来,姑娘家祖上还是蒋总统的亲朋了?”
“不,这是我爸爸在我刚出生的时候转手从别人那买来的,以前住的就是那个无赖张俊卿一家。”
这么多年我看遍了多少女人,在这一时刻我的直觉告诉我,傅婉云的内心深处肯定存在一个难解的结,这个结有关于她自己的家族,也很可能有关于不为人知的隐秘故事。
“什么很风光?那是相当风光喏。”
不知道为什么,望着面前素妆长发,略带骄傲的容颜,我似乎在那古旧的灯光中看到了迷离的幻影,多少年前,也曾有一个女子在这镇上,在一间似曾相识的小洋楼中,与年轻的僧人谈经论道……
<a href=http://www.*****.co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