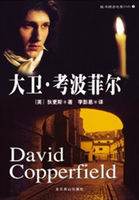陈铎一行走着走着已到了落西山的时候。
这时西北角有桔红色的云头涌起。整个西北角都泛着桔红色。陈铎感到不对劲儿,对冯仙说:“台风刚过又来台风,这连环风暴是最致命的。如果在雷州半岛沿海,难免家破人亡,好在他现在向西北走,或许能免于台风之灾,但朗月、铜鼓湾一带无疑会遇灭顶之灾。
他心里这样想着,脚步不觉沉重起来。到底朝哪儿走?他一时茫然。
走着走着,他们就觉得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污浊甚至腐臭味。北面是安铺石城呀,天色怎么会灰蒙蒙、阴森森,笼罩着一层邪气?行人十分稀少,牛羊更见不到影儿,地里全是枯黑的番薯,发霉的黄豆、腐烂菜类。陈铎站定,环顾四周,沉思片刻,喊道:“不好,不要走了,不要朝前走了。”冯仙立即拉着晓云和晓霞,惊疑地问:“为什么是这样?天和地都变了色?”陈铎脸朝北,双手按住丹田,闭目,慢慢地,双腿在轻轻地发颤。“不好”,他吼道:“发人瘟了,又发人瘟了……安铺和前后左右的村庄死人不少哇!”接着,他转脸向南,双手按住丹田,闭目……然后慢慢地睁开双眼,说:“往南走吧!到红土塘去……”
大家不敢说话,跟着陈铎朝南走。翻过一丘丘被遗弃的番薯地,绕过一丛丛勒古头,进入一条罕见的路。这是很古老的高轮牛车路,早已被遗弃了。红土地上两条深深的撤痕,向前延伸,像是大地无限延长的永不愈合的刀口,刀口凝结着暗血的血迹。年岁久远了,风也吹水也流,两条辙沟渐渐变成深深的峡谷。两边是壁立着的红土,长着稀疏的藤蕨。人在峡谷里走,只见一线天上,流云掠过。
“不要怕,但要小心点。这路太古老了……”陈铎见妻子额上的汗一串串滴落,两姐妹已气喘呼呼,便安慰说。说实的,这条古老的路,只有他走过。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从未对别人讲过那段历史,那段由人变鬼由鬼变人的恐怖历史。那历史严格地说,是从这条古老的牛车路开始的。陈铎父母双亡是在同治七年即一八六八年七月三日。四日后连旱了八个月的安铺、石城、雷州等地竟一边几日降下大雨。平地水深数尺,溪流两岸已变大河,庐舍全毁的村庄有数十条。数千人流浪他乡,陈铎才十岁,就把只有七岁的妹妹交给朝宇公,独自流浪去了。他记得被人抱上一张破艇,破艇从村东那条河驶出,竟进入了这条急流着黄泥水的古老牛车路峡谷。牛车路峡谷变成了急流,是陈铎亲眼见到的。那时也是红泥壁立,一线天永没有尽头。艇上只有五个人,陈铎最小。飘了五天五夜,飘到了北部湾海面,被越南船民救起,进入了越南的河内时失散,在街头流浪时,被一个来赶集的乡下寡妇拉走,寡妇在自己的茅房里跟他举行了“婚礼”,他半夜逃了出来,跑过五道岭,涉过三条溪流。流浪了五十九天之后,被人带到了泰国,再坐上商船过了孟加拉湾抵达印度。十四岁时他在一个长着许多野竹子的乡村,被婆罗门教法典的信仰者把他归为四种姓以外的旃陀罗,即贼民、不可接触者。两年以后,他听懂了印度语,有人告诉他,在印度,谁都遵守种姓制度。婆罗门教法法典把种姓划为四种: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贵族)、吠舍(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首陀罗(奴隶)。他所属的旃陀罗,是最下贼的。他一听气炸了:“我不是你印度人,我不属你的什么旃陀罗……”有人属于首陀罗的后来成了有文化的农民,有一天带他去听教典。他听到“灵魂可以复活”,转世很奇特;行善者成善,行恶者成恶;有什么种子就有什么收获。“轮回”开始无终,周而复始,但要经历生死和苦难,他还听人讲:宇宙本是一个“空”字。人也是“空来空去”。或许也是一种轮回吧,那年春季,天下的刺竹全开花的时候,一个好心的中国商人把他从印度带到巴基斯坦,再过缅甸、老挝,重回越南。最后进入广西,跟冯子材的部属回到风流村。这个“周游列国”的后生,仗着一身死胆,竟在回风流村第三天,就寻老祖宗独自悄悄地到了洪秀全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率领拜上帝教会众人起义的广西紫荆山麓的金田村,又到广东花县洪秀全故居旁搭个草寮,住了三个多月。
牛车路古老、漫长,竟藏匿过,陈铎的足印和由人变鬼、魂游四方的神话。如今,他带着老婆和两个内侄女儿又走进这恐怖的峡谷,他的心有一种苍凉感。看看日头已经偏西,直向“一线天”之西滑落,而牛车路峡谷还在遥遥伸着,他又一阵发冷,当即决定说:“往回走,你们在一个地方避避,我到牛脊村看看,到底村里的人是死是活,也好弄点吃的,孩子都饿了……”
冯仙领着两个孩子,在峡谷的一个干爽处歇息。上了牛车峡谷,朝牛脊村方向走去。
腐臭味和污浊空气越来越浓重了。田野里没有人劳作,路上也没有行人。来到风流村的邻村尖角塘,只见人去村空,只有几个老人在村口张望,神色悲怆、可怖。他认得最长者是李胜逵,有九十岁了,便上前问:“胜逵公,到底怎么啦?十户十空……天地全变啦?”老人干涸的眼眶里,忽然老泪溢出:“你是谁呀,还敢在地上走?!”
“我叫陈铎,被称为讲古王,不死鬼的陈铎呀!”陈铎自我介绍说。
“噢噢,你胆大,不怕死……”老人抹了把泪,说,“发人瘟啊!三乡五里,死绝的死绝,逃亡的逃亡,你为啥又回来?”
陈铎说了缘由。老人说:“村的神灵,村里只死那家‘万人恶’,不过还留下一丁,能逃走的都搬走了……好像还有几户人还在……”
急急地告别了李胜逵老人,径直向西村走去。
村里冷冷清清。不见狗叫鸡鸣,只见紧关着门的老气横秋的屋。他先到了一家的柴门前。门外,野草丛生,蟋蟀在草丛里嘀嘀嘀地悲鸣。屋檐,蜘蛛网被尘封已久,垂落下来。墙脚上却长着贼绿的清热凉药凤尾草。他摇了摇头,撞开了柴门。他一下惊呆了:
“不好!”他接连喊道:“不好,不好,不好呀!”他转身冲出柴门。
大叶榕旁那屋里只有老人洪朝海叔公和他的白岭婆在;隔壁住着龙弯婶和她的跛脚儿子;老井边那座茅屋,清空兄和他的老婆笑口嫂和在剥那霉腐的黄豆。他们见陈铎回来,不禁惊愕起来:“这不是陈铎吗?”笑口嫂慢慢地站起来,“哟,是呀!你怎么这才回来,狗仔、水妹呢?”摇了摇头。老人站起来握着陈铎的手直摇头:“天灾人祸,村里人都走散了。你快到红土塘去看看吧!”
“还有吃的吗?”陈铎问。
“有,煲的番薯还有几条,快吃吧!”笑口嫂忙到灶上取番薯。
用手巾包了几条番薯,向朝海公点了点头说:“我先去找他们,再回来看你们……”
说着转身出了牛脊村。
日落之前,西北血红血红的像刚刚歃血的大嘴巴在得意地笑着。陈铎自语道:“不好,不好……”他知天文懂历法,西北火烧天,台风扫平川,他知道不出二日,雷州半岛最可怕的台风就会到来。他来不及多想什么,匆匆回到了牛车路峡谷。
几条番薯分给晓晓云、晓霞和冯仙吃了后,他们又走进了阴森莫测的古老的牛车路峡谷。他头一句就对老婆说:“糟了,路呢?”老婆也为之愕然。
一线天上,偶有几点星光。他们眼望星空,默默地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这比当初破艇荡急水好得多了。他觉得奇怪,那时,牛车路峡谷已变成了河流,如今怎么又成了旱谷了?
晓云和晓霞的心在扑扑地跳。她俩各自拉着陈铎和冯仙的衫尾,跟着走,她们从未走过这样的路,从未见过一线天,也不知道跟他们走到哪里。陈铎对她们说:“别怕,有我俩在身边,什么也不怕。这条峡谷我走过,年纪比你俩还小的时候走过。那时是条急河流,我是坐破艇飘流的。”冯仙从未听他说过,以为他在对孩子说谎,说:“你讲古啦?那时是河流么?怎么不见水?”
“天地会变的。人间也会变的。生死也会互变的。那时有水,水会干的,那时我小,我会大,会老的。”陈铎说个不停,让孩子越听越有神。冯仙说:“是的,你姑丈呀越变越古怪了。他什么都不怕,跟着他,我们也不怕。”
风很大,不知从那里呼啸而来,直灌进大峡谷。两壁的林木呼啦呼啦地响起来,越响越大,像闷雷,又像野兽的怪叫。不知名的鸟被刮得惊慌起来,呱呱呱地飞着。在狂风横扫的黑夜,它们找不到归宿,无奈地在一线天的迷茫中拍打着双翼。晓云打着冷颤说:“姑姑,我怕……”晓霞拉着她的手说:“别怕,姑和姑丈在身边,什么也不怕。”
峡谷的深处不时传来狐狸和山狗的嚎叫,一阵紧似一阵,在峡谷里回荡,仿佛此起彼伏,没完没了似的。陈铎使劲地咳了三声,朗声笑道:“咳三声,回六声,你听。”冯仙知道他在逗孩子,也说:“这峡谷也有灵性哩!”陈铎说:“这就对罗。每一种生命物类包括人在内都有灵性,都有灵魂。”“灵魂是什么呀?”晓云脱口问道。“灵魂么,灵魂就是附在人的躯体上有主宰本事的看不见的东西。”陈铎像先生讲解文字一样文文雅雅地解析,晓云听不懂。晓霞说:“灵魂有谁见过呢?它是不会消灭的吗?”冯仙噗嗤地笑了。为了孩子高兴,驱除夜路的恐惧,她附和着陈铎,说,“你姑丈呀,没有什么不懂的。你们就追问他好了!”陈铎又大咳了三声,听了回响后说:“灵魂不会死的。有情物死了,灵魂又粘附在另一个躯体上。人死了可以转世。转世才容易呢!行善者成善,行恶者成恶,成牛成马成害人精。要想有好报,就要一辈子经过生死和无数苦难。捱得苦,成佛祖……”
晓云和晓霞拉他俩的衫尾边走边听着姑丈的离奇答话。虽然半懂不懂的,但觉得新鲜有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