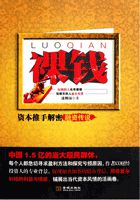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美妙。学年末,评先进。当优秀教师的却是秀和洲,奖状之外还得了一个搪瓷茶缸子。我无所谓,这两人当先进的奥妙,我相信川老兄的解释:“秀同志裤腰带松,嘴甜,她不光和明有一腿,和谦也很难说。不过我估计,老头儿有那心没那胆。洲呢,不说话,任谁也不得罪,而且会巴结。他背后给老头和娇主任送了多少东西?你不懂!”萱这次却不够超然。她没说什么,起劲儿蹙鼻子,将那漂亮的小鼻子蹙得惨不忍睹,小嘴也撅着。她撅着小嘴别有一番韵致。我逗她乐:“不就是一个破茶缸子吗?还没盖儿。”她仍撅着嘴,仍朝我蹙鼻子。
没辙,就切磋。切磋也没滋没味。我这才知道,女孩儿敢情都心眼儿小。
不料夜半时分,萱姑娘说了件惊人的事。前不久我有几天不在。谦校长有一次在萱的房子里,指导帮助备课至深夜。临了他竟苦苦觊觎这女孩儿的粉腮,最终借故摸了上来。被萱用肘臂阻隔而未遂。萱撅嘴原来不在于先进不先进,而在于此。
“这老公狗。”我暗骂。我想,他与秀的关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警告我俩儿原来正是狐狸吃不着葡萄。
“委实有些妈妈的!”阿Q曾如此教导我们。
我提醒萱,我与她之间该发生点什么了。不然,枉担了虚名。
她有点儿脸红。
她若有所思。
这天,杨村小学全体老师带着三、四、五年级的同学去参观一座水库。这是包括我们本乡在内的三个乡联办的工程,有上级政府的拨款资助,主要还是靠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说这是翻身工程,命脉工程。
让学生搬了一阵儿石头,以表示对水库工程的支持之后,是参观。参观完了,在水库岸边休息。没注意,有几个调皮的学生闹出了乱子:有两个爬上一条小船,另有几个解开了系着小船的缆绳。于是船顺水顺风,缓慢地向水库中间、向下游荡去。船上的孩子吓得吱哇乱叫。岸上的老师手足无措。我看那船上,并无桨篙之类的东西。即使有,那几个小调皮蛋也不会划。
川眼尖,他看见船上有一个铁撮箕。
“别动,小心翻船!”川一喊,船上的孩子不敢动了。
“拿好撮箕,别掉到水里。”川指挥道。
我领会了他的意图,接着指挥那个拿撮箕的孩子:“划,用劲朝后划水!”
“拿到左边来划!”川道。
“右边也来几下!”萱同志也跟着我俩儿喊上了,“左边,左边!”
还好,船又缓慢地向岸边移动了。
“哎呀!”岸边“扑通”一声。我一看,糟了,萱指挥学生划船指挥得忘情,自己竟一脚踏空掉下去了。
这里的水至少也有两丈深。我知道旱鸭子一般的萱同志掉下去,绝不是闹着玩儿的!我环顾四周,谦校长黑脸变白了,娇主任白脸变紫了,秀手舞足蹈吱哇乱叫:明不大迷糊了,但也不知该干什么;洲处变不惊,大约仍在默诵“沉默是金”;川要脱衣服,又明知自己水性不行,急得头上直冒汗。我责无旁贷,我义无反顾,我他妈当一回英雄或者傻冒儿。我脱掉衣服也“扑通”一声,跳得既干脆又漂亮。
我水性好得连我自己也像发现了新大陆。我抱上连吓带呛,已经犯迷糊的萱努力朝岸边游去。生死关头,虽然肌肤紧贴我也顾不得想入非非。临上岸时,他们七嘴八舌、七手八脚都显得对革命同志十分关心,十分爱护,十分不舍得让萱同志去喂鱼鳖虾蟹。
萱吐出一滩水后就清醒了,但仍然像面条似的软溜溜。明建议让荡船的学生抬萱老师,以示对他们的惩戒。谦不同意,说让秀和娇扶着走,实在不行就由川和洲轮着背。我和明年轻力壮却无事可干。我想,这件事能显出领导就是高明,也显出谦是正人君子。
好在萱恢复得快。走一走,她竟不让娇和秀扶了,牵着几个学生的手越走越精神。
我想我和萱真是有缘分。
我想她掉进水里,生死攸关,由我而不是由别人救她上岸。这大约也是老天爷安排的。
后来有一天晚上,切磋完了我并不想离开萱姑娘的房子。当我发现她眼神有些异样,呼吸有些粗重时,我冷不丁上去就是一吻——不是在唇上,而是在腮边。
不料她大怒。
“你这人……”虽算不上是勃然大怒,也分明是杏眼圆睁,“你……”
再无下文。我也顾不上听下文。我十分狼狈、十分尴尬、十分脸红心跳,匆忙告退。
又不料,半小时后,她竟到我的房子里来了。此时左邻右舍已熄灯就寝,万籁俱寂,世界真安静。她坐了下来,不羞不臊、不温不火、不言不声、不哼不哈,反倒把我弄得莫名其妙。对坐良久,她才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又怨又恨,又疼又爱,一切尽在不言中。
前嫌尽释。
我汲取了教训。我自知与吻什么的无缘,便只轻轻拉上她的手。她破天荒地没有抽出。
我发现,这手也漂亮。小拇指细细的,嫩嫩的,真像小孩子的手。随之而来的是我男子汉大丈夫的感觉油然升起。明白了女孩子柔就是美,美就是柔,又柔又美,又美又柔,才可以叫作女孩子。她的可人,她的依人,使我突发奇想:当初出生时真该努力争取时辰,弄个哥哥的身份才合乎道理,现在悔之晚矣!
有戏吧?
我与萱的“戏”全部也就在于此!
此后是暑假。一个暑假我过得很愉快,干活如舒展筋骨。深翻土地,不觉其累;掏挖猪圈,不闻其臭。看书如饮甘醇,昼寝夜读,不知其艰涩;困苦,不厌其烦。
我知道了“萱草”亦作“谖草”。古人认为它可以使人忘忧。我还知道嵇康《养生论》日:“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由此,我认为萱的父母给她取名为“萱”,比我的爹娘把我叫作“春”要高出好几个档次。我估计我从今以后,天天“忘忧”,月月“忘忧”,年年“忘忧”,这辈子大概都会无愁无苦、无虑无忧!
却不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高兴得太早了。
暑假里,萱和她妈一起到县上她爸那里去住了。我天天想夜夜盼萱同志的归来,没有想到却盼到了一条坏消息。
说是萱要订婚了。
当然不是和我。
我气急败坏。
我像热锅上的蚂蚁。
好不容易她回来了。
“真的?”我问。
“……真的。”
“谁?”
“喜。”
喜是什么东西!
初中时,喜和我和萱是同学,他有个外号叫“压塌板凳儿”。整天坐在教室里学呀学,考试老是倒数。年龄不大,皱纹满额,堪称严重自然灾害。每每看见他,我就想起我家后院养的那动物的脸,且挥之不去。他凭什么能和萱订婚,而我却不能?什么叫作鲜花插在牛粪上,嫩白菜叫猪啃了?
“为什么?”
“……”
“为什么?”
我脑袋涨大,眼睛发红。虽没有照相摄像,但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可怕。
萱用沉默作答。
后来她看我实在痛苦不堪,就主动上来拉住我的手,使劲儿摇晃,想让我看看她的眼睛。
我看了。她泪眼迷离,脸如死灰,全身颤抖。那痛苦不见得就比我的轻。
我想搂住她,揉碎她,然后就让天崩地裂,地球爆炸或地震水灾,失火触电,刀劈斧砍,怎么死了也比活着强。但是我不能如愿。男子汉大丈夫看见一弱女子比自己更痛苦,那么自己的痛苦就只好不痛苦。这也是我一瞬间的顿悟。
她剥夺了我歇斯底里的权利。
我还原如故我。
喜他爹是村上的副支书,副支书的妈是萱她爸的奶妈。萱她妈娘家的隔壁邻居就是喜他妈的娘家,萱她姑家的弟媳妇的妈又是喜他妈的姨妈,如此等等的关系和萱她爸妈要为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的想法,以及喜是当兵的又传言要提干(当时的姑娘们都喜欢解放军)等等原因,促使萱一家为她选择了喜。而我的父母,大字不识,老实巴交,本分为人,在村上的影响力实在有限。况谦校长以及熟识我的许多人皆评价我,瘦里巴叽,怪里巴叽,傻里巴叽,不会成大器,不会有大出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们杨村以及周围村上的年轻人订婚仍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自找对象的风气还远没有后来盛行。所以,萱很可悲,我很可怜。
更可悲的是她能反抗而不敢反抗。更可怜的是我想反抗而不能反抗。所以让她父母不费吹灰之力就铸成大错。
将错就错。
小学校的同事们都去喝萱的订婚酒,我也去喝。
为什么去喝?
为什么不去喝?
于是就去喝。
是萱她爸请小学校的人,在萱她家。并不要送礼的。用萱她爸的话说:“等孩子结婚再送礼不迟。”显示了他做人的精明。
白喝。白喝谁不喝?谦校长率领我们一行七人(萱不计算在内)如约赴宴。
一块钱一斤的散装白酒。谦喝得有滋有味;川喝得痛快酣畅;娇嘴咂得吧叽吧叽响;秀的笑声又响又浪;明迷迷糊糊,捏着个酒杯不辞不让:洲推三阻四,硬说自己没有酒量。我没怎么喝过酒,今天很想体味一下醉的滋味,猛喝。
萱很忙。添酒上菜,跑前跑后。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欢乐,还是忧伤。
萱她爸让萱给大家敬酒,每人喝双杯。杯很大,萱给别人都满上。给我的第一杯,她倒了半杯,我没说什么,仰起脖给灌了。第二杯让川给发现了,他说:“倒满倒满,茶半盏,酒杯满,不满不算。”萱不情愿地添满,我又一饮而尽。
酒越喝越没有滋味。萱几次三番将我面前的杯移开,都被我自己抓了回来。
不醉一回算没喝。我想。
喜来了。这小子初中毕业不久就去当兵。第一次回家探亲就订婚,而且是萱这样出色的姑娘。虽不是洞房花烛,也足够他风光一阵子的。他那长满了深刻皱纹的脸溢彩流光,笑得很傻。但也笑得真诚笑得酣畅。他与我们一一碰杯,嘴里无词可祝,于是只能越笑越傻。我趁着酒劲儿将他的杯一直碰得掉在地上,他依旧笑得很傻。我无可奈何,只有如灌凉水般地灌那廉价的酒液。
总算喝迷糊了。
我朦朦胧胧、恍恍惚惚、昏昏沉沉、摇摇欲坠、飘飘欲仙,萱模模糊糊、飘飘渺渺、影影绰绰、如烟如缕、如隐如现,渐渐远离我而去。
半醒半醉间,又闻谦校长放屁,声声如故。
他妈的正所谓积习难改,太煞风景。
这老浑蛋。
不,老公狗。
我醉了。
今夜无故事。
与萱的切磋备课在我看来,已成纯粹的例行公事,真正的革命工作。她也恬静如故,热情如故,从容如故,聪慧如故,悟性如故。总之,一切如故。
我弄不清楚她是顶傻,还是顶聪明。
我觉得我深沉还是她深沉,是个值得深思、值得研究的问题。
切磋如故,然而乏味如斯。
有一天晚上喜来了,他即将假满归队。我表情木然与之寒喧。
我出门时,漫不经心地将大半个吃剩的蒸红薯丢在萱的房子门口的台阶上。红薯是萱分给我的夜宵。
第二天,我对喜的鼻青脸肿表示同情。
我对我的卑琐亦表示同情。
日日夜夜无故事。
时光飞逝,我发现我唇四周的毛或日胡须变黑了变稠了,需要我用剃刀来对付了。我认为我教书之余,还应该干点儿什么,制造点儿什么。我穿着有洞的黄胶鞋和没有脚后跟的黄尼龙袜子,在母亲的抱怨声中,花光民办教师每月五元后来涨到七元的补助费,买来《朝霞》、《群众艺术》和《人民文艺》,苦读苦写。想发表点儿什么,换取点儿绝非稿费,而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什么。于是,我失恋的痛苦得到了渺茫的希望和忙忙碌碌的充实。
我觉得我与众不同,虽不伟大,但也不十分渺小。
萱还是萱。我买的杂志,她也偶尔翻翻,偶尔也与我讨论几句。她教书依然很好,普通话很快就消除了醋味,比我显得纯正流利。她工作之余,也增添了给喜回信之类的事情。喜的来信她看得很潦草,往往脸上挂着鄙夷或不屑。我去了,她也不回避甚至把喜的信推给我看,而我却从来都懒得瞧。倒是有一次,她给喜写信。见我来了,漫不经心地扔到桌上,我也就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发现她对喜批评表扬兼而有之,在纠正对方来信中的错别字之后,也称道对方为人忠诚厚道。
从此我视萱为喜的媳妇。
我觉得我与正人君子十分相像。
不料,忽一日我又将萱抱在怀里。
从部队传来消息。
喜原来是提干的对象,但事到临头突生变故,提了别人没提老实巴交的喜。喜想不通,找去问,没有结果,反倒挨了好一顿训。老实人发起火来,尤其暴烈。这家伙一怒之下,竟把部队一位干部打得脑震荡了。这错误犯得大了。据说即使不军法处置,也要开除军籍,回乡务农。从此再无前程可言。
这消息对萱不啻是晴天霹雳。
她哭了。
喜的爹,我们村的副支书很开明,他让媒人告诉萱她妈,自己儿子不争气,不能连累了萱。萱是好娃,是争气的娃,千万不能叫娃受委屈,娃想怎样就怎样,想不跟喜了也行。娃爱跟谁,就跟谁去。
萱听了这话哭得越发厉害。我想与她切磋也没法切磋。她看见了我,恰似看见了亲人,看见了兄弟,看见了能诉衷肠的人。她泪如泉涌,红着眼睛拉开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我坐下,她也坐下,不声不言继续哭。我看她哭得认真,哭得投入,哭得动情,哭得没完没了,自己不觉也有些鼻子发酸。但我牢记“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古训,狠了狠心抑制了自己。不哭不流泪不等于无动于衷。我坐了许久,不觉站起身来绕过桌子,来到萱的面前。她又如同上次落水一样,先是抓住我的手,然后扑进我的怀抱。如同要死里逃生,要与我甘苦与共,一起游向幸福的彼岸,我能怎么样?
于是,我狠狠心搂紧了她。这一搂显然是同情,是安慰,是帮助,是解救。她理解,她明白,她感激,她回报,她也就搂紧了我。搂到后来,她抬起头来,泪眼迷离,满怀深情地搜寻我的眼睛。我想这时候假如我低下头来,吻她眼,吻她唇,她除了幸福得颤栗之外,大约不会再有别的选择。但我是血气方刚的五尺男儿,怎能趁人之危,趁火打劫?我高昂起头,眼睛死盯着对面的砖墙,内心在拼命抑制某种欲望。终于,我扒开她的手,挣脱她的搂抱,回到她桌子对面暂时属于我的那把椅子上。
“我该咋办?”萱慢慢冷静下来,止住哭,问我道。
我默然。
我能说什么呢?
“人家有难,我总不能再给他家的人伤口上撒盐。”
萱太善良,她竟被副支书一番话感化了。她决心继续做副支书的儿媳妇。
我知道我与萱之间依旧没戏。
我知道我的戏在什么地方。我想我得面对现实。我很清醒。
萱写信。
不屈不挠地写。她劝喜知错认错,深刻检讨,深刻反省。她主张喜要主动请求处分,主动承担责任,不要推诿不要抱怨。她还说我不怪你,我原谅你,因为事出有因。她说我想着你,我等着你,你要鼓起生活的勇气。如此等等。
她每写一封信都向我征求意见。我认为她可悲,她可怜,她值得同情,于是我全力支持她并不甜蜜的爱情。但我始终弄不清楚,我这样干是十分高尚,还是三分卑鄙,是行善还是作恶。
她也给部队领导写。以喜的未婚妻加乡村女教师的身份分担责任,说是她对喜帮助不够,教育不够,请求部队首长对喜既要从严教育又要宽大为怀,无论如何也要给条出路。言词恳切,情文并茂。我要是部队首长,一定会深受感动。
可怜天下少女心。
就冲着萱写的这些信,我想喜这混账王八蛋以后要是对她不好,那就该揍,该杀,该天打五雷轰。
我也写。
没完没了地写。投稿寄稿,请求改稿,用稿退稿。顺颂;编安;谨祝;近祺;斧正;敬请,不吝赐教之类的话。
我也有收获。收获了大量的退稿信和少量的稿件采用通知单。不像萱尽收获些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