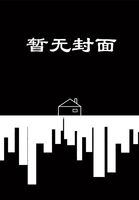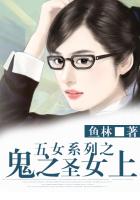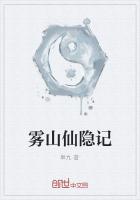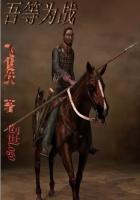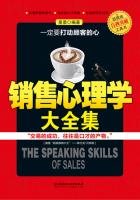1993年秋天,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授予了FCC将无线通讯频谱运营执照拍卖的权利,并且要求该委员会在一年之内开始第一次拍卖。对于一个没有实际拍卖经验的机构而言,在如此紧迫的期限内完成这项任务,或许FCC最好的方法是采用在其他领域被实践检验过的拍卖方式。然而,这样的做法在FCC当时所面临的环境下是行不通的,因为电信运营执照蕴涵的商业利益是巨大的,其潜在的市场价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从而在其他领域可以被采纳的拍卖方式无法防范拍卖过程中的串谋行为。当时有许多经济学家参与了这项拍卖的机制设计工作,当然,这些人当中包括米尔格罗姆。
首先被FCC考虑到的问题是选择上升价格式拍卖还是选择单轮标单密封式拍卖。因为美国联邦政府曾经在海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权的拍卖中普遍采取标单密封式拍卖,所以FCC的主管们确信他们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先将各个竞拍人的标价封闭进行报价,然后打开标单,选择出价最高的人。但是当时有很多人怀疑拍卖机制是否可以安排得更复杂一些以达到更好的结果。最终FCC还是选择了同时上升式拍卖。这主要是因为在一个相对公开的竞价环境中,各竞拍人之间会有信息的传递,竞拍人掌握的信息越多意味着最终的分配结果会更有效;并且,正如米尔格罗姆和他的合作者经济学家韦伯1982年的论文所提到的,这样的拍卖方式会减轻“赢者的诅咒”。
FCC当初(1993年9月)的想法是一个将上升价格式拍卖和第一价格标单密封式拍卖相结合的拍卖形式。对于两个覆盖全美国的通讯频段中的每一个,FCC计划首先对其51个营业执照作为一个整体采用单轮标单密封式拍卖,紧接着对每一个执照单独采用公开叫价式拍卖。封闭的标单在公开叫价式拍卖结束后被打开,如果标单出价最高的竞拍者的标单价高于所有51个执照在单独公开叫价中的价格总和,那么该频段的运营权将属于这个竞拍者。
在FCC最初的备案当中,也包括了同时上升拍卖。和其他的拍卖方式不同,这种拍卖形式是采用一个时钟系统;在特定的时刻,所有的竞拍人同时将自己的出价给出,并公开在显示屏上,经过多轮之后,出价最高的竞拍人获得执照。当时还没有人知道如何进行这样一种同时上升式拍卖,甚至有人怀疑它是否可以在一年的最后期限内被实施。但是米尔格罗姆和鲍勃·维尔森(Bob·Wilson)以及普雷斯顿·麦卡菲(Preston·McAfee)彻底改变了这样的想法。对于FCC本想要或者将要采用的拍卖方式复杂性的限制,米尔格罗姆以及另外这两个人的很多建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都建议FCC采用多轮的同时上升价格拍卖,因为这种拍卖形式在保留了标单密封式拍卖的简便性的前提下,还提供了上升式拍卖的经济有效性。
停止规则是拍卖机制设计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它规定了拍卖者在什么时候停止拍卖。米尔格罗姆和韦伯建议FCC采用一种同时停止的停止规则。与麦卡菲等其他人所建议的规则不同,这种规则规定所有执照的竞价同时结束,且只有在没有任何竞拍者出价于任意一个运营执照示所有的竞价行为才会同时停止。米尔格罗姆力推这种方式是因为,在这种机制下不会导致竞拍人无法使用某些备用策略。比如,若不是同时停止,一个竞拍人正在竞拍某一个运营执照,而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执照对于他可以替代这一个,若这一个竞拍失败,他可以选择替代者。但若一边的竞拍还未完成,而可替代的执照的竞拍已经完成了,这无形中组织了竞拍人使用备选策略,导致分配的无效。显然,采用同时停止规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然而,当时有人怀疑米 尔格罗姆所提出的同时停止规则是否会停止,或者会进行很长时间,这样是否会导致无效。但米尔格罗姆显然充分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并明确回答了对他方案持怀疑态度的人,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他的方案不会导致任何的无效。
另一方面,米尔格罗姆提出的拍卖方式中的活动规则被称为是对于复杂拍卖设计的完美解决方案。米尔格罗姆建议FCC使用这样一种活动规则:如果一个竞拍人在某一轮中停止过多的竞价行为,以至于他所参与竞价的营业执照的数量占他有资格竞价的数量的百分比低于某一个下限,那么他将永远失去参与以后每一轮竞价的资格。这样就无形中对竞拍者中止竞价的行为施加了一个成本,这样一个成本来源于对他未来竞价资格的剥夺。
FCC非常欢迎这种做法,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承受由于竞拍人竞拍行为的不积极所导致的低价成交的风险。这样一个活动规则有效地提高了对参与人的积极竞价的要求,并且减少了竞拍人在其他形式拍卖中会面临的风险,他们不会在他们还想继续叫价的时候被意外地告知竞拍已经结束,当然,这对FCC本身也是极为有利的。从而FCC可以更好地控制拍卖节奏。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如果不是这样一种活动规则的存在,宽带个人通讯服务的运营执照会在进行仅仅12轮之后结束,FCC获得的收益只有12%。而由于采用了米尔格罗姆的方案,在进行12轮之后,拍卖又进行了10轮,而收益的增加更是戏剧性的。
最终,米尔格罗姆的拍卖方案脱颖而出,被FCC采用。他的方案被采用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他的方案是拍卖设计领域的杰作。这种方案使得在竞拍过程中,竞拍人之间的信息更加透明,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更加充分。在这样一种信息结构下每一个竞拍人可以充分使用其所有的备选竞价策略以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从而达到一个更为有效的拍卖分配结果。然而,仅仅是一个好的方案不是被采纳的充分条件,因此第二个原因是米尔格罗姆出色的表达和说服能力。事实上,在米尔格罗姆最初提出他的拍卖方案的时候,FCC的主管们根本无法理解如此复杂的拍卖规则,他们无法预知这样的拍卖会给他们带来什么。而米尔格罗姆运用他的非凡的说服能力为官员们解除疑虑,他将复杂的拍卖机制中的各种机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给他们,让他们确信,他的方案是可行的且是非常有效的。
1994年7月,在进行了大量的计算机模拟拍卖之后,FCC的多轮同时出价拍卖在华盛顿开始。在每一轮中,FCC控制每个竞拍执照的价格增量,另一方面,他们还请了拍卖理论专家和实际操作专家作为顾问团用来给竞拍者提供策略上的建议。在经过5天47轮的同时出价之后,拍卖结束。这次拍卖成交了70亿美元,并向个人通信服务运营商发放了99个许可证。
爱德华·拉泽尔(EdwardP.Lazear)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大师爱德华·拉泽尔现为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与经济学”(JackSteeleParker)讲席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同时担任胡佛研究所(MorrisArnoldCox)高级研究员。
1974年拉泽尔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74至1992年间,他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历任副教授、教授。
1974年以来,拉泽尔一直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员,并且在1987至1990年期间担任了国内研究部协调员。
1992年以来,他一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历任教授、讲席教授。他主要研究雇员激励、提升、报酬、企业的生产率;文化、语言与人力资源管理等,尤其强调美国多文化主义的兴起及其对管理学的意义。拉泽尔的重要着述有《人事管理经济学》(中文版为三联书店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彼特原理》、《教育的生产率》、《业绩报酬和生产率》、《经济帝国主义》、《文化与语言》等。
全文核心提示
中国教育的问题是一个数量问题,而不是质量的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力资源的累积
中国政府在大学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两个方面的投入都应该加强
关于中国政府解决下岗工人的问题,拉泽尔认为必须寻找有效途径对这些人进行“再培训”
廉价劳动力冲击市场的观点在美国饱受争议,拉泽尔认为情况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糟
在某些公司内部有必要设立更多的等级职务
CEO并不需要激励,他自己会努力地工作
与其不断地从外面“挖人才”,还不如建立好的内部激励机制,“用好人才”
中国企业家必须了解世界其他各国在商业领域所使用的交流方式与方法
世界“管理经济学之父”拉泽尔谈人力资源
年初秋,在绿树掩映的珞珈山上,连续几天跟踪采访了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并为武汉大学EMBA学生授课的爱德华·拉泽尔教授。
1981年,拉泽尔曾经以旅游者的身份到过北京和上海,那时,他算是中美建交后比较早的美国游客了。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的北京没有宾馆,他们几个人住的“一种像学生宿舍”的建筑。他说,当时的中国人几乎都穿着一种蓝色制服,喜欢远远地好奇地瞧着他们,但是很少有人向他们打招呼,连随行的翻译也不敢与他们合影,生怕惹来麻烦。拉泽尔这次是第二次来到中国大陆,我有幸成了第一个采访他的记者。
拉泽尔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大个子、大耳朵、大嘴巴,那看不见头发的头颅也特别的大,光亮的额头格外耀眼,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还发现他的手也非常的大。一开始,他那种典型的美国西部牛仔形象让我怎么也无法与满腹经纶的大学者爱德华·拉泽尔联系在一起。拉泽尔教授第一次出现在武汉大学的课堂上,发现学生们都穿着休闲装,于是他用中文说了一句“早上好”之后,便以最快的速度脱去西装,解下领带,他说:“我希望与你们做朋友,现在大家都平等了。”课间他感叹道:“现在中国人的衣着在华尔街上也毫不逊色,上次来中国时的那种蓝色制服,现在都看不到了。”他多次感叹,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在4天的时间里,我听拉泽尔讲述了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许多前沿的重要的信息。但限于篇幅,我只能把他谈及的关于中国的话题拿来与读者分享。
一、中国现在急需要做的是积累足够的财富和人力资源来增加大学的数量我问拉泽尔,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与国际上先进的教育体制究竟有什么实质的差别?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富有思想与创造力的人才?中国在教育方面最急需要做的是哪些事情?
拉泽尔说:“中国教育的问题,我与一些人的观点可能不同,我认为这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不是质量或者方法的问题。如果你研究美国的教育制度就会发现,美国对17岁以下学生的教育是十分失败的,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比美国做得好,尤其是中国。然而美国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已经超过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典范。美国成功的原因是它拥有很多大学,而且大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竞争。如果你是一个18岁的美国人,你想接受大学教育,那么你一定能成功。
当然如果你想进入美国的名校,例如哈佛、斯坦福之类的,那么你要面临很大的竞争。然而,情况是美国50%以上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本科教育,而且哪怕没有进入名校,你同样有机会从事很重要的工作。”
因此,拉泽尔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是一个数量问题,而不是质量的问题。实际上,美国和中国的教育体制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区别。中国现在急需要做的是积累足够的财富和人力资源来增加大学的数量,增加国民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
拉泽尔还强调一点,美国大学更倾向于培养全面型的人才。在这一点上,美国与德国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的学生在接受本科教育时会学习很多方面的知识,而不是很快地专业化。拉泽尔说,他自己在读本科的时候就修过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很多科目。而德国则不是如此,他们的学生很快就转入专业方面的学习。这样做的不利因素是会使学生变得呆板,缺乏创造力。
“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的做法就一定比德国的好。”拉泽尔补充道。
拉泽尔所说的德国的现象在中国也存在。中国的学生很早就转入了专业方面的学习,一个16岁左右的孩子,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要选择是读文科还是读理科;到了大学里,专业就分得更细了,而大多数学生别无选择。
二、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人力资源的累积
拉泽尔作为人力资源领域最权威的教授,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力资源的累积。
拉泽尔说:“物质资源的增长并不困难,技术方面也很容易效仿,惟一困难的,就是如何储备更多的人力资本。现在世界最发达的一批国家,其人力资本存量也是最高的。因此,中国现在必须增加大学与专业技术学校的数量,做好人力资源的储备工作,这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另外我想补充的是,美国并不是惟一的范本,事实上德国的模式也很值得学习。他们很多人员接受的是专业技术学校的培训,其生产力也十分出色。你没有必要要求所有的人都进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专业技术培训也是很好的出路。关键的问题是,国家和企业对人力资源持续性的投资。例如在德国,当你完成专业技术培训进入工厂后,你仍然有很多机会进一步深造,提高自己的能力。”
三、中国政府在大学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两个方面的投入都应该加强
我向拉泽尔介绍了中国的一种现象:中国现在有很多职业专科学校,但许多企业却认为这些学生的教育水平不高,大多数的招聘广告都要求应聘者须有本科以上学历,企业不愿雇佣从职校出来的学生,即使雇佣,薪酬也很低。
拉泽尔说:“我想这需要一个过程。德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他们的专业技术培训体系十分完善,从中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有很高的职业技术素养。而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尽管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很高,然而中国并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这就又回到了我们上面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本身的素质问题,而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专业技术教育中。因此,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政府在大学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两个方面的投入都应该加强。”
四、政府应该寻找有效途径对下岗工人进行“再培训”
拉泽尔认为,美国关于职工“再培训”的经验,中国可以借鉴。他向我介绍了美国对学生毕业后以及下岗职工“再培训”方面的一些做法,同时,对中国下岗工人的“再培训”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