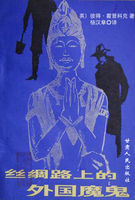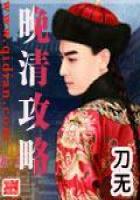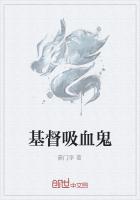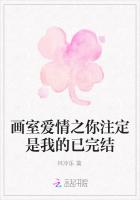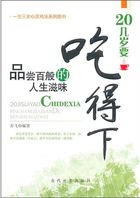最后,对皇城扩建、皇帝出巡可能导致的拆迁,宋代君主表现得比较克制。如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车驾行幸”,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没有下令拆迁、封路什么的,而是简化了仪式,“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这简单有点不可想象。又如南宋时,高宗说:“将来郊祀诣景灵宫,可权宜乘辇。此去十里,若乘辂则拆民居必多。”辇是轿子,辂则是皇帝的专用礼车,要用四至六匹马来拉。临安人多路窄,皇帝郊祀如果乘辂,势必要拆迁太多人户,宋高宗不愿意因此大搞拆迁工程,便主动降低了皇帝出行的规格。
不管是设“城管”,还是“搞拆迁”,无非是在“自发的繁荣”与“管制的秩序”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放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上,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历史性的博弈:是退回到坊市制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还是顺应时势之发展,尊重市民社会之形态,并忍受一定之代价。对于城市的主政者来说,那种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宋初曾经试图恢复坊市制,如谢德权重设禁鼓,便有此意。但这种与市民日常生活为敌的审美秩序,终究阻拦不了内在于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坊市制最后还是不知不觉间瓦解了,生活在仁宗朝的人们突然发现,“二纪(近二十四年)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掌禁鼓的官职)废矣”。到北宋中后期,宋政府对市民的侵街建筑,也很少有“过当拆屋”的行为了。这意味着,北宋政府已经承认既成事实,在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之前,克制住权力的冲动。
《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北宋繁荣景象,就是这样形成的。
皇帝也不敢强拆迁
11世纪的北宋汴梁(开封),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人口超百万,“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在那个时代,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有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来。《东京梦华录》:“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我们现在展开《清明上河图》,或者翻看《东京梦华录》,还能够领略到扑面而来的北宋东京的如梦繁华。
不过,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宫城,可能又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宽阔。甚至站在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所以后来官府干脆禁止市民在丰乐楼的顶层眺望,以免他们“下视禁中”。
宋朝宫城为什么格局不大?主要的原因是,汴梁城是从唐代的州城发展起来的,宫城的前身只是节度使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长安、洛阳这样的故都相比。赵宋立国后,宋太祖曾按洛阳宫殿的模样,扩建了汴梁皇城的东北隅,“建隆三年(962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宋史·地理志》)。虽然号称“壮丽”,其实周长也不过五里,而明代北京城的皇城周长为十八里。
宋朝的皇帝不想将皇城扩展得更加阔气、大气一些吗?肯定想。但如果这么做,首先必须面临一个问题:拆迁。这是因为,汴梁城跟宋代之前的城市有点不一样,以前的城市是权力规划出来的,显得工整而呆板;汴梁则是自发“生长”出来的,显得杂乱无章,而又生机勃勃。宫城之外,都是密密匝匝的民房、商铺。不论从哪个方向扩展宫城,都势必要拆掉一大批民居、商店。
拆迁,不就是今日城市化过程中的家常便饭吗?这还不好办吗?嘿嘿,在宋代,还真有点不好办。据《宋会要辑稿》,雍熙二年(985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宫失火,让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下了诏书,提出了建设规划,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太宗一看,要拆迁太多民居,便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停止扩修宫城的计划。
另据《宋史·地理志》,太宗可能还曾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搬走。宋太宗没有今人的胆魄,不敢搞强拆,只好作罢。现在有一些杂文、评论作者,将发生在太宗朝的这桩事情安到宋仁宗身上,并作了夸张其词的演绎。比如有篇文章说:“宋仁宗因皇宫太小,打算扩建,于是就让大臣与拆迁户协商。拆迁户们拒绝了,给多少钱他们都不搬,事情就这样僵持着。最后宋仁宗退步了。于是北宋就有了有史以来最小的皇宫,相当于一个节度使的府邸。”其实这是以讹传讹。以宋仁宗的俭朴、宽仁性情,我觉得他不大可能提出扩建宫城的计划,因为他会觉得居住的地方已经够大了。这倒不是我的臆想,有史为证。《宋史·仁宗本纪》记述:“有司请以玉清旧地(玉清宫失火烧掉了)为御苑,帝(仁宗)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
两宋诸帝当中,宋徽宗算是最爱大兴土木的一个了,比如劳民伤财的“艮岳”便是这个人搞出来的,这也埋伏下北宋灭亡的祸根。但,即便是这么一个爱折腾的君主,也不敢大搞拆迁。崇宁五年(1106年),宋徽宗想为赵宋皇室的王孙公主“建第筑馆”,但京师之中,“居民繁夥,居者栉比,无地可容”,修建王府,必须拆迁。宋徽宗“深虑移徙居民,毁撤私舍,久安之众,遽弃旧业,或至失所。言念赤子,为之恻然”,所以放弃在京城内建设王府的设想,只令于汴梁南郊“展筑京城,置官司军营”,并下了一道诏书:“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
靖康年汴梁被金人攻陷,宋室南渡,以临安(杭州)为“行在”。临安皇城也是比较狭小,宫殿规制简朴,甚至陛阶只有一级,“小如常人所居”。宋金和议之后,皇城陆陆续续有扩修,不过宋高宗也是比较注意拆迁的问题。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十四日,宰相进呈了一个报告,说临安府欲将近城僧舍拆掉,建成行宫。高宗制止了这个计划,说道,“僧家缘化,营葺不易,遽尔毁拆,虑致怨嗟。朕正欲召和气,岂宜如此?”至于行宫,“但给官钱随宜修盖,能蔽风雨足矣”。当然皇上的行宫不可能只是“能蔽风雨”而已,但那几间“近城僧舍”确实躲过了被拆毁之劫。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宋代宫城之所以格局不够开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都对拆迁民居的事情颇为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大拆大建。那么,为什么贵为天子都不大敢搞拆迁呢?我不相信赵宋皇帝个个都长着菩萨心肠,都会“言念赤子,为之恻然”。宋朝以儒立国,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响甚深,我认为当时朝野上下有一种共识:夺民私产、逼民搬迁,是很不体面、很不道德的事情。这种共识经过培育、累积、感染、沉淀,形成为一种无形却时时可感知的风气,让皇帝在展开拆迁图纸的时候感受到强大的道德压力,不得不有所节制。
即使皇帝心理强悍,执意要扩建宫城,拆迁人居,也未必能过士大夫这一关。宋代已发展出严密、丝丝入扣的君臣分权制衡制度,君主不加节制地大兴土木之举,通常会为执政的士大夫集团抗议、阻挠。来看一个例子,宋仁宗继位时,因为年幼,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天圣八年(1030年),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几乎烧成灰烬,章献太后向大臣哭诉说:“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几尽,惟一二小殿存尔。”大臣都听出太后的意思,是想重修玉清宫。宰相吕夷简反对,说上天的惩戒如此,万不可重修。给事中范雍说得更为激烈:“这玉清宫还不如烧光了。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另一位宰相王曾也反对重建玉清宫。太后只能息了念头,只是将烧剩的两殿略为修葺。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增建另两殿。
市井民间的繁荣,恰恰正是以国家权力的节制为前提条件的。这个道理,一千年前的赵宋君主已经明白了。据《北窗炙录》记载,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古人能明白,今人呢?
虽然宋代的君主由于不敢大肆拆毁人居,在皇城扩建方面显得比较克制,但是,宋代还是有拆迁的。出于建设某项公共工程之需,比如扩展街道、修筑城墙,都免不了要拆移商民的住宅与商铺。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宋真宗曾令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即将侵占街道的违章建筑拆掉,不过因为当时“方属严冬,宜俟春月”,又下诏暂停了拆迁。
那么宋代的拆迁有没有补偿呢?有的。中国自古承认私有物权,拆迁作为对私有物业的征用,当然必须做出等价的补偿。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正月,因为要开挖汴梁新城四面壕沟,不得不“移毁公私舍屋土田”,朝廷便委任了一个叫做杨景略的官员,专门负责补偿工作,对土地被征用的民户,“估值给之,或还以官地”;被拆迁的民坟、寺舍,则由政府“拨移修盖”。
从这次拆迁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宋政府对拆迁户的补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实物补偿,即由政府另拨给官地、或者另造房屋;一种是货币补偿,“估值给之”,即按照房地产的市场价,给予赔偿。但具体赔偿多少钱,史料没有记录。
不过,元丰六年闰六月的另一次拆迁,则留下了政府补偿标准的记载——当时开封府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市容市貌整顿,按规划,城墙内三十步范围的官私建筑物都要拆迁,以便留出足够的城市公共空间。负责拆迁工程的是开封府的推官祖无颇。他统计了工程所涉及的拆迁户数目,并一户一户参验地(房)契,再根据当时开封府的房地产价格,计算出被拆迁物业的估值,总共有“百姓屋地百三十家,计值二万二千六百缗”。算下来,平均每户可获得政府补偿170多贯钱。朝廷批准了这个拆迁补偿标准,由户部拨款支付。
每户170多贯钱的补偿到底是多是少?以北宋时期铜钱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大致相当于今日10多万人民币。以当时开封的物价,繁华地段“寸土寸金”,170多贯钱肯定买不了一间像样点的房子。但这次拆迁的房屋都在城墙附近,属于偏僻之地,房价毫无疑问要远低于市中心,每户170多贯钱的补偿是参照时价计算出来的,应该说是合理的。北宋前期,在开封府下辖的中牟县,100贯钱就可以购买到一套很好的住宅。
上面说的乃是北宋的拆迁补偿标准,我们再来看南宋的拆迁补偿。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六月,由于“皇城东南一带,未有外城”,宋高宗命令“临安府计度工料,候农隙日修筑”。高宗说,需要多少钱,临安府请先做个预算出来,报给尚书省,从皇室的内藏钱中拨款;尽量不要拆迁“民间屋宇”,如有拆迁,务必“措置优恤”。
当时负责拆迁补偿的官员叫做张偁,负责筑城工程的官员叫杨存中。七月份,杨存中向皇帝呈交了一个报告,大意是说:根据筑城图纸,臣等做了实地勘察、测量,划定了建设路线,现在要修筑城墙的地方,十之八九是官府的“营寨教场”,只有少数“居民零碎小屋”需要拆迁。等筑城完工后,“即修盖屋宇,依旧给还民户居住”。高宗同意了这个筑城方案。
张偁也向皇帝报告了拆迁补偿措施:“所有合拆移之家”,如果是业主,则在附近官地中拨给一块同等面积的宅基地;如果是租户,则由政府盖造公寓,“仍依原间数拨赁”;新城内外,只要是“不碍道路”的屋宇,则“依旧存留”。此外,政府对所有的拆迁户,都补偿“拆移搬家钱”,业主每一间房补贴十贯钱;租户则减半,每间房五贯钱,另外五贯钱给业主。这个拆迁补偿方案,高宗皇帝也批准了,“出榜晓谕,候见实数支给”,即禁止经手的官吏克扣补偿款。按南宋初的物价,十贯钱,刚好可以在临安府建造一间民房。应该说,这个补偿标准,不算高,但还属于合理范围。
值得指出的是,租户也能够获得一半“拆移搬家钱”,表明政府对租户权益的重视。在宋代,由于商品经济、市场交易的发达,私人物权已经发展出多个可相分离的层次,比如一个房屋的物权,可以分为所有权、占有权、用益权、典权等等。租户能够获得赔偿,说明独立的用益物权是得到政府承认的。
从宋代的拆迁补偿来看,我们大致可以说,宋人的私有物权显然是得到政府的尊重的。一个尊重民间私有产权的大宋,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宋朝的“福利国家”气象
宋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说它崭新,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革:原来旨在保证“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被“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市场所代替,庄园经济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被基于人身自由的租佃制所取代,国家承认人民迁徙之自由,商业受到前所未有之重视。而随着商业的展开,城市的繁华,人口的流动,贫富也明显分化,乃至产生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这个群体不仅隐藏在乡村,而且流浪在城市街头,变成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宋代政府的面前。
这个时候,建立起一个为贫困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救济的国家福利体系,就显得特别迫切。而且宋朝“以儒立国,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儒家的“保息”思想也要求朝廷负起养民之责。正是在这样的内(价值追求)外(社会需求)压力下,赵宋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去构建一个完备的国家福利体系。
国家福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其实很早,《周礼》中就记载了六种“保息”之法:“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不过在宋代之前,国家福利并未实现体系化,多为临时性救济,带有备荒赈灾性质。宋代则建立了一套覆盖面极广的福利救济体系,救济的对象涵盖了孤寡老人、残疾人、乞丐、弃婴、孤儿、贫困人口等所有无法自立的群体,提供的福利覆盖了国民“生有所育、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等层面,可谓“从摇篮到坟墓”均有国家救济。《宋史》说“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真不是溢美之词。
现在,就让我们穿越到宋代,以“生老病死”为序,近距离观察一下彼时国家福利机制的运作。
先来说“摇篮”即“生”的福利。
宋代的“摇篮”福利可以分为补救性救济与预防性救济两大类。预防性救济是指国家在发现贫家妇女怀孕之后,给她们提供生活补贴,以免穷困人家因养不起孩子而溺婴、弃婴。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高宗下诏在全国推行“胎养助产令”,诏曰:“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具体做法是,每一家贫困户发钱4000文(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这笔经费来自国家征收的“免役宽剩钱”。南宋的州县还设有“举子仓”,即由地方政府向贫家产妇发放救济粮,一般标准是“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举子仓的仓本来自国家常平仓、官田收入及富人的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