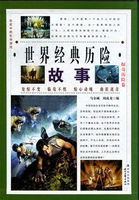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天冷得人只有不停地跺脚,契卡办公室里连火炉也没生,几个穿皮衣的人围着她和叶莲娜,冷冷地一言不发。
她不知道叶莲娜的中国姓名,只知道她从浙江省来,是一个富商的女儿,高大健壮得象短跑运动员,正是她的家庭成份和自命清高的个性使她身入囹圄的。
皮衣袖口磨得光秃秃的那个契卡头子放眼冷冷打量着她们,听凭她俩满口呼冤,诉说自己根本不是托洛茨基份子,一点儿也没有反对斯大林的意思。也许俄语方言太多,那人一点也没听懂她们的表达,或许这类事件他看得太多,看把戏一般瞧着两个又哭又叫唤的女人,一点儿表情也没有。
女人不叫了,她们叫累了。
契卡头子用长满黑毛的大手在两个女人身上乱摸,摸得女人浑身发抖。他摸着叶莲娜的屁股冷笑,用力一捏,叶莲娜痛得一声尖叫。紫苏听到他叹惜说:“可惜了,一对来自东方的小母驹。”
叶莲娜不堪侮辱,扬手给他一耳光。
那人怔怔的,没想到到了这个地方还有人敢动手,半晌狠狠地骂了一句:“母猪!我要你想死也死不了地遭罪。”
门推开了,彦来小心慎重地走进来。他带着他的老师谢苗诺夫写的一封信,手里拎着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两瓶伏特加。
彦来说:“先生们,看来咱们发生了点误会,对不起,这女人不是托洛茨基份子李少然——也叫安德留拉的妻子,她是我的爱人,我想求个情保她出去。”
契卡头子冷冰冰地看着他把酒放在桌上,看完谢苗诺夫的信,脸上露出丝奸笑,说:“好,好的,你看,你打算用什么方式表明这女人是你的爱人?”
彦来一点也没犹豫,上前一步抱住紫苏,贴着她那苍白的嘴唇就是一阵深吻。
吻完他拉起紫苏就走。
紫苏挣脱了,无言地望着绝望的叶莲娜。
彦来说:“先生们,咱们是不是再商量……”
“滚!快滚,千万别让我后悔放掉一匹母驹。”
彦来只好牵着紫苏走了。
这一走,让紫苏内疚了一辈子。
后来在上海,他们遇到了一个衣着破旧的同学,那人刚从俄国回来。他说,卖了,什么都卖了,国格、人格,连灵魂都卖给老毛子了。他是在远离莫斯科的西伯利亚一个刑事监狱里认识那个刚来时高大健美的浙江姑娘的,没有姓名,只知道她叫2758号囚犯。多美的姑娘啊。她一到地方就被囚禁在一个单监里,天还没有黑,就让五个看守脱得光光的,当着满监杀人犯、抢劫犯的面把她轮奸了。她边哭边喊“妈妈”,那几个性欲狂一个人强奸,另外几个人一把一把扯她的阴毛,大叫大喊说是“杀野马”。那个惨呀。
从此她不用像其他犯人一样上工,她的工作就是满足看守老毛子的性欲,一天披张又污又烂的毡子,衣服也不让穿,老毛子任何时候,不管白天黑夜,想上扯掉毛毡就上,满监常常传来她杀猪一般的叫喊。
一个多下来,她就变得脱了人形,看见人就怕,一句话也不说,坐久了,就自己念:“我是中国人,叶莲娜,二十七岁。”
日子久了,看守也倦了,何况又来了新的漂亮女犯人,也就不管她了。但是她的景况并没有好转。人说死鱼也有烂老鸹啄,几个在厨房里帮厨的犯人看上了她。帮厨的犯人在犯人里地位高一等,他们可以借开伙分食品的机会支配一切犯人。他们就借送食品的机会,摸进叶连娜的囚室强奸她,有时看守发现了,也仅仅付之一笑。有次看守为了取乐,还专从犯人里挑了五个精壮汉子,放进去轮奸她。几个看守在外面看得又拍手又跺脚,高兴得很哩。
当然,这在那所彼得大帝起就建立起来的监狱里是常事,也不仅仅针对中国女人,对他们自己的女人他们一样践踏。叶莲娜错就错在她比别人漂亮和性感。
后来不久,她就死了,是半夜死的,清早被人发现时,早就冷硬了,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埋葬了她。
不知怎么的,关在小房间里的紫苏不时想起那个曾经和她关在一起的女人,自己差一点就跌进了她相同的遭遇,想起那个面无表情冷冷地向她诉说过这一切的人,时而这个画面,时而那场情景,把脑子装满了,乱糟糟的。她又想起那个姓张的连长,不知什么时候他会摸进来,不顾廉耻地收拾自己。
天不知什么时候黑了又亮了,只有窗外那个被点了天灯的人头上的火没息,一晃一晃地明灭着,象幽冥地府里的鬼火。
院门又被人从外面拍响了。
这次拍得很有节奏,又轻脆又短促。全幅武装的兵呼地拉开大门,一个中等个粗实的人领着一行人悄然走进门,卫兵惊呼了一声“古秘书长”,紫苏看到李韶九急急迎上前,两人有礼有性地握手,问候。
来人是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他是奉总前委命令来富田加强肃“AB”团力量的。他交给李韶九一封总前委的信。
清查运动更加惨烈地展开了。
段良弼等人再次遭毒刑拷打。段良弼并没有屈服,他从自己十多岁参加革命说起,把过去很少炫耀的斗争历史一桩一件列举出来,企图证明自己不是“AB”团。李韶九说了句令人深思的话。为写这篇小说,作者后来不止一次从各种文件中查对过原文。他说:“我不与你讲理,我只有七项刑罚,第一项就是这打地雷公烧香火……无论如何你要承认是AB团与说出你们的组织,否则给你一个不生不死。”
李韶九等人一共抓捕了“AB团分子”一百二十多人,他们刑讯的原则是“不招供,不停刑”。
严刑之下,被捕人员全部被迫承认自己是“AB团分子”。
不少人被折磨至死抬出去扔了。
大门又被捶得乱响,杂夹着好多女人的喧天呼喊。紫苏抬起糊糊粘粘的泪眼,看见大门一开,几个女人一阵风跑进来,抱着捆绑着的男人就哭。紫苏认出了那个剪短头发穿列宁装的年青女人是省行动委员会秘书长李白芳的妻子,她发着怒戟指李韶九大骂,温顺的周冕的妻只顾抱着垂死的丈夫哭泣,马铭的妻子呜咽着试图放松绑在马铭身上的绳索。一时女人哭,男人喊,把个森严得令人畏惧惊恐的气氛搅了,刑场一片混乱,枯树上的老鸹在天上盘旋,绕着血腥的庭院哇哇乱叫。
起风了,是十二月少见的白毛风。
一时天怨人怒。
李韶九发怒了,他要教训这几个敢来闹事的女人。一声令下,女人们全被捆绑起来,一阵乱鞭打得女人本来就嫩的身上血肉模糊。女人并不比男人坚强,不久她们都供认参加了“AB”团,或被打昏让人按着手指在悔过书上按了手印。
事情发展到这里还没有停止。
最令人惨不忍睹的一幕终于发生了。
几个女人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请注意上文的引号。作者一个字也不敢编造,全是从有关文献中抄来的。
段良弼等受刑不过,被迫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人“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
后来,解放军将军萧克在一九八二年著文回忆当年事,他写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空气中充满人血的腥气,被火烧焦的人的体毛糊臭味到处都是。几个女人失去知觉,不知羞耻地叉开大腿直挺着身子瘫在地上。
紫苏看得惨叫一声,一头晕倒墙边。
不知过了好久,她抬头一望窗外,只见三星在户,月光皎然,四周静得怕人。
一个人就在墙外的窗下,用口带很浓的长沙口音的湖南话命令:“去,把带队的张连长唤来。”
那是李韶九令人恐怖的声音。
一阵军人的整齐跑步声。是张连长到了。
“张连长,辛苦了。”
“没什么,应该的。”
李韶九话锋一转,阴沉沉地问:“张连长,咱们关押的人犯中间还有个人没动吧?你在干么事哟?有私心?”
紫苏一听,犹如一阵闷雷在心坎上响起,脑子一震又要昏去,死期到了。
张连长一阵沉默。
可以想象出李韶九星光下那双刺人的眼睛。
“我……我这就去带。”张连长回答说,口气迟迟疑疑的,有点不情愿的拖泥带水。
李韶九转身走向刑讯桌。桌子被罩在那棵大枯树的阴影下,月光下黑白分明。
紫苏抚摸着自己的小腹,小腹有点硬,胎儿一动不动,想必胎死腹中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难道长时间母体受到惊吓,胎儿也受到了影响?这样也好,一想到火烧阴户必然会烧到孩子,紫苏想还不如现在就死了算了。
张连长沉重的脚步声来了,踢踢踏踏的,像要把人的肠肠肚肚牵扯出来一样。
紫苏牙一咬,干脆闭上眼睛等死。
脚步声穿过门廊,走向西屋,木栅门开了又关了,脚步声乱杂杂地,象在推拉着什么重物,又渐行渐远。
紫苏不明所以,挣扎着跪起来抬眼望庭院,见张连长带人把个瘦小的人犯推到李韶九坐的桌子前,有战士大声报告:“AB团漏网分子,嘿,差点让他个狗日的麻脱了。”
李韶九一下站起来。
紫苏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和张连长象两尊风侵蚀过的石像,一动不动地对峙着,两个人都没说话。
被带进场的是姓杜那个告密者。
场院里死一般沉寂,后来就是一阵紧似一阵皮鞭抽打人体的声音和被打人的尖嚎,双方的气都发到了这个可怜的告密者身上。
庭院大门吱呀呀地开了,又有几个被整死的人被拖出门,一具死尸的脚“乒”地一声撞在门框上,发出象干枯的树丫枝拆断的声音,在沉重的夜色里分外刺耳。
紫苏的神经绷得太紧,随着这声折断肢体的脆响,好象有人用锋利的小刀在哪根主神经上轻轻划了一下,全身骨肉一下就散开了,她目光一散,身子象塌山一般乒然倒下。
她感到自己在水上漂,月亮浸泡在血水里,满天血腥的星斗,特别令人眩目,身旁周围是柔软的水草,缠得她动不了身,张嘴也叫不出来。
腹中的婴儿又动了,有股暖暖的水从下体流出来,她闻到一种刺鼻的腥味,心里有些放松,恍恍惚惚中就看到门开了,姓张的那个连长轻手轻脚影子一样飘进来。
象有人关门。
她闭上眼,绝望地等待叶莲娜的呼唤。
空荡荡的屋里传出男人急促粗野的呼吸声。
那日子好久,好难挨。
一只男人的大手有力地按在她的乳房上,手在颤抖,两只手指轻轻夹住她的乳头。
心一紧,紫苏顿时失去了知觉。
小窗外有不知名的野虫在鸣叫,屋檐遮住了月亮的光照,黑糊糊地在窗上画出道宽宽的黑线,粗糙的雕花窗格挡住了外来的山气,屋里空气太少,闷得人心里发慌。
远处有一阵野狗沉闷的嘶叫,大约在争抢死人的肉体。
门缝里有双冷冷的眼睛在黑暗中大睁着,尽力要看清屋里的动静,可惜屋里的人一无所知。
紫苏几十年后尽力回忆当晚的情形,可是无论她怎么努力,那段历史就象被人强行从照相机里扯出的胶卷,一下子暴了光,什么也没留下。
她只记得那天夜晚好冷。
是令人从心灵凉到肉体的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