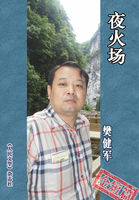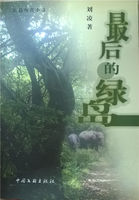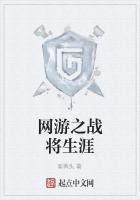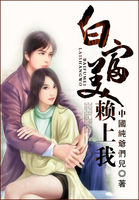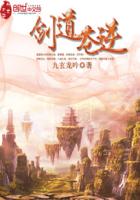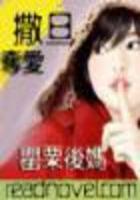查阅历史文献我们知道:就在项英准备主持调和会议的时候,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重新作出决议,并派出专人赴江西解决问题。可以查到的是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文件发放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地方党部。
文件上写着: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全权调查解决这一问题。
文件虽然没有提出处理富田事变的意见,但是倾向已经十分清楚,并赋予代表团惊人的权力,他们甚至可以改组苏区中央局。从事后中央派出的调查团成员全部担任苏区中央局要职的历史事实看,他们从上海出发就肯定负有重新“组织中央局”的使命。
一切有关富田事变的历史走向基本确定。
不久,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总前委紧急会议决议送达上海的中共中央,决议说:
“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那年的毛泽东38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他已经走过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龄。他手握二万雄兵,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以大气磅礴之笔,写下了让后人永志不忘的《渔家傲》: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刚刚打了胜仗的毛泽东,地位在上海租界里那批书生中间陡然上涨,他们决定把中共中央搬到苏区,摆脱受制于人的遥控指挥地位。于是,3月28日有了对富田事变的最后决议。
首先,文件把富田事变定性为“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
然后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
这就决定了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命运。
几十年后,人们几乎有意或无意识地忘了,那是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发出的一个文件作的结论。每当我们学习党史的时候,总会背诵出一大串“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说他们主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一直到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几乎都是后面的领导否定前面的人所做的一切工作,不“左”即右。他们使用的也不是简单的数学上负负得正的方法。按说“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如果把每次中共领导编上一二三四五六号的话,那么一三五正确,二四六就必然错误,反之亦然。但是,我们的党史却把单数双数一齐安上各种主义的错误,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观。当然,平心静气而论,这种现象也不是不能存在。问题这就出来了,所有的各种错误的决议之中,唯有王明这个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在我国大多数党史研究者中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一致认为它是正确的。
也许是因为与毛泽东的兴起有关。
为尊者讳。
中央文件中提到的代表团从上海出发了。他们由三个人组成,中共党史上把这三个决定毛泽东命运的人叫做“三人团”。
他们是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
职业革命家任弼时是湖南湘阴人,时年二十七岁。湘阴那片沃土为中国近现代史培育过无数风流人物,好多人改写过中国的历史,或者影响过历史的进程。如清季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左宗棠左季高,背上一身恶名后又领兵驱逐侵占我国新疆的沙俄军队,收复祖国领土,在新疆广植“左公柳”,使人民受惠到今,人称“新植杨柳三千棵,引得春风度玉关”第一人。又如郭嵩焘,中国第一任外交官,一八七六年以礼部左侍郎身份出使英国,后又兼任驻法大臣,对清末的洋务运动作出过卓越贡献。民国年代湘阴更是英雄辈出,国共两党不少精英都在这里看剑饮马,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他们的血管里流尚着湘阴人倔犟的热血,骨子里浸透了总理天下的诗书,以天下为己任,三湘子弟,人满天下,誉满天下。
寒春四月湘阴人任弼时走出上海,绕道福建进入江西的时候,我们猜想不到他当时的心情,他也没有日记、文件之类的东西供我们查询。想来二十六七岁时就肩负大任,作为口含天宪的一方大员,负责处理一个省的问题,应该是雄姿英发,春风得意的景况,但他是一个沉稳内向的人,不会有那种外露和剑拔弩张的锋芒,从他挂着那幅很厚的眼镜和唇上浓浓的髭须就看得出来,他一路上已把中央精神反复琢磨,推敲,吃透了中央领导的意图,执行中央决议的方案基本已经形成了。
从上海开出来的列车一离站,王稼祥就靠在车椅靠背上休息,周围拥挤喧嚣的旅客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尽管有卖小吃的商贩不断走过吆喝,躲查票的人挤来挤去,他还是闭着眼睛养神,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比任弼时小两岁,1924年在上海大学读书,1928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成共产党员后,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型的革命者,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干事,比起任弼时来,只能算个后生晚辈,虽然年龄相差不大,他却显得一脸书生气,而那时任弼时已经担当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行动委员会书记了。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当然在他的领导之下。
王稼祥是个党性很强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以后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大胆发言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史实上看出来。不过他当时刚出茅庐,免不了经验不足。
火车还在哐铛哐铛地摇摇晃晃着,车厢内充满了汗气和劣质烟草味,沿途是吵吵嚷嚷争着上下车的人,王稼祥却靠着椅子睡着了。
“三人团”中年纪最小的是顾作霖。一九0八年生,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相对前两人来说,他的名气要小些。名气的小是因为他只活了二十六岁,就是说到苏区三年后他就牺牲了,牺牲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着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红军第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年纪青青的二十三岁,顾作霖却有惊人的经历和业绩。他是江苏嘉定人,字冬荣,十七岁加入共青团,十八岁加入共产党,担任过共青团上海沪东区委书记、浦东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领导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先后担任过三个省的共青团省委书记,后调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之一,曾经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工作。
上海中央派出的三架马车,轰隆隆驶进八闽大地,在那儿拐了个弯,径直奔向江西宁都。
四月上旬,以任弼时为团长的“三人团”到了江西宁都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并负责传达中央精神。
四月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宁都青圹举行。
会上任弼时以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决议明确指出:
“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份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
针对项英,任弼时说:
“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
把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暴动”之后,任弼时要求“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大会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决议中基本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
大会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确定一个正确的反“围剿”战备方针。
会上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及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部分人主张分兵退敌。
毛泽东则坚决反对,他主张根据有利地形,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的军民集中兵力反“围剿”。他的主张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的支持。
毛泽东处变不惊,他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带兵的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都来参加会议并得到允许。
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他们都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这种变少数为多数的办法使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高了领导艺术,以后的遵义会上他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艺术,再次登上最高领导阶层。
会上有个叫周以栗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根据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实际经验,鲜明提出了“穷山沟也有马列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毛泽东从实践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他实践的就是马克思主义。
争议的结果是毛泽东的正确决定获得胜利,从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来看,毛泽东的战略确实是正确的。
大幕落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