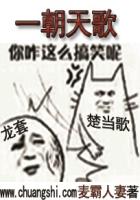门口白晃晃的日光里站着兴顺,身前的影子拖得老长,门洞里射过来的光柱里看得见细毛毛的粉尘飘浮,狗日的兴顺宽大的身板塞满了门楣,阳光把他周身镀了一层闪亮的金边。
“先生,你走,”兴顺说,眼里露出丝诡密的笑意:“俺爹会听话,会吃药的,先生,你啥也不用操心,你走吧。”
彦来也顾不了再说什么,提起医箱就走。
兴顺闪身让他出门,出门就听见老头虚弱的声音在背后说:“娃,医生是好人,万万莫要害他,莫要害他呀。”
此后身后就毫无动静,看样子莽汉子没有追出来。彦来却心跳不止,他从背后感到那汉子目光如刀,一直盯着他的后心不放,预感早迟那叫兴顺的汉子必定会追来,决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的。
也不知跑了多久,彦来站定喘了口气,抬头望望苍白的天穹,判定太阳的位置,他不敢再到旅店去,就认定东北方向走,只想绕过清风店再往前赶。他感到胸部很闷,肩上的皮箱好重,眼前有星星在乱窜,他想起了刚到二十军时的那次急行军,说是白狗子来占地盘,乘我们的哨兵忽略摸上来好多人,团部的人就跑,也是这么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他那幅金丝眼镜就是那次跑脱的,后来还挨了团长一顿骂,说是假若敌人捡到了,一定知道逃亡的人中间有知识分子,再笨的敌人也能从金丝眼镜上推论到追的是首脑机关了。幸好当时是一场虚惊。
这回就不是虚惊了。
前面当路拦了一个人。
那人正是店老板宋祥福。
宋祥福手里捏了把手枪,日光照耀下寒光闪闪的,自有一股逼人的气势,他笑了一笑,望定彦来说,走,先生,走跟我回去,咱们有话慢说。
彦来慌忙说不,你开的啥店不关我的事,我一个穷医生走一路吃一方,身上球钱没得,杀了卖人肉包子肉也不多,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让开,我走我的路,不碍你的事。
宋祥福哈哈一笑,说先生错了,我不是剪径的强盗,我是有信仰有主义的人。你先生回来时如果原路退回哩,我不会怀疑你,一定会送先人板板样送先生去南昌。我就害怕你过店不入,绕道而去,先生,你怕什么呢?我只好在这里等你,可是又怕等着你,没想到你还是撞上来了,先生,走吧,咱们回店,有话好说,说得好,你饱饱吃一顿再上路。
彦来说你说了这么多我不懂,我不懂到底犯了你们哪条店规?
“你看了你不该看的东西。”
“啥东西?”
“别装了,你看了那堆乱石坟没有?看了?那你会不会问里头埋的什么人?开店还杀人恐怕全世界哪个国家都算犯法,我会让你甩手甩脚走人么?跟我走,先生,我也不忍心杀害你,跟我回去问明白了,只要你不损害我们的利益,我们不会错杀一个的,先生,请吧。”
彦来不敢硬来,他知道那铁家伙的利害,再结实的脑袋也经不往它的一击,而脑袋一敲碎,就再也补不好了。
宋老板挥了挥手枪,笑着说,走吧,店里还有几只羊,几只肥羊在等你,说不定你们认识,还不定是一伙的哩,编着套儿想让我上套,又想立什么大功破获什么组织,你认为你们分期分批来就麻痹得了老子?请吧。
彦来就想见鬼了,平常看小说总觉得开黑店卖人肉可笑,笑那些作者编得一塌糊涂,没想自己还真碰上了。
彦来只好随他走。
宋老板说你别给我玩花花肠子,本来该把你一枪崩了就埋在这里,你看这环境多好,你可以永远与草木同伴,和日月同辉,不朽嘛,为了对你负责,我还要多问一问,怕误杀了武松也是有可能的。彦来就想你狗日的自己承认是开黑店的孙二娘,老子可不是什么武松,要是水泊梁山上有什么大学生留学生的话,那还差不多。
宋老板押着彦来七弯八拐地走,彦来也就随他的便,叫左就左呼右就右,东走西走终于又回到了清风店。
兴顺早回来了,他站在柜台后望着彦来呆呆一笑,仿佛早就预料他会被截回来一样,甚至嘴角一别还隐隐做了个怪相。
店里还坐了三个人。背对门口的那人身量极大,颈项上的肌肉一块一坨鼓起,肩宽腰细,一看就是个练过功夫的壮汉。另外两旁坐着的人正一口一口地喝酒吃腊野味,彦来觉得他们声音好熟,用心一看,不由心中暗暗叫苦,发觉这两人一个是段良弼,一个是中央大员易尔士。
对门而坐的易尔士也同时认出了一头跨进门的彦来,眼里闪出一丝诧异,立即又调头与希良弼碰了一下酒杯,尽力想装出不认识的样子。段良弼见了彦来与店老板,惊得“噫”了一声,身子一动几乎站了起来。
易尔士在桌下踢了他一脚。
这一切都没逃过宋祥福的眼睛。
宋祥福和蔼地笑,说:“同志们,请坐,何必多礼呢。”说完就指着桌边一个空位让彦来去坐,说是让同志们聚聚。
彦来下意识取下肩上皮箱,顺手放在大门旁,身不由己向空位走,心想这两个人怎么走到一起来了,店老板为啥叫他们同志呢?想着突然记起离开富田时刘敌的吩咐:不要说认识段良弼。那么对于易尔士就更不敢高攀了。
易尔士和段良弼还是自顾喝酒。
他们是昨天黄昏时刻住进店的。
本来路过清风店时日尚早,依老段的意思呢说再赶一段再歇,易尔士却辨认出了这清风店是他来时住过的地方,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心想还有什么比这更安全的地方?就领头把老段和二十军临时派的警卫魏彪让进了门。
老板还是那个老板。
伙计还是那个伙计。
久走江湖的易尔士却忽略了一件事:交通却不是原来的交通,这次带的是对交通联络暗号一窍不通的魏彪。
他们出发时二十军首长考虑到他们身带大量黄金,路上一不安全,二来负担又重,就派出了武功高强的魏彪一路保护,另外大多数黄金伪装后放在个软袋里让魏彪背着,段良弼怕魏彪负重过多影响行动,就取了80两让缝在个小布袋里缠在腰上,后来怕路上出事,又象女人捆月经带一般缠在胯下。魏彪开玩笑说老段小心,莫把你家什磨光球了,一天走上走下少不了磨哩。老段说你着急个啥?你嫂子都不急还用得了你操心?我用家什天天抵到才放心,不然半路掉了都不晓得。
骚话野话啥话都会,就是不会讲暗号。
宋老板的交通站之所以敢叫红色交通站,之所以几年不出问题,关键就在宋老板敢于坚持原则,认事不认人。对过往干部从不打听是宋祥福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不时受到上级的赞扬。几年来清风店交通站成功地掩护过刘少奇、项英、陈毅等中央高级首长,但宋祥福从不以此为傲,从不打听过往的都是谁,他对每个干部都恭恭敬敬,绝不会因为你是个普通的负伤的战士而看不起你,也不会因为你是中央高干而着意巴结,他把输送过往干部看成十几年前在上海滩偷送违禁物品,唯一的信条就是不出事,不出事生意才做得长,出了事儿壳就要搬家。
尽管易尔士进门就握住他的手说“同志你好”,他还是不动声色有礼有性地问:“九江渔牙子有信来?”
易尔士一愣,忙说我们是去九江,不是从九江来的。
见如此简单的暗号对方也对答不上,宋老板的心就一沉。他知道暗号经常在变,但这第一句一般是固定的,这人怎么一点不懂?就把头转向了段良弼和魏彪,希望他们中间有一个是带暗号的交通员。
“九江渔牙子有信来?”
其他两人更不懂,就含含糊糊地说没有,没有谁托我们带东西来。
这就出问题了。
易尔士想的是我来时路过此地你们对我恭敬热情,安安全全送我们到下一站,双方既然是熟人了,你再麻烦一次送我走就行了嘛,中国人不是说送佛送西天吗?他忽视了来时的路线是中央特科安排的,一路自然有人周到照顾,可是去时由于富田事变突然暴发,从苏区到上海的交通本应是省行委安排,现在一下打乱了,刘敌、谢汉昌本是军队干部,自然就没考虑到这个问题。至于段良弼呢?在行委他没分管这块工作,也就不了解情况的复杂性。
宋老板想的又不同。
他首先想到的是出事了。没有联络暗号住店的只有两种人:一是普通过往客商,他们不需要暗号;二是外部敌人想要打入交通站内部,以达到破获党的组织的目的。这个看来眼熟的老熟人见面就称同志,装出一幅亲亲热热的样子,可是连最基本的暗号也对不上,联系到最近苏区发生重大事件,白军频繁出击的具体情况,这三人基本可以肯定是白军的探子,利用原来交通站掩护过他的事实来进行刺探,以便破坏沿途所有交通站。那个前两天就来了的医生呢?他们是不是一伙的?医生是他们打前站的人?宋祥福又想到医生上过山,如果兴顺口不严出点问题,前几天杀人的那河水就怕要犯在医生手上,所以他决定先把医生弄回店再说,他若没在新坟上找出碴儿,把他放了也行。谁又想得到,医生真与这三个奸细认识呢?宋老板精如狐狸,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肯定没错,这几个人先前肯定认识。
他庆幸自己提前作了准备。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上级一再告诫的基本常识。宋老板首先把易尔士定成了党的叛徒,这人不久前还来过,宋老板脑子里印像还深。那大汉肯定是保镖,看他那一身紧紧凑凑的装束就知道,至于另外那个中年人,肯定在哪里见过,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到底何时何地见过面呢?宋老板一边回忆一边抬头又看了他几眼。
昨夜安排住宿时宋老板有意让兴顺去帮保镖提口袋,哪知那保镖十分警惕,绝不让伙计兴顺碰那软袋,那怕摸一下也不行。也许因为他看出兴顺另有企图,从昨晚起保镖就滴酒不沾,任其他两个客人把酒杯喝个底朝天,保镖始终不尝一滴,真是他妈一条好狗哩。
那袋子看样子挺沉,壮汉提得有些吃力,兴顺估计里头装的枪,老板说那一定是电台,狗日的晚上要向主子汇报哩。
昨日晚黑宋老板就想了一夜,到底下手还是不下手?几经权衡,唤起兴顺打算动手时,才想起山上还有个医生,生怕安排不周密让医生跑了,最后才决定罢了罢了,捱到明日早晨把他几爷子诓到一堆,再多试探几下再下手,又怕他们人多对付不了,宋老板便使出了开黑店的老祖宗孙二娘的惯用伎俩。
宋老板亲自给他们上了一盘青椒炒腊骨头,一边张罗着让兴顺给医生添幅碗筷。彦来说不用麻烦我自己来,就惴惴地走进厨房拿家什,斜眼见兴顺目光防贼般盯着他,也不敢有啥动作,拿了碗筷就回来了。
宋老板就问一路还安全吧?提醒他们要小心,说这几天突然乱起来了,也不知什么原因。老段就说我们只顾赶路,也不晓得出了啥子事。宋老板就试探着小心地问:听过往客商说富田老家杀人了,杀了一大批,不知道同志们清楚不?老段一听脸色马上一变。他是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说是好人杀坏人他当然极不情愿,说坏人杀好人现在党中央还没定论,作为党的一级组织的代表他不敢乱向外宣传,就只好拿酒杯出气,嘴巴含着杯沿不松口,不松口自然也就不用回答老板的问题了。
易尔士站在他的立场自然更不愿乱表态,就批评说你这个同志咋这么没原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最起码的一条你还是要整清楚搞灵醒的嘛。宋老板就想,那最该搞灵醒的就是接头暗号,这倒是非整清楚不可的,不得已就启用了紧急时刻才动用的暗号。
他竖起食指晃了三下,问:“井漏了?”
这是一句几方的交通员都必须知道的红色警号,当时的暗号分成三种颜色。绿色表示安全,可通行;黄色表示有危险,抓紧行动;如果动用红色暗号,那就表示情况万分危急,赶快撤。其中暗号变化最大的是绿黄二色,因为怕出乱子,上级按时不断更换,因此不管是上海中央、中央苏区、红一军团或其他有关单位都有专人负其责,以便随时掌握变化。唯有这红色暗号永远不变,只要红色暗号一发出就意味着出事了,接到暗号的人回答一句“娃儿哭了”立马就走,发信号的人拼了命也会保护的。
老段等几人不但没回暗号,当然他们也回不出暗号,反而继续悠哉游哉地喝酒,只有医生彦来答了一句:漏了就漏呗。
宋老板还不死心,怕他们是去办私事而没有交通护送的我方人员,因为其中有两个毕竟还是面熟嘛,就嘿嘿一笑打个圆场,说同志们一路辛苦了,要出门特别是出远门,该先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嘛。
易尔士一听就品尝出老板话中有话,马上意识到可能手续上出了问题。
“来客喽!”柜台后的兴顺一声吆喝,分明提醒有陌生人进店。
一个当地妇女打分的年青女子走进店来,腆着个肚子显得很吃力很累,显然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女人挑门口一张桌坐下,细声细气叫了声“来点吃的。”
那声音惊得彦来一颤,偏头一看,那女子正是自己千辛万苦遍寻不得的紫苏,没想到她孤身一人闯进了这黑店。
女人也正抬头打量这方的客人。
她一眼看到的是正面坐着脸对脸瞧她的段良弼。
女人一下立身站起,冒然叫了一声“段书记!”喊完就要过来,突然听到有人用俄语喊了一句:“不,危险,不要过来!”
稍一偏头,她就看到了她的新郎正焦急地巴望着她,又喊了句“不”。
一声“段书记”猛然提醒了宋祥福,他一下子辨认出了一年多以前在小店住过一宿的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
没错,就是那个“AB”团的头子段良弼。
富田事变后没几天,总前委政委毛泽东同志亲手写了一篇六言体的“讨逆檄文”,好多儿童都会唱:“段谢刘李诸逆,叛变始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几十年以后这篇檄文基本没有人能记全,但肖克同志回忆说,其中有两句肯定是“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连。”
就是那个名例榜首的段良弼。
杀心就是在那时起的,
彦来看到了宋老板眼里飘过的那丝杀气。
他感到黑店里的屠杀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