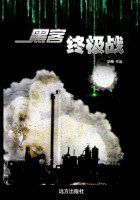她垂首不再言语,千年前,迦兰若是东辰天镜的女主人,她虽嫉妒有之,却不敢动念,长宁似神似魔之性,连天君也忌惮几分,迦兰若自幽冥而出,在这九重天中仍有不适应,灵气昌盛的膳食每每都吃的很少,长宁为此几乎竟又从幽冥提升了两人上了九重天,更为她们更换仙骨,只为负责迦兰若的吃食,天君只此不合规矩,却也不敢多加阻扰,只让岚禾做些汤羹去东辰天镜看看,她本也是领命而为,却不想她的汤羹倒是正对迦兰若的胃口,迦兰若心下高兴便送了她一只青笛,她倒是送的随意,却不知整座蓝山青木才换这一只青笛,岚禾面上欢喜,心下却愈发嫉恨,可这千年已过,不曾想这只她从未再摸过的青笛竟救了她一命,她心下惨然,却也知这不过是自己的命数。
长宁眸光又是一转,伸出食指朝我轻轻一指,“还有你……”
他话音刚落,我只觉有一团火焰在心口翻搅,似要划破我的皮肤烧毁我全身,我意识深处是红色的火焰,如鲜血一般妖娆,突然间,我又像是坠身冰泉之中,所有的火焰被浇熄,我却疲惫的难以睁眼,我听见商皇的声音如一阵清风飘至耳边,“她扔瑞雪,只为救梦西庭。”
梦西庭的声音随后响起,“她为雪妖,与雪兰本就同根。”
长宁看着商然,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随后一阵轻笑,仿佛像是自嘲,正欲离去之时,他转身看向梦西庭,“你可愿要回你的火翼?”
梦西庭微微一愣,“火翼离体千年,许是早已化了尘埃。”
“火翼一直放在东辰的深渊缝隙中,她将它保存得很好。”
梦西庭暖暖的笑了,“我以为她那时不过一句戏言,不想她真的做到了。”她深深地看了眼紧抿着唇的苍邪,复又说道:“我以火翼为她做嫁裳,幽冥,我是再也飞不出去了的。”
他突然笑了,似真似假,“你要什么?”
梦西庭道:“我要见她一面。”
苍邪的身体微微一颤,长宁依旧是那副云里雾里看不真实的笑,“好——”
他飞身离开,白雀跟在身后,白衣飘然像是一抹不食烟火的云团,终究一片衣角也未落下,自他走后,雪停了,西陵站了起来,看着他消失的地方久久不动,苍邪走至梦西庭的身边,默然的看着她,只见她宛然一笑,“帝君,她醒了。”
许久之后他才开了口,“谢谢。”
她仍然笑着,“去寒山墓吧,替我见她一面。”
“西……庭……”
“我知迦兰若是长宁的魔障,却也是你的,逃不掉的,便是死,也逃不掉的。”
他重重一叹,“我送你回云影殿。”
一直未曾说话的西陵突然开口,只说了五字,“寒山墓动了。”
苍邪的身形一动,突然又停了下来,看着梦西庭,只听梦西庭道:“去吧,已错过了千年,不该再错了。”
苍邪终是转身飞去,黑色的衣袍被夜空掩埋,只剩下落寞的星宿和盘旋而舞的火龙,商然抱着我离开,与梦西庭擦肩而过时,问了句,“不后悔吗?”
她道:“苍邪,也是我的魔障。”
既为魔障,便是舍身成这世间大凶之物,梦西庭的那句‘死,也逃不掉的,’竟成了我的梦靥,我在那个梦里拉着一个同我一样一身白衣的女子,不知是对谁欢声笑着,五彩的霞光映照在他脸上,甚是好看,我乖巧跟他介绍着我身边的女子,“她叫夜歌,满夜星辰齐声歌唱的夜歌,多好听的名字,她也是雪兰花妖了,你不是说天地间只有一只雪兰花妖吗?错了吧。”
他微微愣神,在我脑门上轻轻一点,“是雪夜鸣歌孤唱。”
“是是是,大学者,可是你还是错了,原来你也有错的时候,还是被我揪住的小辫子,哈哈哈……”
他在我脸上轻轻的掐了一下,随后又正色道:“笑不露齿,看来礼官们又该罚了。”
我耍赖道:“谁叫我嘴大呀。”
他嘴角微微上提,“既然嘴大为何不多吃些,今日早膳你又只喝了雪露?”
“诶,我觉得自己哪里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嘴刁挑食,所以为了不让您老担忧,我就把夜歌带来了,她做的膳食可好吃了,不对,应该说经过她手的东西就没有不好吃的。”
他看着我身后的女子,“夜歌?”
夜歌突然脚下一软,便跪了下去,我一恼,将跪在地上的夜歌拉了起来,气道:“你吓她作甚?”
“这般胆怯,若你惹出祸事来,她如何护你?”
“我护着她不就好啦。”
“你?”他又笑了起来,“你就是个狐假虎威的主,在你身边者,必是忠你护你之人。”
我拉着他的衣角,撒娇道:“好啦,有你这只老虎护着我们两只小狐狸,谁见着了不是闻风丧胆的跑了呀。”见他不语,我放开他的衣角,学着他的模样正色道:“反正我会护着她的,你,也不准欺负她。”
所有的画面全都倒映在雪花里,好像如昨日,转眼却又是一冬,我好像被困在了巨大的冰块中,外面的天地不过一方狭小的洞穴,有人来看我了,月白的罗裙印着略带红晕的脸颊,“夜歌?”
她说:“对不起,他不让我来见你,所有我才……今日我是好不容易避开他,才能过来的。”
“我知道,谢谢你来看我,他……还在生我的气吗?”
“你杀了九尾灵狐,毁了九州同东辰的关系……他……”
我愤愤不平的打断道:“谁叫那只臭狐狸想要轻薄你的,活该,更何况是他先取我的性命才被我的赤龙令反噬的,他这么聪明应该知道的呀。”
“我将前因后果都跟他说了个清楚,想必他气恼的不过是平日里太过纵你了,我……我眼见你在这受苦,却不能救你……”
我宽慰她道:“不碍事,他不过是想让我收敛收敛性子,想来要不了几日便能出去了。”
“恩,到时候我来接你。”
我像是在梦里醒着又像是在梦外面睡着,我知道这只是我的一个梦,我能恰如其分的跟梦里的人相处,好像是我本来就该如此,可我又清楚的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我能感知阳光洒满天地,可我摸不到它的温度,我能看见周围冰雪陡峭,可我接不到一片雪花,我在冰封的空间中,看着洞穴外的唯一一抹光亮暗了又明,好像日复一日不过须臾,可眼角溢出的泪珠又在提醒我度日如年的苦闷,我自知心境如何却又有些不明所以,直到……
直到我在某一日醒来,或者说我在等着自己从某一日醒来,这里仍是梦境,只是今日我变得莫名的紧张起来,人影走近,洞穴被遮去了一半的光亮,然后我看见朱红的嫁衣一步步朝我走近,在她路过的地方,花开遍地,那些姹紫嫣红的花色在这冰雪陡峭的洞穴中开得分外耀眼,隔着厚重的冰面我还是看清了来人的面容,一支凤尾簪,一袭百花朝圣衣,已然让我红了眼眶。
他自生来便是众星拱月,万神朝拜,手握天地之权,也执剑平定魔乱,他说他从未碰过女儿家的东西,却也不知是一时兴起还是兴之所至,他将随身多年的白玟剑碎了,亲手打了一支凤尾簪,又取了瑶池的百年霞彩,化了蓬莱的千木花园,以罗湖的流光为线,织就了一件朱红的嫁衣,取名百花朝圣。
神魔两界皆知,凤尾定情,百花朝圣是他的彩礼。
来人轻启朱唇,问道:“你觉得,我美吗?”
我拭去眼角的泪珠,一字一句道:“夜歌,让他来同我说。”
她的笑声在这寒冰的洞穴里显得空旷刺耳,“他不会来了,世间只有一只雪兰花妖,他从未错过,其实万象虚空中本无雪兰之花,他自出生便是天地之主,无欲无念已至天境,本要羽化成就大道,却在羽化之时,落了心头血在天河冰原之上,心头血融雪而化,竟生生的开出一朵花来,花色似雪,淡香入骨,也正因这一抹入骨的香让他弃了羽化之念,至此住到了天河冰原上,日日以心头血浇灌那一株花,一人一花相伴了无数个日夜,转眼已过千年,花**血而生,血又入冰原,冰原的雪和那株花一样都有了灵力,只是未能幻化人形,可是却已能交谈,他心下欢喜便将此花命为雪兰……”
她顿了顿,看着我已然清晰的目光,接着说道:“雪夜鸣歌孤唱,是我在雪原的夜色下为他唱的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他轻抚我的枝叶,为我赐名夜歌,后来神魔之战,几乎将天河冰原尽数毁去,雪山崩塌,雪水滴落,我也随着雪水落下了凡尘,他寻了我百年,寻回的却是你,你本是冰原的雪水所化,跌落幽冥便化成了雪兰花妖,而我本就仙灵附体,即便落了凡尘,我仍是仙体,世间雪兰花仙只有我一个,而你……是雪兰花妖。”
我拼命的摇着头,“我不信你,我一个字都不信你。”
她不再管我转身离开,嘴上噙着笑意,唯独留下一句,“你若还不死心,便自毁内丹,放出玄天之火解了这水墨洞天的冰封亲自去问他,只是今日是我们大婚之日,你若去了,许是魂飞魄散之命,他,不会再容你。”
最终,我还是出了水墨洞天,以内丹化出的玄天火烧尽了整个水墨洞天,我疯了,满目的霞彩像是被我血液染红一般,我内丹已毁,意识消散,我在手臂上划出一道又一道的口子,我必须清醒的见到他,脑海里的片段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他说,小白,你的心是凉的,捂不热吗?
他说,你是妖又如何,我可入魔。
他说,小白,你是我的软肋。
他说,你若陪我去看一次雪兰花海,我……就把命给你。
他说,小白,你只能是我的妻子。
那些话还言犹在耳,可是他,却已执手她人。
东辰天境的五彩霞光竟铺就了万里,火凤衔着花枝在空中飘洒,飞鸟成群结队的齐声歌唱,银河的星尘被仙娥们装在了玉篮中,一路飘洒,空气中浮荡着雪兰花香,沁人心脾,十二仙音怀抱琵琶箜篌,以灵气催动琴弦,琴音如爱语,一曲曲百转千回却又动人心弦。
他喜白衣,我一直都知道,可我不知他穿红衣也是这般蛊惑人心,好像天地之间独他一人潇洒,别的景致似乎都成了俗物,眼前是一双璧人成就姻缘,他牵着夜歌的手,在天宫众神面前给她正妻之位,可是这个人曾为我挽袖下厨,为我劈山铸琴,为我坠入轮回化身人族,挡下灾劫,为我踏平整座南荒山,灭去灵猫一族。
我现身而出,撑着最后的力气喊了一句,“长宁。”
他放开夜歌的手,转过身来看着我,眉头微微皱起,却不发一言。
我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耗尽所有灵识,捻诀成剑,不等他反应便不偏不倚的朝着夜歌刺去,不过瞬息之间,却让我觉得那是漫长的千年万年,漫长到他曾经的每一个转身都一一在脑海里浮现,他为我转身,眼里有我的影子还有火光的跳动,而这一次,他为的是夜歌,我看到他将夜歌护在自己的怀里,他的背对着我的剑。
我的右手已是难收之势,在剑尖刺破他外衣时,运气于左手,狠狠地朝着右手的手腕劈下,他以前时常夸我一心二用的本事放在剑招上,一剑两招甚是独特,却不想如今竟用到了自己身上,右腕吃痛经脉尽碎,那柄灵识所化的剑也终是落了地。
其实以剑相逼,要的不过是一个答案,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可能伪装的答案。
我的体力已是极限,这一击后便软软的倒在了他的面前,他抱着夜歌凝视我许久,我突然想起第一次在幽冥见他,他从月亮河的河底悠然走出,莹白的长袍未被打湿半寸,似乎河水都避让着他,我大着胆子好奇问他在做什么?
他说,我在这里丢了东西。
我问他是什么东西,竟掉在了河底,他并未答我,反倒突然问我,你是雪兰所化?
那时的他就是这般凝视我许久,好像眼目所及之处都能染上寒霜,我倔强的看着他,本以为他会骂我、恨我、恼我,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就在他将夜歌横抱而起之时,微微的朝我挥了挥手,一阵清冷的掌风袭来,自我脚下开始,寒冰开始封存我的身体,我一边笑一边哭,不知道是在问他还是在问我自己,“你要了我的心,怎么就不珍惜了呢?”
然后,我亲手碎了魂魄。
最后一抹意识,只有一句,“迦兰若——”